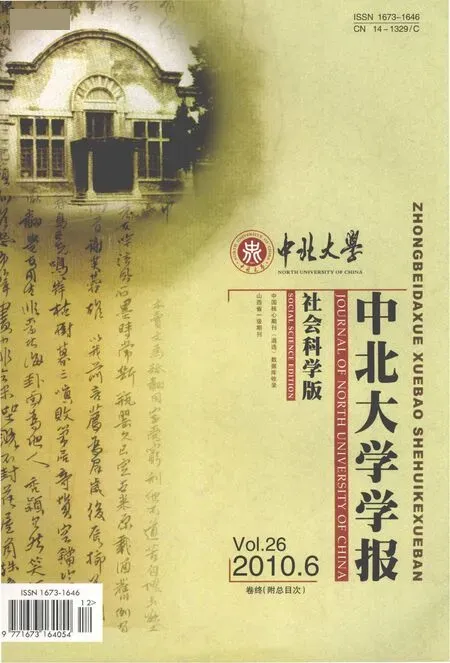迷途的青春期与得道的成年期
——刘恒的城市系列小说研究*
张 柠,许姗姗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迷途的青春期与得道的成年期
——刘恒的城市系列小说研究*
张 柠,许姗姗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刘恒的城市系列小说通过空间、人物、语言三个方面关注城市文化的复杂属性:小杂院和街道等真实空间代表了传统乡土与现代都市的两个维度;纯情女与狐妖女等欲望空间充满了传统男权的想象;青春期和成年期两个人物代际展现着与生活和解或无法和解的状态;小说的语言也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北京第三代胡同青年对革命符号、都市符号的运用。
城市文学;空间研究;青春期;成年期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的现代化和城市意识的觉醒,构成了许多作家另类的文本叙述和想象方式,一批具备真正现代都市特征的城市小说出现,刘恒便是这批作家中的一个。刘恒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系列小说包括《黑的雪》、《白涡》、《虚证》、《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其中有迷路青年的形象,在街道上无方向的漫游,或者寻找一方净土,用自杀来逃脱进入成人世界的成年礼;其中也有得道者的形象,完成蜕变与搏杀进入成年期的飞黄腾达,或者自我幸福指数居高不下。这里,迷路的青春期与得道的成年期代表了具多元文化属性的北京城中两个代际的不同心路历程,城市投射在他们心中,展现着不同的倒影。
1 意象化空间:文化的自留地
按照克朗文化地理学的观点:“不论‘文化’如何被定义,我们都应该把它放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情景中,放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去进行研究[1]1。”因此,刘恒北京城市系列小说的文化内涵,首先可从他在文本中设置和排列的一系列空间体现。他的意象化空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真实的空间,以小杂院和街道为代表;另一类是虚拟的欲望空间。
1.1 小杂院和街道:传统乡土与现代都市两个纬度
传统对于北京城而言,不是一种抽象的能指,也并非来自遥远乡村的愚昧观念。它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已经成为整个城市无意识中最坚稳的一部分。它挥之不去地漂移在城市的空间形态,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和精神构成之中。比如胡同、四合院、小杂院,等等。
刘恒的小说《黑的雪》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故事都被安排到了小杂院里。小杂院是具有北京特色的一代建筑,“小杂院是辛亥革命之后渐渐普及开的,当时没落的旗人为了生计,将他们住宅的部分出租[2]68”。小杂院不同于四合院,它是许多人家合住其中。如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张大民“像一个掉在地上的汉堡包”的家,院子里还住了“在轧钢厂做翻砂工”的亮子等其他家庭。这种杂住首先说明了居民们的社会经济背景。它不同于四合院的独门独院,其拥挤程度堪比北京城郊的贫民窟。因此,张大民居住的小杂院就代表了小人物的悲欢,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作者不是对城市做出大全景式的概览,而是切入细胞内部进行白描。这延续了京味小说一贯的叙事逻辑,如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小羊尾圈子,在这样一种“都市中的乡村”或“田园化的都市”中展现人伦亲情、邻里友情。而此时的人物也少了现代都市中疏离而冷漠的城市病,更像一个亲近热乎的乡土熟人社会。
刘恒城市小说中最能体现作者空间焦虑和关怀的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高楼林立的北京在迅速发展,作者的镜头却停在一个“掉在地上的汉堡包”上。这里没有霓虹灯、拱廊街、高层建筑、旋转扶梯,而是被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都市所忘记,是城市中安乐的乡土。王安忆也曾在《长恨歌》中描写上海的弄堂,现代化浮靡的大都市里,弄堂才是历史的芯子。从“爱丽丝公寓”到弄堂,空间的变化恰恰言中了王琦瑶从上海三小姐的风光,到被时代与现代都市遗忘的生活状态。《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汉堡包”也与现代化大都会的北京无关。张大民家院子中的石榴树就是极好的隐喻:父亲种下的石榴树代表着传统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和合状态;可是这棵树却成了张大民们现实生活中的障碍,它阻挡了子辈们想要拓展生存空间、提高生活质量的意图。石榴树不能砍,它成了张大民在自己新建房屋中一个突兀的存在。这代表着城市下层平民依旧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也代表了北京传统与现代属性的内在张力。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张五民有不同的选择,他为了逃离喘不过气的屋子,决意出走走仕途。这代表了一部分精英们的意识:要撕破自身才能获得自由,逃脱压抑逼仄的传统空间,进入更为广阔的现代都市中去。
要进入广阔的现代都会,首先要进入一个特殊的空间,即街道。比如《黑的雪》中李慧泉经常在街道上溜达;《白涡》中周兆路和华乃倩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也是在街道边;剧本《四十不惑》开头便写到“街道上一张张陌生的城市人的脸,男女老少表达着极其对立的情绪。[3]233”街道是城市文明的产物,它因交换而出现,不是因生产而出现。因此,街道是都市文化中一个奇特的存在,不仅仅是地缘学意义上的一条路,而且有深层的文化学意义。街道代表着完全的陌生化。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而都市生活则不然。街道因此就像一个宽容的器皿,不需要身份证和人生档案,完全充满异质性。《白涡》中周兆路第一次见华乃倩时,作者借周兆路之眼观察了街道:“长安街平庸的人堆里不时闪出被薄薄的纺织物包裹的年轻女人出众的肉体。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可以随意支配目光,去追逐他感兴趣的每一个人。这时候他是自由的,略微带点邪恶。[4]111”单位相当于传统的“熟人社会”,周兆路作为医院的领导,熟人社会中当然不能胡作非为。而街道则不同,它是一个片段的回避性场所,逃离了限制性的空间,可让人们暂时将日常逻辑和权力逻辑置于身后,人群彼此不相识,不清楚对方的身世和历史,没有一种严厉的权力目光,或洞晓自我秘密的目光。也因此,邂逅成为城市中最浪漫的情节。
正因为街道的陌生化,流浪者对于这个陌生世界的发现(再加上都市货币、女人、商品符号的刺激)就构成了现代犯罪学的起源。街道是流窜作案的场所,也是罪犯和逍遥法外者的庇护所。《黑的雪》中,刚从狱中释放的李慧泉极其渴望自由,而街道第一个给了他自由身。“他要沿着熟悉的街道好好转一转,想上哪上哪儿,没人看着你管着你,这滋味真叫人陌生。[5]6”街道以其宽大的肚量和健忘的记忆包容了李慧泉这样的失足青年,成为“逍遥法外者的最新避难所,也是那些被遗弃者的最新麻醉药”[6]78。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是一个代表政治历史经验的街道,而是商业性的街道。在《黑的雪》中,街道的交通功能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减弱,街道的尽头便是李慧泉的小摊,街道的一部分变成了商品展示和贩卖的拱廊街。“日落之后,摊前聚了一些女孩子,她们的目标是面积只有巴掌大小的康佳短裤……短裤的遮盖面积越小,越能引起女人的兴趣[5]84”。这里走私进口的丝薄短裤撩起温柔的小手,召唤着人们脱去坚硬意识形态包裹一身的中山装,以暴露获得解放,尽情展示着属于现代城市文明的身体,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身体。小杂院与街道,以“传统”与“现代”的两级展现着北京复杂的文化属性。
1.2 纯情女和狐妖女:欲望空间的传统想象
刘恒擅长描写欲望。他的乡土小说一直将视野放在人类本能欲望——食和色的描写上。他的城市小说也描绘了一系列的欲望空间,尤其是“色”,成为环绕城市人心头的痼疾,并且展现了传统男权的想象。
刘恒的小说有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其中存在两种较为明显的人物类型:纯情女和狐妖女。纯情女以《黑的雪》中的赵雅秋为代表,包括《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张三民的媳妇毛小莎;狐妖女以《白涡》中的华乃倩为代表。而刘恒论述了一个圈套,那就是“纯情女”原本只存在于传统男权的想象中,实质上她们也是熟谙都市生活规则的聪明的浪荡妇。
《白涡》中,作者借男主人公周兆路之口,刻画了华乃倩狐妖女的形象。“女妖在他眼前跳舞,那是华乃倩赤裸丰满的身体”[4]13;“那个女人魔鬼般似的立在黑漆漆的海滩上,向他伸出了苍白的手臂”[4]19。“狐妖美女”是传统男权对于女性的一种想象。古时便有《金瓶梅》,新时期以来,有路遥《人生》中黄亚平对高加林大胆的追求,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香久、马缨花;《白涡》更是塑造了一个女妖面、女妖心的女性。“他迷恋那具温软的肉体。说到底,是她勾引了他”[4]13。从《伏羲伏羲》到《白涡》,一脉相承的狐妖女所代表的传统想象如同暗夜在霓虹灯下游荡的幽灵,挥之不去。纯情女以《黑的雪》中赵雅秋为代表。赵雅秋是酒吧中的歌手。男主人公李慧泉第一次见到她时,“使这个姑娘讨人喜欢的,是她脸上略显腼腆的纯净表情和她的歌声。[5]65”他一直认为她纯净若水,因此连自慰时也不用她做发泄对象。赵雅秋成为他内心自设的净土上独开的一枝梅,与外部俗世格格不入。小说最后却让他自设的爱情传奇轰然崩溃。李慧泉发现,赵雅秋因为投机倒把分子崔永利答应圆她的明星梦,便愿意肉体交易,跟随崔永利南下广州。李慧泉再一次遇到赵雅秋时“他觉得自己仿佛不认识这个人,[5]199”他想到,“她叫人毁了,他战战兢兢地给自己设了一尊神,结果发现这尊神是个聪明的婊子”[5]203。这意味着现代爱情根本无力超越平庸的性质,李慧泉内心憧憬了古典爱情的浪漫色彩,而现代都市的爱情却以此成功反讽了传统的古典爱情。
同样的还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张三民的媳妇毛小莎,“长的就那德行,其实不妖,挺懂事的。看电影老掉眼泪。我不跟她好,她就钻汽车轱辘,挺懂感情的。[7]316”小说最后又一次用都市文明下的现代逻辑撕裂了这个纯情女的面纱。她和别人睡觉换来了升迁的职务和扩大的住房。“我媳妇是个婊子!不是一只好鸟,是一只浪鸟”[7]355。这再一次反讽了都市中的纯情形象,她们只存在于主人公任性的想象里。实际上她们却是都市文明中穿着水晶鞋的灰姑娘。都市文明的钟声敲响,灰姑娘奔出大厅,她对那传统文明的南瓜马车不屑一顾,而蹦蹦跳跳到奔驰、宝马、保时捷上,空留着手拿她遗落水晶鞋的人暗自惆怅。
2 青春期与成年期:人物的两个代际
刘恒城市小说中的人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拉斯蒂涅式外省来的青年人如何适应都市生活,如《白涡》中的周兆路,另一类是北京土生土长的胡同青年们的精神状态,如《虚证》《黑的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这些青春期与成年期两个代际的人物展现着不同的心理变奏:一类是表面与都市生活和解,内心却躁动不安;一类是生活本身贫乏混乱无法和解,内心却倍感幸福;居于两者中间的还有表面与内心都驯服而安稳的和解者。
2.1 青春期的游荡者
《虚证》中的郭普云与《黑的雪》中的李慧泉都是城市中游荡的边缘人形象。这些青春期少年表面与外部世界和解,内心却充满自卑和孤独,最终不得不选择自我结束夹缝中痛苦的生命。
《黑的雪》写了失足青年李慧泉出狱后企图重新生活,却在格格不入的环境中寻求自救而不得。“迷路”是他的起点。他因打架而入狱。出狱后,虽然他老老实实做生意,却依旧找不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他始终感到自己被抛掷的命运,首先是因为他的身份原罪。“他是父亲的朋友从北京火车站抱来的,他既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五九年秋季一个阴雨天,多半是他的生母,把它连同一团破布扔进了北京站东边的一条电缆沟,她可能指望雨水淹死他”[5]3。世界的敌意在李慧泉这里,首先从母亲的敌意开始。连骨肉相连的母亲都想让雨水淹死你,还怎么希望整个社会容纳你?而他失足青年的形象也铁板钉钉一样钉在邻居们,以前好友父母们的心中,他一直是遭人厌恶的多余人。“生活就是这幅模样,他永远挤不上车,乘车远去的人吵着叫着笑着,没有人在意他一个人给抛了下来,他也许永远赶不上趟了。[5]18”他渴望得到社会的接纳和认可,却一直感到“要么浑浑噩噩的活着,要么四处逃窜,像丧家犬[5]176。”自杀前耳边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养了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对于这些世界的流浪儿,死成为他们与世界和解的仅有方式,停止迷路和流浪的最好解脱。
《虚证》中的郭普云虽然并没有真实的失足经历,但他却有巨大的内心创伤,即被阉割。苏珊·桑塔格宣称:“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惧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8]7”性便是这样一种角色。它不仅仅是秘而不宣的个人行为,也一直与政治、革命、历史、道德等多种因素相关。从郁达夫开始,性就与现代国家的文化相联系,人物的勃起期待与国家的富强期待同质同构。之后古华、贾平凹、刘恒、王安忆都曾塑造了一些失去性能力的“阉割人”,《芙蓉镇》中的谷燕山,《鸡窝凹人家》中的山山,《红高粱》中我奶奶的前夫,他们以丧失性能力暗示生命活力的消失和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刘恒的《伏羲伏羲》也是如此,杨舍山的被阉割隐喻了时代衰朽势力的消退。《白涡》中林同生的性无能凸显了阴盛阳衰的狐女华乃倩。《虚证》中主人公郭普云是一个阉割人,他身上体现了都市中传统文化和纯真心灵悲哀的现实处境。
郭普云在心里觉得“爱情是多余的,就是这样”[9]17,在生理上,“郭普云的家伙不好使[9]47。他并不向往爱情,但在小说刚开始他喜欢看一个“长得像林黛玉的姑娘”,这表现了他内心对古典审美方式的留恋。但这又在现代物质文明和思维方式面前溃不成军。他性能力的丧失,不单是一般医学意义上的阳痿,而且隐藏了非生理性的精神创伤。小时候学跳舞被男生嘲笑,“他的初吻被一位强有力的异性夺走了”[9]19,异性的强大让他一直未曾走出青春断乳期的角色,始终是孱弱的男性符号。所以他表面虽然未对世界有敌意,被大家公认为好人,但是始终“感到和周围世界难以沟通,他(郭普云)请我喝酒,烧菜给我吃,都遏制不了他内心激荡不已的排他情绪……不独我,整个无边的外部世界都无力给他哪怕一点点的救护。[25]”也正因为并不熟谙都市的法则,成为都市文明的边缘人,和《黑的雪》中李慧泉一样,他充满强烈的自卑情结,自卑源于“眼底出血永远不能根治,黑色素永远不能再生,诗歌永远不能写出光彩,生殖器永远不能勃起,命运永远不能把握[9]68”。他最终选择在一个“干净的地方”自杀身亡,死在驹子峰和河水里,是对都市文明的最后一次反叛和对传统文化的醉心回归,也证明了人生存在的虚妄和内在悲剧性。
2.2 成年期:四十不惑
生活混乱无法和解,内心却倍感幸福的代表是贫嘴的张大民。《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写的是北京大杂院里一个物质生活贫乏的下层工人家庭的故事,在贫嘴的背后,是阴郁的生的沉重和无奈。从表面上看,张大民有充分的理由和生活不和解:父亲横死,母亲痴呆,妹妹病死,家里拥挤的住房,让人际关系内部扭曲。如果换一种腔调描写,这个文本应该算作“底层文学”。可是都市生活中的张大民却找到了与社会的和解之道,就是自我调侃。这在后文论述,此不赘述。
以《白涡》中的周兆路为代表的是一批表面和内心都驯服于世界的和解者。在《白涡》中,北京已不是一个负载着古典和文化记忆的古城,而是一个充满欲望与冒险空间的国际化大都市,它记载了“拉斯蒂涅”式的外省青年周兆路的发家史。周兆路来自农村,“他这个土包子刚到城市上大学时,同学们都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他。裤子是粗布做的,袜子上打着补丁。可是一旦他的成绩名列前茅,使别人在竞争中失败的时候,他的山里人特征乃至他的口音,都成了人家嘲弄他的把柄。他努力改变自己,终于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胜利者。[4]41”都市一开始嘲弄这个外来者身上的乡土特征,试图将其排挤到边缘。但是周兆路却将乡土社会的生活法则和粗布裤子补丁上衣糅在一起,统统丢掉。然后西装革履地融入都市的规则,“他希望在一切有关人的心目中,中医研究院年轻的研究员是个随和而谦虚的人,这种人比那些本领高强却性格怪癖的家伙更容易被别人接受”[4]3。他用都市人的身份改换了自己的历史和现在,将乡土印记抛到脑后。“如今那一片山林(家乡)留给他的痕迹,只有它(茶)了。[4]2”正因为熟谙了都市生活的规则,周兆路成为世俗真正的成功者,通过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他也明白了华乃倩为什么爱他。不是她勾引他,而是他把她俘获了。[4]43”来自乡土的周兆路,终于在不惑之年成为都市里追名逐利游戏的最大赢家。
3 语言的炼金术:改造与效用
京味文学最外在的特征是语言,从老舍为代表的第一代京味,20世纪80年代以林斤澜、邓友梅,汪曾祺为代表的第二代京味,再到第三代如冯小刚、王朔等北京作家,都是漂亮的“京片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语言也体现了北京人特有的“贫”文化。“贫”是张大民获得幸福的重要手段,他娶的妻子,激怒亮子实现盖房,获得戒指,揶揄技术员,击退情敌,都是通过他的“贫”得以实现。而他的口中喷涌而出的,除了逗人的语料,还有第三代京味文学中胡同青年们的精神文化形态。
张大民“贫”的方式首先是对革命符号的调侃,将个人问题上升到集体、国家等宏大境界中进行阐释。李云芳失恋后得了忧郁症不说话,张大民劝其开口说:“你为什么不说话?江姐不说话是有原因的,你有什么革命秘密?你要是再不吃饭,再这么拖下去,你就是反革命了!人家董存瑞黄继光都是没办法,逼到那份儿上了,不死说不过去了。你呢?[7]306”
张大民的劝说动用了革命符号。在前意识形态中,个人经验是不被许可的,只有与国家、集体、民族等宏大的概念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张大民的语言便是对这种逻辑的调侃。革命完全嵌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包括其遗留下来的语言碎片和思维习惯。因此对革命符号的调侃,也是对长期主宰人们生活的“革命话语”的调侃,造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滑稽感和荒诞感。这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波普的常用手段,让童年的阴影成为成年期随手拈来的搞笑材料,它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诉求,不是去营救历史人质,而是向历史和某种官方说法索取个人的叙述方式。
“亲娘的奶水终于把美国奶粉打败了。不对!是一只中国的王八,一只变成了浆糊的大王八,把美国的牛奶拖拉斯给彻底击溃了。[7]346”“我敲了足有一万个门了,终于看见了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中国有救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有救了。我们靠暖壶吃饭的人有救了![7]385”在上述极为琐碎的情境中,张大民都用极端严肃的政治概念来搭配。在张大民嘴里,国家、民族、政治、革命等语词并非被祭奠在宏阔的祭坛上,让他们磕头神往,而是降格为插科打诨的原材料,可以搅拌均匀做成个人的小蛋糕。
张大民的“贫”还代表着都市小市民的精明和精神胜利法。
“你们厂夜班费6毛钱,我们厂夜班费8毛钱。我上一个夜班比你多挣2毛钱,我要上一个月夜班就比你多挣6块钱了。看起来是这样吧?其实不是这样。问题出在夜餐上面。你们厂一碗馄饨2毛钱,我们厂一碗馄饨3毛钱,我上一个夜班才比你多挣1毛钱。我要是一碗馄饨吃不饱,再加半碗,我上一个夜班就比你少挣5分钱了,不过你们厂一碗馄饨才给10个,我们厂一碗馄饨给12个,这样一算咱俩上一个夜班就挣得差不多了,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二民,你可千万别糊涂。早市上萝卜3毛一斤,到中午2毛一斤,天一黑就1毛一斤了。这时候过来个家伙,问你5分卖吗,你一不耐烦心一软,说不定就卖了。太贱了!”
小说中随处可见张大民的精明算计,有传统小农的节约,又有都市小市民的精明。这充分体现了消费已成为社会的新问题。从王朔的“边缘人”,到朱文的《我爱美元》,金钱爱好者们主动走进了物质世界,不再是商品时代里恐慌的大众,而是冲锋上阵成为其中的生力军。平民通过“贫”将实际行动转化为语言调侃,通过整人和涮人,通过制造语言诡计而成功获救。
“在美国年头儿不短了吧?学会刷盘子了么?美国人真不是东西,老安排咱们中国人刷盘子。弄得全世界一提中国人,就想到刷盘子,一提刷盘子,就想到中国人。英文管中国叫瓷器,是真的么?太孙子了!中文管美国叫美国,国就得了,还美!……他们叫咱们瓷器,咱们管美国叫盘子得了。[7]384”
这是张大民在揶揄老婆的前男友,一个技术员时的语言。张大民无法和技术员的物质水平相比,他获救的方式是调侃。通过擅长的调侃行为去自救,保障自己的自尊并获得语言上的胜利,寻求自我平衡,获得暂时的满足,用语言的胜利满足自我胜利的想象。
张大民的“贫”还用一种碎片化的语言拼贴,代表着碎片化的生活状态。
“我给您开门。上飞机小心点儿,上礼拜哥伦比亚刚掉下来一架,人都烧焦了,跟木炭儿似的。到了美国多联系,得了爱滋病什么的,你回来找我。我认识个老头儿,用药膏贴肚脐,什么病都治。回纽约上街留点儿神,小心有人用子弹打你耳朵眼儿,上帝保佑你,阿门了。保重!妈了个巴子的![7]384”
他的语言中经常会使用譬喻的方式,并且通过非逻辑化的语言碎片的嵌入,词语的拼贴,夸大无意义的东西,缩小重要的东西,使他小说中音调与内容不和谐,幽默于此产生。而这碎片化的语言也恰恰代表了破碎的现代生活,一个接一个并列的句子,一个接一个形象的拼贴,一句赶似一句的语速,带来了眩晕感,暗示着后现代狂欢嬉戏拼贴的质感。语言也不再是精英的独白,承载着梦想与责任,而是小市民们插科打诨的戏谑调侃。这种调侃也使我们想象了一种新的中国形象,它轻松自如地打碎了来自精英规范的那种一体化、绝对化和僵化的体制,小市民们模仿着大人们说话郑重其事的声调,然后哈哈大笑。
刘恒的《黑的雪》、《虚证》是传统与现代夹缝中个体迷失的寓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又为一个新时代的中国生活形态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感。个体若想跨越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鸿沟,跨越现代人沉沦的谶语,得道升仙,或者如同《白涡》中的周兆路一般夹着尾巴一步一个脚印地顺杆向上爬,或者如张大民般用话语的涂改液把周围的敌意涂抹掉,这或许才是大众犬儒们最后的免死金牌,或者挥斥方遒的鸡毛令箭。
[1]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白鹤群.老北京的居住[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3]刘恒.四十不惑[G]//刘恒自选集·电影剧本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4]刘恒.白涡[G]//首届北京文学获奖作家作品精选集·刘恒卷.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5]刘恒.黑的雪[G]//刘恒自选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6]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
[7]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G]//李敬泽.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8]苏珊·桑塔格.痴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9]刘恒.虚证[G]//刘恒自选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Lost Adolesc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Aadulthood——Liu Heng’s City Novels
ZHANG Ning,XU Shansh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Liu Heng’s city novels concern the complexity of urban culture through space,characters and language.Real space like small courtyard dwellings and streets represents the two dimensions of traditional local color and modern city,and desire space like pure female and fox demon female is filled with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imagination.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ce and adulthood unfolds the states of compromises or the contrary.His language interprets the revolutionary symbols and urban symbols used by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BeijingHutongyouth.
city literature;space research;adolescence;adulthood
I206.7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0.06.001
1673-1646(2010)06-0001-06
2010-11-10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当代北京作家与城市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BeWY060)
张 柠(1958-),男,博士生导师,教授,从事专业: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