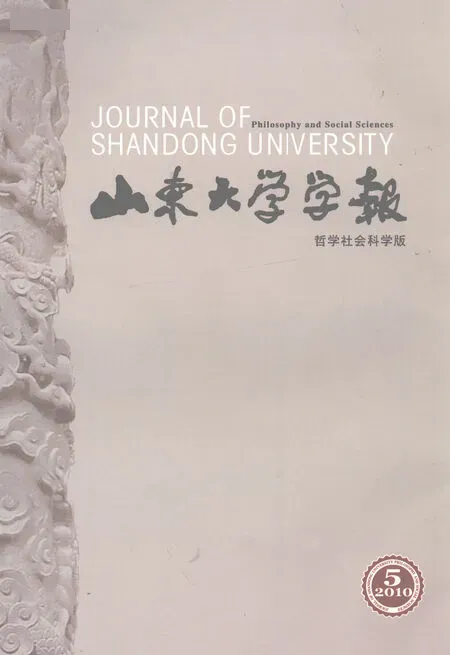作为生存之道的非正式社会控制
王启梁
风俗、民间法等民间规范的运作以及社会成员运用非正式手段对越轨作出反应,被视为非正式社会控制。非正式社会控制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生存之道,解决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细微但是重要的问题,维系和生产着地方性的微观社会秩序。
与人类学家早期重点研究的初民社会或国家统治松弱的社会不同,这些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而我们所身处的当代中国,国家权力已高度渗入社会,从空间上来讲,几乎已经不存在所谓的国家不入之地,仅存的只是摩尔所说的“半自治社会”。①Sally FalkMoore.Law as Process: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Routledge&Kegan Paul,1978.因此,即使我们考察的是在民间社会中生发出来的非正式社会控制,也需要放在两个背景下认识和理解,第一个是特定的历史脉络、话语和情境中即地方性的生活,第二个是多元社会控制(或法律多元)的框架中。在地方性的生活中,我们才能洞悉什么样的因素塑造了非正式社会控制,并理解非正式社会控制对于社会生活的建构和维系的重要性;而放在多元社会控制的框架中,也才能认识国家对社会的建构和秩序形成的影响,发现非正式社会控制与来自国家的正式社会控制之间的紧密关系。
一、引子:凉山彝族的“死给”、家支械斗
在一份调查中记录了一个案例:在四川凉山,1953年一个叫根扎莫冰比的女子因为受到羞辱而自杀,直到近 40年后的 1991年,此案被根扎家族重新翻出,经过德古调解才最终解决。②海乃拉莫、曲木约质、刘尧汉:《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集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170-171页。此案在凉山彝族社会中并非特例,因纠纷而自杀是一种制度性的私力救济现象,此类自杀被称为“死给”,当地彝语称之作“斯吉比”,直译意为“互相死给”。“死给的基本情形是,某两人因为任何事情,通常是些小事,发生口角纠纷,一
死给的可怕之处在于,发生死给之后也就导致了当事人之间家支的对立和冲突,此时如果没有第三方“德古”或者德高望重者及时出面调解,则会引发严重的家支械斗,②张晓辉、方慧:《彝族法律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04-324页。这种械斗甚至持续数代人。③林耀华:《凉山夷家》(1945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 79页。根扎莫冰比案发生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使此案没有引发家支械斗,但是时隔近 40年后的调解过程涉及到几大家支的上百人,如果没有德古的成功调解,仍然有引发家支械斗的可能。④转引自蔡富莲:《论凉山彝族传统习惯法的功能》,载韦安多主编:《凉山彝族文化艺术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 213-214页。
在死给案中,自杀行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方式。第一,自杀直接导致了权利救济程序的发动,自杀使家支介入纠纷,要为死者讨还公道。在大多数案例中,还会导致德古等第三方调解者介入调解纠纷。死给的一方在纠纷的解决程序发动之后显然可以立刻扭转先前处于弱者的局面,在彝族习惯法中被死给的一方处于不利的地位,导致他人死给就是一种不道义的行为。⑤详情参见周星:《死给、死给案与凉山社会》,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下)》,北京:群言出版社,1998年,第726-727页。被死给的一方面临巨大的压力,死给的一方可以成功地在死后把一大堆麻烦留给和自己发生纠纷的一方。所以死给首先是一种发动权利救济程序的私力救济。第二,如果死给发生之后,没有第三方调解者介入或者调解失败,将导致发生纠纷的双方的家支之间的械斗,无疑是一种规模更大的私力救济,虽然这种私力不是由死者所组织,但是乃因死者而发动。
二、非正式社会控制与社会结构
从上述凉山的案例中,我想引起的讨论是非正式社会控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凉山彝族死给案及相关习惯法的产生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凉山特殊的社会结构。周星先生在研究中指出,凉山彝族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家支林立、互不统属,并且在这些家支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和组织,因此家支成为人们的主要依靠,如根扎莫冰比案中,赔偿是由当事人家支共同承担的。围绕家支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习惯法,死给、家支械斗都是这种社会结构的产物。⑥周星:《民俗、习惯法与法制》,载乔建等主编:《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的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 302-331页。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法律等一系列的制度进入了彝族社会,但是在凉山彝族的腹心地带,国家法律的影响力仍然是松弱的,家支仍然是彝族社会的主要结构构成,个人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缺乏独立行动的能力。个人如果发生纠纷、遇到问题就不得不依靠家支,因此,死给就是一种发动家支力量的程序和方式。死给以及由此发生的一序列家支行动、调解就成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并且能够持续存在。
在云南金平县一带的哈尼族和彝族村寨中,对于违犯村规或习俗的村民,集体能够实施一种非常严厉的处罚“开除村籍”。⑦详情见曹文武:《检察机关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执法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问题》,载方慧主编:《少数民族地区习俗与法律的调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 406-410页。从社会结构和组织的角度看,反映出的是这些哈尼族、彝族村落的社群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社会中,村落是一个基本的行动单位或者说是可以超越家庭、家族的行动单位,具备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否则,需要高度团结和组织化的“开除村籍”行动就不能发挥效率。这类社会控制在“原子化”的村庄中是不可想象的,⑧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 115-138页。同样,在那些人和人之间相互关联度和依赖性较低的社会中,这样的惩罚既不能被发动也不能对越轨者产生出威慑。在另一项田野调查研究中,可看到一个傣族村落曼村有着很复杂的社会结构,多元的社会控制严密地嵌在其社会结构中,秩序良好,这得益于村落中尚未完全瓦解的社群生活方式以及高度复杂的权威结构能够有效提供出社会控制者。①王启梁:《内生性村落社会秩序是如何形成的?》,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 8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41-73页。在另一个村落个案中也能看到民间权威在纠纷解决中起着重要作用,②王晓珠主编:《拉祜族——澜沧糯福乡南段老寨》,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107-110页。其原理同样存在于村落的社会结构中。
这些研究表明,不同的社会结构会产生出不同的村民行动单位,而社会控制说到底是一种行动,村民行动单位往往与社会控制者相重合,或者行动单位决定了村庄中的社会控制形式及其运作机制之间的关联性。贺雪峰教授依据在核心家庭以上是否存在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将村庄作了不同类型的划分。③贺雪峰:《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载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第二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99 -118页。如果把贺雪峰教授的这一研究和社会控制的机制相联系,那么每一种认同单位都可能成为社会控制者,形成不同的社会控制运作机制。而民间生活中,社会控制的复杂性就在于,村落中的认同和行动单位的不同,决定了越轨或纠纷发生时村民采取的行动不同,因为行动单位是村民所能动用的一种资源,是他们所能依赖、发动的社会控制者。如果在这些认同和行动单位、不同的社会控制者之间能够形成有效的关联和清晰的认同层次,那么村落中多元的社会控制之间就能有效协调,实现社会秩序。如果村民对这些社会控制者不能形成不同层次的认同、协调,那么就会产生出社会控制机制之间的冲突、真空地带。④王启梁:《传统法文化的断裂与现代法治的缺失》,《思想战线》2001年第5期。并且,由于村民认同所形成的社会结构规定了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格局,并直接影响着社会控制和纠纷的解决。⑤参见陈柏峰:《村落纠纷中的“外人”》,《社会》2006年第 4期;易军:《关系、规范与纠纷解决》,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
对社会结构有着多种认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布朗的研究,⑥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 159-160、165页。说明社会结构是社会行为者个人及其群体在社会当中的配置与组合,社会结构直接规定了个人、人与他人以及群体间的身份归属与关系,所有的社会现实最终都能够还原到人与人的关系上。这种关系构成了一种规范,它是芸芸众生在互动中生成的,是对自我与他人的角色的一种定位和认同,并发展成为人与人之间支配、被支配以及相互支配的权力配置,规定了个人可能选择行动的方式和能够动员的资源,也规定了个人对他人如何行动的预期。社会结构本身就蕴藏着某种社会控制和秩序。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一旦形成,就构成了对生活于其间的个人和群体的约束,并且更为复杂的是它总是和特定的社会结构相关联,它反映、保护着社会结构,根源于社会结构,也因此受制于社会结构,但又能建构着某种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过程往往就是非正式社会控制变化的过程,而一旦非正式社会控制发生了变化也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些社会结构相似的微观社会如村落,往往也会有相似的社会控制机制,而另一方面,微观社会的结构是多样的,这是导致非正式社会控制多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非正式社会控制与文化
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结构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客观维度,也是人们借以采取行动、发动社会控制的客观约束,这种约束决定了人们能够动员的资源。但是,社会控制还受到社会中的价值、意义等这些文化性的主观维度影响。
回到前文凉山彝族社会,我们需要追问:普遍发生的死给和家支械斗难道完全由社会结构来决定?死给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呢?死给和家支械斗显然不能完全由社会结构来解释。凉山社会普遍发生的死给和家支械斗的深层次原因是彝族的主观价值和人生意义——对英雄的崇拜。对英雄的崇拜或者说是一种英雄主义和凉山彝族社会结构的结合,导致了世代绵延的死给和家支械斗。①王启梁:《意义、价值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年第 3期。社会所创造的英雄主义系统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道克服死亡恐惧的重要防线,它创造出一个英雄体系,使人们相信,通过参与某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人们就超越了死亡,②[美]萨姆·杰恩:《前言》,载[美]恩斯特·贝克尔:《拒斥死亡》,林和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 3页。人们也因此无需恐惧死亡。并且,凉山彝族的生死观认为,“个体在死亡之后,通过必要的送灵仪式,他们就能同逝去的祖先生活在一起,死亡只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③嘉日姆几:《试析凉山彝族传统临终关怀行为实践》,《社会科学》2007年第 9期。这就使人们在追求英雄主义的道路上比一般人更少惧怕死亡。社会就是一个大剧院,凉山彝族的死给以及由此引发的家支冲突、械斗、德古的介入、调解等一系列的习惯法制度,则为人们提供了展示英雄主义的舞台。英雄主义的戏剧行为从死给开始,至家支冲突达到高潮,到调解结束落下帷幕。凉山彝族的死给作为一种受到英雄崇拜鼓舞、生死观信仰系统支持而形成的制度化的暴力性私力救济或非正式社会控制,它的背后并不是野蛮,而是英雄主义的过度彰显。
从凉山的个案中,我们看到,什么是对与错和特定的文化相联系,人们为什么选择自杀作为发动救济程序的方式则是社会结构、彝族的生死观、英雄主义的主观价值复杂互动的结果。如果不能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脉络和情境中,我们就无法理解彝族社会中这种独特的社会控制。同样,在法律实践中,如果我们处理这样的纠纷时仅仅是简单地运用国家法律进行判决,那么终将无法真正了结纷争,因为纠纷的真正原因仍然存在,而这是我们在法律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形。在人类学者嘉日姆几的一项研究中,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游客和本地彝族的纠纷,双方在责任认定上没有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却集中在赔偿金额的额度上,彝族方按照本民族的观念提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价金,这对于彝族文化之外的人非常难理解。④详情及讨论见嘉日姆几:《云南小凉山彝汉纠纷解决方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 47-49页。另一个个案中,对于有舅表、姨表亲的男女发生性关系,双方又要结婚的,那么婚礼中必须举行一个“同槽吃食”的仪式。⑤谭晓健主编:《布朗族——勐海布朗山乡新曼峨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107页。越轨人须模仿同一种牲畜在同一料槽进食的行为,按照当地人的理解——近亲之间发生性关系无异于畜生。这一严重的羞辱性社会控制方式无疑和人们对于什么是人、人和动物的差别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这无疑体现了人们关于社会控制手段的独特想象和建构。事实上,各个民族和社会都有关于婚姻的禁忌,但是禁忌什么、对于违反了禁忌如何处罚则大相径庭,因为各个群体对世界包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不一样,惩罚的手段孕育自各自的世界观中。
又如在汉族的民间信仰中,祖先的牌位作为一个祖先灵魂的象征物,它“本身对已逝的人也许不是真正有什么作用,但是对活着的人却有着相当稳定心理与情绪、解决成员纠纷、肯定身份认同的社会意义。”⑥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 279页。在汉族的生活中,祖先牌位在某些纠纷的解决中是作为一种身份、继承合法性标志对纠纷解决起着作用。这样现象并不会存在于没有祖先崇拜、家族制度的民族中。所以,文化的多样性创造了规则和纠纷解决的多样性。
社会控制意味着存在某种关于是非对错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却来源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文化和价值观。在笔者的一项研究中表明,宗教作为一种世界观与民间纠纷的发生和解决有重要的关系。⑦王启梁:《宗教作为社会控制与村落秩序及法律运作的关联》,载谢晖、陈金钊主编:《民间法》第八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112页。而人的世界观并不仅仅由宗教决定,发现文化、价值观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就显得很必要。人是一种追寻价值和意义的动物,因此,人们如何行动不仅受制约于客观的结构、制度,还和人们关于意义的思考、对价值的追求这些主观性的东西有密切关系。所以,社会控制不仅和社会结构这一客观世界相联系,还和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等主观的世界相联系。社会结构和人的主观世界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规范、社会控制的不同样式、人们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控制的要求以及人们发动社会控制的内在逻辑。在另一项研究中,我论述了法律和规范都是一种安排秩序的分类体系,安排了事物、行为、意义的秩序。⑧王启梁:《法律:一个按排序的分类体系》,载朱晓阳、侯猛主编:《法律与人类学:中国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189-210页。分类的观念存在于文化体系之中,而文化其实是人们面对生活的环境所创造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种安排秩序的倾向,也是群体生活的规则。每个社会、每种文化都有它与众不同的分类体系,除却面对客观环境不一样之外,即使面对同样的问题,人们也会创造出不同的解决方法,所以每个群体都可能创造出其与众不同的规范和社会控制来,由此也就产生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的多元格局。
我们必须注意到,虽然可以在理论上分别对影响着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形成、运行的客观维度社会结构和主观维度文化进行研究和考察,但是两者对于非正式社会控制来讲是不可分割的。只有两者同时作用于个人、群体才会引发人们的行动,才会生发出非正式社会控制。非正式社会控制是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结合体。
四、非正式社会控制与生活样式的构建
非正式社会控制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运用源自生产和生活实践的规范来消除越轨和实现秩序的过程。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非正式社会控制是地方性的、群体的生存之道,关乎如何安排生活和秩序,它表现着社会结构和群体的文化,构建了生活的样式。
李亦园先生曾引罗素名言:“人类自古以来有三个敌人,其一是自然,其二是他人,其三是自我”。并以此来说明文化的内涵,人类创造文化正是应对这三个“敌人”。①李亦园:《人类的视野》,第101页。这其实是说人类生活始终要解决三对关系:自我(自己与内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国家正式社会控制如法律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后两对关系,非正式社会控制则要全部解决这三对关系,无论是国家法律还是民间的非正式社会控制,解决之道首先都是对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正确与错误的评判,并通过规则的方式来加以维护。所不同的是,国家法律等正式社会控制所要提供的是一种普适性的、关于一个国家如何获得秩序、获得发展的方式,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法首先是政治共同体用以安排、调整和形成(重构)人类共同生活的必要的组织和统治工具。”“任何政府都必须颁布法律规范保障其政治活动,这表明,法律是政治权力拥有者必不可少的形成工具。”②[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 41-49页。而非正式社会控制所要提供的是一种应对特定空间、时间和群体的问题的地方性的生存之道,是人们如何解决围绕这三对关系而产生的问题的指导。
因为空间、群体、民族的不同,民间的非正式规范和非正式社会控制在地方性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们展现了地方性生活中群体解决问题、维护和生产秩序的能力与方式。在前文凉山彝族的个案中,家支、德古、死给、械斗、调解就是人们应对屈辱和纠纷的方式。又如在村落生活中,我们普遍可以观察到非正式社会控制涉及到村落政治、经济、婚姻家庭、纠纷解决等方面,覆盖了村落生活的各个方面,调整着村落中、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安排了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关系。那些非正式社会控制健全和合理的村落就会展现出对社会变化较强的适应能力,有着较强的秩序维护和生产能力,典型如前引曼村的情况,③王启梁:《内生性村落社会秩序是如何形成的?》,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8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41-73页。相反的情况则是另一个村落个案。④王启梁:《传统法文化的断裂与现代法治的缺失》,《思想战线》2001年第5期。
即使在最为复杂和让人困扰的自我世界中,人们也在宗教系统中创造了关于生命意义的解释,人们得以借此慰藉了心灵,安抚自我,而宗教也创造出一种社会控制——因为自我事实上存在于群体之中。对于民间生活来讲,非正式社会控制就是因源自于宗教、艺术等的那一部分使人们能够“克服自己在感情、心理、认知上的种种困难与挫折,忧虑与不安”。⑤李亦园:《人类的视野》,第101页。在曼村的关于琵琶鬼的个案中,我们看到了驱赶琵琶鬼的社会控制正是人们解释疾病、克服恐惧、恢复秩序的方式(当然,这样的方式是一种悲剧)。⑥王启梁:《宗教作为社会控制与村落秩序及法律运作的关联》,载谢晖、陈金钊主编:《民间法》第八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112页。我们在地方性的日常生活中并不难观察到,围绕着人的生、老、病、死,带有宗教性的禁忌、仪式等非正式社会控制或多或少地安抚了人们的恐惧,秩序因此能够得到维护。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由于非正式社会控制的不同,不同的群体也表现出不同的解决之道。人类必须依靠物质的和社会的环境才能生存。我们的行为影响着周围的生命存在,而我们的行为乃依赖于我们所思考的东西、我们的价值和信仰体系。群体生活中孕育出来的对周遭世界包括我们所生活的自然界的认识演变为一种宇宙观,决定着我们怎样行动,决定了我们如何对待自然界,不同的宇宙观导致了对待自然界不同的态度,并且体现为规则和社会控制。
不同的文化背后的宇宙观决定了不同的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决定了我们在自然中的不同位置和生存方式,决定了人与自然是敌人还是朋友关系,也决定了我们遇到问题时的不同处理方式。我曾考察过西双版纳的一些少数民族村寨,例如傣族寨子周围的“竜林”(傣族人民埋葬祖先的地方,是神圣的地方,受世代居民的保护)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①高立士:《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何昌邑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31-43页。又如,西双版纳的各世居民族有各种保护森林、动物的禁忌和风俗。直到解放前,西双版纳仍然保留大量的森林和野生动物,这与各民族的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正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保护了生物的多样性。②张晓辉、王启梁:《民族自治地方的生态环境保护》,《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 7期。相似的情况是,云南的哈尼族地区围绕着梯田的耕种创造了复杂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套生活方式由非正式的规范和社会控制来表现和维系着。而在我们受到工业化影响的宇宙观中,常常把人和事物、自然看做相互分离而非相互依赖的。所谓现代科学的、“破碎的”宇宙观无法给予一个整合的世界模式,将人类与生态系统都包括在其中并赋予价值,它对生与死的自然进程漠不关心。在这样的宇宙观指导下,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在一种发展主义的鼓动下失去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那些曾经保护着水、森林的规范死亡了,人们选择了一种过度掠夺自然的生活方式。③个案见朱晓阳:《黑地·病地·失地》,《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基层社会的情况比过去要复杂得多,规范形式也随之越来越多元化,各种规范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局面。非正式社会控制与正式社会控制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竞争的情况,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与国家法律、政策介入之前相比明显缩小,但是仍然在很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上发挥着作用。非正式社会控制的作用在于对基层社会微观秩序的建构。国家法律与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国家法与非正式的民间规范相比具有更强的普适性,国家法所表达的价值、精神也具有更多的普适性,而正是这种普适性反而使得国家法往往不适宜解决那些具有特殊性的民间生活纠纷和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无疑是一个悖论。而民间的非正式规范则与国家法不同,它源于生活,具有高度的内在性和自生自发性,解决的是特定时间、空间、人群的具体问题。在纠纷解决中,非正式规范和非正式社会控制为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和纠纷解决者提供了国家法之外的可依据的制度和规则,使纠纷的解决更适宜地方性的生活,大量的民间纠纷就是通过社会规范的运用而没有进入正式的司法程序。非正式规范和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存在不仅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帮助,它还构成了村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指导和建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作为一种与民族和地方性的想象有着重要联系的事项,非正式规范和非正式社会控制还是人们生活意义来源的重要组成,从而成为建构基层社会日常生活以及微观秩序的基本要素。因此,非正式规范和非正式社会控制保卫了地方性生活,是生活方式多样性的存在基础。
特别应该注意到,虽然基层社会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于正式社会控制和准正式社会控制的影响,受到宏观社会变革的冲击,但是非正式社会控制仍然有能力构建起地方性的特色生活,人们有一定的能力“‘融贯’不同的知识、信念并践行之”。④朱晓阳:《面向“法律的语言混乱”》,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27页。
五、讨论:多元社会控制格局、社会转型与非正式社会控制
我们可以按照国家对社会的影响力来分析规范、社会秩序的主要来源和类型,如下表:

社会与秩序类型的分类
如果我们对地方性的生活或者微观社会进行观察时,会发现A、B、C三种类型的社会都存在或曾经存在过。虽然我们能够区分出不同的微观社会受国家影响或大或小,但如文章开篇所说,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讲,已经没有所谓真正的国家法律的不入之地,我们已经注定生活在一个由多种规范和社会控制构成的立体秩序。①王启梁:《法律移植与法律多元背景下的法制危机》,《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年第 3期。不同的社会控制存在于相同的生活空间中,所谓地方性的生活也不再是不受国家影响的“不毛之地”。所以,对非正式社会控制的考察必须注意到来自国家和宏观社会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主要是 B社会,其社会秩序是一种混合型的社会秩序,在这些社会中,我们可能会观察到国家正式社会控制与来自社会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并行不悖,也可能发现两者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通过对人们的行动进行深入考察,发现不同性质的规范、社会控制存在的格局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发生互动继而形成秩序的。简单地把自生自发秩序与计划性的秩序 (经由立法等正式制度产生)进行区别,不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对社会生活的切割,多元的规范和社会控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影响着对方,甚至相互成为对方发生或存在的理由。因此,对非正式规范和非正式社会控制的考察也必须注意到,它与其他社会控制尤其与正式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避免孤立地研究和讨论非正式社会控制。地方性的秩序就是人们在多元的社会控制之间不断行动之后形成的结果。
因为社会控制机制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认可、强化、配合与相互否定、冲突、制约,它们处于动态的相互联系之中,所以不同的社会控制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中还会相互改变着对方。例如在一个村落调查中,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吸收了通行的林场、牧场的管理和使用了民间管理方式。②吕昭义、红梅主编:《门巴族——西藏错那县贡日乡调查》,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95页。
在一项关于纳西族殉情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殉情自杀在纳西族社会中是一种对抗法律、儒教、所谓正统的婚制,维护爱情和尊严的方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习俗、非正式制度。③王启梁:《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及法律失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 5期。而在一些典型的个案中,我们则看到了私力救济甚至私刑的发生,与国家法律不能有效回应村民的治安需要有直接关系。④王启梁:《为了生活使用暴力与暴力对生活的毁灭》,《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 2期。而在前引曼村个案关于社会控制的考察,可以清楚地表明曼村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大部分时候与国家的正式社会控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来自国家的正式社会控制深刻地影响着民间的生活和非正式社会控制系统的变迁。⑤王启梁:《内生性村落社会秩序是如何形成的?》,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第8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41-73页。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到,非正式社会控制的产生、形成、变化是在地方性和群体的生活中,在社会结构、文化这两个重要的维度交互作用下,经由人们的日常实践完成,而国家的正式制度是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民众日常实践的一个外在结构、是日常生活的大框架,国家正式控制是非正式社会控制产生、形成、运作和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可以把非正式社会控制看做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却不能认为这种自发、内生的秩序与国家无关。在一种多元社会控制的格局中,非正式社会控制甚至部分地是应对国家正式社会控制的产物——或冲突或互为补充,或者相互改变,或相互支持或相互规避,唯一不变的是非正式社会控制是人们在这种多元格局下寻求解决问题办法、应对生存之需的结果。
由此,我们会进一步发现,作为生存之道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脆弱性。非正式社会控制总是需要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之中,而一旦旧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发生了变化,那么非正式社会控制就会发生变化。
社会转型带来的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既有的社会结构、文化以及价值体系的瓦解,例如旧有的围绕身份关系建构起来的纠纷解决方式因为身份关系的转型而失效,而转型在当代中国正在普遍发生着。这意味着旧有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将可能失去它存在的基础,旧有的生存之道已不能适应多变的世道,旧秩序因而正在被瓦解。不足为奇,人们的生存环境、社会结构、文化系统总是在变化之中,非正式社会控制就是在这种变化中逐渐生长的。但是,过快的社会变动却使人们的实践不断发生断裂,地方性的生活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因素,社会缺乏足够的时间来培育出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①关于文化的形成过程参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第 14-15页。非正式社会控制因此难以提供出一种适应社会高速变迁的生存之道来。所以,旧秩序瓦解而新秩序不能形成,这就是社会转型时期最大的危险。
在一种多元社会控制的格局中,国家正式社会控制是我们相对能够把握的“一元”,它是一个改变秩序格局的关键变量。也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来讲,国家和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洞察那些秩序的真空地带,国家法律等正式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介入社会并提供出有效的秩序,有效地弥补社会转型带来的非正式社会控制不足的困境、帮助人们渡过这艰难的转型时代,这既是法治的任务,也是前所未有的完善法治的机遇。社会转型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制度转型、生存之道转型的过程。
-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战后中日主导产业与非主导产业的政策比较——基于产业政策史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