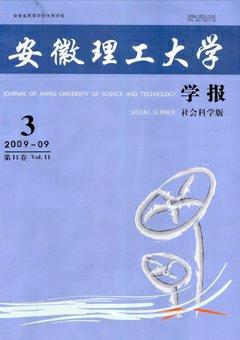历史与伦理:格非小说的叙事向度
祝亚峰
摘 要: 历史与伦理构成了格非小说叙事的核心。从早期的先锋小说,到近年来发表的 《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作品,无论文学是从历史回归修辞,还是通过叙事为历史寻 找筑居之地,他都在尝试建构历史与伦理之间的叙事张力,以打开文学探索的空间,发现未 来的主题。在历史的叙述中对人的存在、心理深度的探询,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叙事伦理取 向,坚守着一份文学创作的道德责任。
关键词:历史;伦理;叙事伦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09)03-0054-14
一、从历史回归伦理修辞
历史与伦理是小说叙事的主要层面。在一般意义上,历史泛指一切事物发生的过程,对 这一过程的记述、阐释和反思构成了所谓的“历史意识”。人类历史强大的理性力量在推动 社会进步的同时,必然会引发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与自我的对立冲突,社会发展的任 何历史时段也必然包含人存在的伦理状况及其道德意识内容。因而历史理性与人伦情感之 间的悖论构成文学历史表达永恒的主题。在传统意义上,文学历来受制于古典主义“一元 化”原则统摄,认为一切的“在场”事物的意义和价值都是这一原则的现实“复现”。文学 通过对历史的叙事能够改变自己“弱者”的形象并获得深厚的精神内涵。因此,一直以来, 历 史在文学叙事中拥有至尊的位置。但是,文学有它自己的逻辑表达方式。文学借助想象与虚 构的艺术力量,通过它的语言、形象、叙事等形式“再现”历史的种种“可能”,这种“可 能”性能够抵御历史理性的异化而保留文学自身的品质。这样文学的历史与个人经验,无论 是主体表达,还是被表达的主体,都如詹姆逊所说的形成了历史理性“与个人力比多驱动” 之间互为冲突又密切的关系。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对民族国家想象性建构,规 定了历史的现实与未来的发展目标,文学也被纳入此进程,而成为“中国现代性发展到极具 乌 托邦时期的产物”,以至于当代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以来,出现了如陈晓明分析的,一方面在 逃离“历史化”,另一方面又渴望重新“历史化”的情形[1]。这种“逃离”与 “渴望”在先 锋文学的历史文本中同样醒目,这也即是我们讨论格非小说历史与伦理叙事的逻辑起点。
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第一次设立一种文学“为自己立 法”式的现代性写作观念。他们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所谓“真实”掩盖了历史本真 的状态,所谓的“意义”不是客观先在的,不是主体自设的。“意义”生成于主体与客体相 遇时,主体对客体的“诠释”过程中。因此文学只有借语言“形式”实验来重新建构“意义 ”,而成为创作主体“我”个体性的精神形式。先锋小说由此迈开了逃离历史、意义,回归 文学语言修辞的步伐。但他们的反叛并非是集体地沉溺于“语言游戏”。他们的反叛一开始 就试图拥有一个“精神的图式”——格非小说始终执著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许多重大命题 ,如乌托邦理想、(家族)历史的颓败、社会革命实践以及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个人,尤其 是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将其折叠整合进伦理框架内,简单的故事结构,明晰的人物关系, 以艺术的形式加以处理,“而且,他还坚持了一贯的内心化视角——即对主体的个体动机, 特别是无意识世界的状况深入探察,这些无意识活动,往往是主人公命运和某些历史关节中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而这,大概是格非带有‘怀疑论‘不可知论或‘宿命论哲 学与历史观念的一部分。”[2]
格非早期的《迷舟》《敌人》很具有代表性。小说《迷舟》在萧的七天死亡之旅中, 战事与人伦纠葛缠绕,指向萧必然死亡的结局。《迷舟》中人伦关系、萧的“情爱”心理等 与即将发生的战争,小说让这二者对峙,互相渗透,使人的“性情”欲望主宰战争叙事的走 向。所谓“伦理问题根本上是人的在世性情问题。人的在世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世,每一个‘ 我在世与前人、后人、旁人的关系构成了‘我的在世的缘和故,一般认为,这就是伦理 的基本元素。……,一个人在世的生存关系、甚至更主要是受自己性情支配的,个体与自身 性情的关系,是更为根本的伦理元素——伦理的在体基础。每个人的性情都是一个随机形成 的价值感觉秩序,它决定了个人的生命感觉和态度,决定了一个人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生活 。”[3]206-207真正致萧于死亡之地的是他自己,就如格非之后的作品所指向的 人内心的“敌人” 。《敌人》同样有一个伦理叙事的框架,那场大火发生之后,留在赵氏家族每个人内心深处 的已经不仅仅是那场大火的灾难印记,而是郁积于内心深处的无名恐惧,或者说是赵家人必 然的宿命。对大火原因的的追查与这源于内心的宿命感互为纠结,派生了所谓的“敌人”;赵家人接而连三地神秘死去,“敌人”似乎无处不在,“敌人”究竟是谁?格非的叙事一 方面诱发对“真相”探询,另一方面又隐匿了真相的揭破,事实的真相变得似是而非。这种 从历史回归伦理修辞的叙事,使得历史在小说叙事中变得模糊迷离。作者真正的写作动机, 也许是要凭借叙述策略的刻意颠覆传统文学历史的“同一性”,而彰显“个人力比多驱动” 被压抑的主题。
格非在展示了人混乱不堪的生存状态,人的精神沉沦欲望横流以及人遭遇种种挫折的 同时,在客观上实现了如韦伯所描述的那种现代性的——脱魅。这种“脱魅”沿着两个方面 展开,一是叙述人的感觉方式不断地渗透历史,“历史”在叙述者与之对话的语境中被陈述 ,“历史事实”因此被化解为历史的“碎片”;二是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形成如评论界一再 提到的格非的“空缺”“断裂”“偶然”等技巧而将历史“脱魅”式写作推向极致。历 史之所以如此微妙,不堪一击,皆因在历史的重压下,个人自我的漂浮感与无所归依,历史 常常表现为“人无法战胜自我”的悲剧。加上格非原本带有的“怀疑论”“不可知论”和 “宿命论”的哲学与历史观,使得其人物始终受“偶然性”“宿命”等因素的钳制 ,模糊了作者真正的叙事动机,小说因此弥漫着一种虚无主义的气味。
二、为历史寻找筑居之地
先锋文学在80年代后期“集体胜利大逃亡”,其原因多有评论,我们关心的是先锋文学 经历了对历史的“脱魅”式写作,如何调整历史与其他诸要素之间的关系,重新聚焦于“历 史”。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其实是一种“叙事行为”,所谓的“历史真实”是不可“还原 ”的,“因此任何‘事件,在进入一个‘历史叙述的结构之中时,实际上已经变成了‘ 一个扩展了的隐喻,它所完成的‘对历史的叙述,实际上是‘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 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4]历史所谓“真 实”“本 质”其实都是被阐释出来的。历史的“真实”就是“虚构”,“事件”进入历史叙述之后, 就成为重新编码的符号,服务于主题的“事件”。
格非及先锋文学的历史解读与新历史主义相通之处在于,都将“叙事”作为历史建构的 手段。他从“存在主义者”立场理解人与历史的关系,历史是不可知的、虚妄的,只有人才 是历史存在的主体,如克尔凯戈尔所说的“那个个人”。
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选择了一个典型的存在主义式角度切入历史——“荒诞 境遇”——秀米个人的成长史 ,以及潭功达、姚佩佩的“孤绝境遇”。“荒诞”与“孤绝 ”境遇,正是现代性社会人与历史必然冲突的表征,也导致人在历史境遇中必然的分裂和失 败。《人面桃花》中父亲陆侃的“桃花源”,张季元的“大同世界”以及王观澄的“花家 舍”,与秀米成长历经的每一时段,并非仅仅是背景构成,而是渗入其生命血液之中的,生 成为她生命的一种冲动;父亲的“疯狂”“出走”与秀米少女初潮来临并置,宿命般规定 了秀米以后的人生道路;张季元的“革命”启蒙与“性爱”诱惑同时拥塞进秀米纷乱的内心 世界。青春期的萌动,父亲的神秘消失、“瓦釜”,张季元的死亡、那本“日记”等如神秘 的咒符在“性”与“精神”两方面打开秀米的视界。“革命”“乌托邦”这些巨型概念就 这样融入秀米“私人痛苦”之中。人尤其是女人,往往只是为了些微感情触动,抛出整个 生命,在情感的某一尖锐点上一再地走失。与其说,秀米爱上了张季元,不如说她迷恋上了 张季元“不属于尘世的那张脸”以及他“胡思乱想的念头”。对尘世的厌倦,无法排解的忧 伤,通过秀米出嫁遭劫,最终完成了她的“成人”与步入“革命”之途的主体性生成“仪式 ”。紧接着“花家舍”土匪之间的火并,让秀米的人生之路迅疾转向。之后,秀米建立“普 济堂”,本着规训人心的旨意实现她的“普济堂”式的乌托邦理想。詹姆逊认为,现实主 义 对于因沿袭而成定规的有关生活的假定进行了一种“系统的潜在损毁和非神秘化,一种还圣 为俗的‘解码工作。而现代主义则正好相反”[5]。《山河入梦》剥离了格非 一贯地先 锋式的技术手法,设立全知叙述视角,线形的故事模式,日常经验的叙写,从外在故事到人 物内心描摹都显“还俗”面相。故事的开放性,朴素性及自然性,都试图对中国传统现实主 义所谓本质规律揭示的目的论写作构成反动和某种矫正。一方面,20世纪50~60年代,中 国社会乌托邦时代的农村合作化、兴修水利、安装电灯等“大跃进”式的政府行为构成特定 的历史情境;另一方面,小说通过主人公潭功达与白小娴、姚佩佩、张金芳、小邵等几位女 性的关系,特别是潭功达与姚佩佩从相恋到悲剧性结局,将那一时代乌托邦激情,置换为主 人公内心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乌托邦情结。社会的一体化将足够的规约加诸于个人,让人在 层层文化的密布中谨慎从事,但凡你要保留一点私人性,就会面临毁灭。轰轰烈烈 的时代对于逃亡中的姚佩佩来说是彻骨的寒冷,导致她最后的毁灭 。
《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写了革命乌托邦实践及个人乌托邦梦想,无论是社会性 的还是个人化的都以失败告终。一方面,《人面桃花》中陆侃、张季元、王观澄以及陆秀 米所构想的“乌托邦”涵盖了中国人文传统的、西式启蒙的以及民间文化要义。传统中国社 会乌托邦“救世”方案无非是逃离乱世及救治人心两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想象 的、神话的、诗性的特点显著,它常常与人间事务交叉渗透,不分彼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想象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相混淆,甚至以浪漫畅想取代生活常识。按乌托邦的完美预想, 人类社会最终要建立一元的世界,即审美诗性的世界。“但是,在距离最终目的的漫长过 程中,区分却是必须的,它是人类理性认识的一次飞跃,同时是现代立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没有这场区分,人类将走不出神话思维美妙却空洞的误区,无法克服道德理想嬗变为嗜血 的悲剧。”[6]196另一方面,历史上的灾难形成固然有意识形态或体制上的根源, 但行为者的 道德意识起着更为激进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现实中许多的恶行,都是在一个光明堂 皇的口号下进行的。且不说,陆侃张口闭口“桃花源”,在丁树则眼里,“说来说去,还是 贪恋官场声色。你看他,这么一把年纪,还要养个雪白粉嫩的妓女在家做甚?”当秀米看了 张季元死后留下的不乏“令人难看”的日记,感叹到:“张季元呀张季元,你张口革命,闭 口大同,满纸的忧世伤世,壮怀激烈,原来骨子里你也是一个色狼呀。”如果真的实现了“ 大同”,他们颁布的《十杀令》并且实施,就足以制造一场人间灾难。即便如秀米品性纯正 坚韧,她的“普济堂”也只能成为一帮乌合之众聚集之地,她奉行的道德纯洁结果导致是道 德“恐怖”。《山河入梦》在20世纪50年代革命化的大背景下,当权者种种的劣迹足以说明 :人类的良知所给定的某些道德底线,是决不能以高尚的口号“革命”“正义”“道德 ”等理由来突破的,而以“理想主义”为说辞就为更荒唐。事实上,能够构成“理想”基础 的意识形态与信仰,无论基督教、新教,人文主义还是无神论者的社会主义,都包含着人 类普遍的,如正义、良知、仁爱等价值内涵,包括对个人性最基本的尊重,否则就不会有持 久的精神魅力。格非通过他的小说清理了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内心那种乌托邦冲动以及这种 冲动付著于实践之后所遭遇的一系列难题和困境。
三、叙事伦理:历史与伦理的纬度
人类的生活简约地可以由两部分构成,精神(心理)的和现实的,或者说,隐喻的与常 识的。前者,更多的关涉宗教、神话、审美及诗性,注重个人的幻想臆测、原创性独白,及 想象力的绝对自由;后者,涉及国家建制、理性与科学、法律与经济,及具普适性的准则规 范等[6]196。乌托邦幻想/革命实践原本属于隐喻与常识不同领域,但是由于乌托 邦内涵着人类 改变不幸的处境,要用正义来安排一个新的世界的愿望。这一人类古老的关于被拯救的神话 ,就在不同时代被注入新的活力,而演绎出形色各一的世俗化的乌托邦“革命”实践的版本 。格非历史叙述是要恢复历史情境个人的生命时间,感受个人切身的疼痛感。在历史的叙述 中对人的存在、心理深度的探询,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叙事伦理取向,坚守着一份文学创作 的道德责任。
通常对历史的叙述必然以时间的进程为基本依托,历史的“线型”发展携带着重大事件 ,诸如民族迁徙、异族战争、政权更迭、人民革命等,构成历史的宏大叙述基本元素。但任 何的历史都是个人的历史,历史“线形”存在与个人的“此在”的空间性存在既互为关联, 又具不同的意义内涵。传统的乌托邦“革命叙事”是以历史的线型发展来取代了个体生命的 “此在”。又因为革命的意义是建立在对未来的乌托邦承诺之上的,关于革命的想象与结局 的圆满对接,而使得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封闭在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中,取消了革命过程性的 时间,定格了革命发生的意义及其中人存在的意义。这一历史时间的演绎过程充斥了“ 革命”“胜利”“牺牲”等乌托邦概念,个人生命时间置于此历史时间结构中,就消融 了自身的个体存在的意义。格非小说的叙事伦理体现在对历史“时间”的重新安排上,他特 别地观照在线形的历史进程与个人伦理空间性时流中,人自我存在可能的选择与状态,“还 原”人存在的基本伦理属性。由此打通了历史时间与个体生命时间的阻隔。它的基本叙事策 略是隐喻和写实。
小说《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一路写来,将对“大历史”的道德责难替换成对人 物命运、个体的不幸遭遇、“私人痛苦”。那么“私人痛苦”是“革命”“乌托邦”异化 人性的结果,还是个人的在体性问题?或者说,秀米的“私人痛苦”是她“革命”必然酵母 ?其实个人的情感受伤在任何时代都是普遍的现象,生活不是按照理性原则或个人美好意愿 设计的。个体的随机性存在,各种意外的事件拼合,甚或必然地使得伤害事件频繁 发生。格非似乎并不在意一定要对历史追根溯源,批判有加。他的历史叙事,如米 兰•昆德拉谈到 小说存在的意义时说的“生活世界中总得有某种思想要理解人的具体生活,小说就是这样的 思想,他甘愿与一个人的生命厮守在一起,……小说询问什么是个人奇遇、探究心灵 的内在 事件、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会的历史禁锢、触摸鲜为人知的日常角 落的泥 土、捕捉无法捕捉的过去时刻或现在时刻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状,等等。”[3]1 32《人面 桃花》《山河入梦》中的人物,他们是真实的个人,拥有自己独特的个人经验和生活边界 。当秀米最终从长长的“梦”中醒来,发觉“原来,这些最最平常的琐事在记忆中竟然那样 亲切可感,不容辩驳。一件事会牵出另一件事,无穷无尽,深不可测。而且,她并 不知道, 哪一个细小的片刻会触动她的柔软的心房,让她脸红气喘,泪水涟涟。”从这个角度说,《 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描述了中国人在那一历史时期的集体性丧失,但它却为个人寻觅 到一条抵达幸福和慰藉的路径。对于格非与读者来说,“文学话语既不是一种拯救的信仰、 教义,也不是任何一种意识哲学的理论及其说服力。它带来的是一些不可重复的、 瞬间的、 个人化的、经验的、可以感觉的意义。……用既非信仰的、也非知识理性所体验到的意义感 的方式,当然既不能被看作一种理论,一种教条,也不能看作一种正在不断积累的、永恒的 知识。它意味着在文学话语中探索一种个人的修辞学,一条道路,把思想的陈词滥调的葬仪 中复活为思想着的肉身的语言,它是思想,又是批评,然而又超越了这一点……。”[ 7]
参考文献:
[1] 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2.
[2] 张清华.《山河入梦》与格非近年的创作[J].文艺争鸣,2008(4):121-124 .
[3]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
[4]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3.
[5]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小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61.
[6] 艾云.隐喻与常识:空间的区分[J].大家,1998(3):196.
[7] 耿占春.言语活动的想象物[J].大家,1998(3):194.
[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