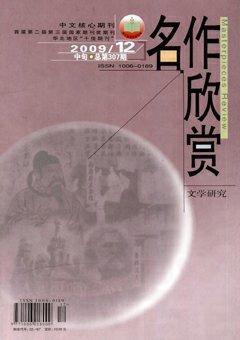论冯至《昨日之歌》的新诗史意义
黄 玲
关键词:冯至 《昨日之歌》 节制 哲思
摘 要:1920年代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在现代新诗史上的意义,与其说是为诗人日后《十四行集》的成功作了注脚,不如说是在白话新诗创作初期,在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从形式上为新诗重建规范时,冯至以其曲折幽婉的情感表达和冷峻深沉的哲思凝想,为探索中的白话新诗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
一
《昨日之歌》是冯至在1927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收录了诗人在1921年至1926年间所写52首诗歌。这些诗都写在冯至21岁以前,那时候诗人还没有从北京大学毕业,因此完全属于青春少作。另外,由于诗人自己对于这些早年的诗歌曾作过出这样的评价:“诗里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愁,如果说它们还有一点意义,那就是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的苦闷。”①因此,《昨日之歌》里那些只写“狭窄的情感”和“个人的哀愁”的青春少作长期以来很少被人重视。事实上,冯至上述这段话是上世纪50年代说的,这样说除了自谦之外也有当时文化环境的原因,因此决不是盖棺之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这本诗集,研究也渐渐走向深入。但综合起来我们却发现,这些研究一般都在以下三种框架内论述:一种是对《昨日之歌》内的个别名篇(如《蛇》《我是一条小河》等)进行解读;第二种是在考察诗人一生的诗歌创作时,作为第一个创作阶段的主要作品谈及,这种情况下论者的讨论对象除了《昨日之歌》,还会有冯至的另一本诗集《北游及其他》;第三种是在研究冯至1940年代能代表其诗歌创作高度的成熟之作《十四行集》后,追本溯源时才谈到《昨日之歌》的,所论一般都带上了寻找证明的色彩。站在冯至一生的诗歌创作这条纵线上考察《昨日之歌》,得到的结论无非是为冯至日后能取得更大的成功找到一个注脚,但在这些研究中《昨日之歌》从未真正独立过。
本文的研究视角和问题的提出正是基于上述诸种研究的不足,我们准备换一种视角,把这本诗集放在1920年代的诗坛上做一个横向考察:《昨日之歌》自身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它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被谈论?这样做的意义与价值又在哪里?
二
让我们首先回到最初的阅读感受。读冯至的《昨日之歌》,我们会觉得它们没有胡适的通俗晓畅,也没有郭沫若的激情澎湃;没有徐志摩的浓烈浪漫,也没有闻一多的形神整饬;没有“小诗”的清新唯美,也没有象征派的鬼魅跳荡。有的是什么?是令人回味的郁结惆怅。
撇开上述感性的描述,我们要追问:这个集子里的诗所呈现的相异于同一时期其他诗歌的地方在哪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读者郁结惆怅的阅读体验和进一步回味的冲动?我以为是曲折幽婉的情感表达和冷峻深沉的哲思凝想。
《昨日之歌》创作的年代,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刚过,文化思想的启蒙使反抗封建束缚,争取个性的自由和解放成为时代要求。在这个旧秩序被打破的奔放时代,似乎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一腔澎湃的激情。体现在文学上,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仿佛胸中强烈的情感来不及选择表达的方式就已喷涌而出。具体到诗歌创作领域,“诗体大解放”也让诗人们在形式上甩去了无数桎梏,情感表达变得直白而浅露。了解这样的背景就会发现,《昨日之歌》与当时流行的诗风有多么大的不同!
《昨日之歌》中最多的就是诗人借日常生活事象来写自己的生存感觉、生命欲望。比如集中的第一首《绿衣人》,一开始我们会认为是写邮递员,读到最后才猛然发现,其实它不是写邮递员而是写诗人内心那种“没有花,没有光,没有爱”②的生存感觉,写那种对不可知命运的惊悚感。这首诗是冯至写诗的开端,虽然诗人曾自谦地说:“这不能说是一个好的开端。这个开端不是健康的,它不能预示什么远大的前途。”{3}但它确实预示着冯至诗歌创作中一个最大的特色。集中的《一颗明珠》《暮雨》《楼上》《小艇》《瞽者的暗示》《你倚着楼窗……》等把生命的孤独感、寂寥感写得非常真切细微;《夜深了》《初夏杂句》《残年》《绿树外》《雨夜》等又把人生的凄婉哀伤刻画得丝丝入扣;《在海水浴场》比较隐晦地书写了蛰伏在生命深处的真实欲望;《歌女》《“晚报”》等把诗人内心的落寞与酸苦写在了字里行间。这些诗歌看似在写现实生活某些事情或物象,事实上都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事象,曲折地表达出诗人内心形而上的生存感觉和生命体验,而不是事象本身。
《昨日之歌》中还有一些诗歌是写爱情和友谊的。《问》通过玫瑰花的开谢写爱情面对岁月的无奈,《满天星光》用奇特丰富的想象写诗人对于琴瑟和谐、超凡脱俗的爱情的渴望。《怀——》《秋千架上》《春的歌》《在郊原》《默》《我愿意听……》等诗中,爱情都是被以非常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爱情诗中最经典的当属《蛇》与《我是一条小河》。前者把寂寞比作蛇,爱情的热烈并没有通过深情的表白来实现,而是隐藏在“冰冷地没有言语”的背后,唯其如此更显热烈;后者既写出了两情相悦、心心相印的缠绵浪漫,又写出了爱情被现实摧毁后浓郁的感伤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命的孤独感与空茫感。“冯至的爱情诗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避免自我感情的直接抒发,不满足于一般生活层面上的爱的表白,而是将爱情的种种思绪注入一种富于哲理性的思考,在爱情的冷却与热烈,绝望与希望的辩证关系中,来传达复杂的内在情感。”{4}《别K.》《怀Y.兄》《遥遥》《孤云》《如果你……》等写友谊的诗,其情感表达也非常委婉曲折。
1920年代,配合着扩大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和语言革命自身的要求,诗坛上弥漫着的是对通俗的追求。《昨日之歌》与此不同,冯至并不刻意追求通俗,而是以冷峻深沉的哲思凝想在当时的诗坛上独树一帜。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里批评“沉钟社”青年道:“玄发朱颜,低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乍一看,冯至的《昨日之歌》正中箭靶,因为这些冯至在16至21岁写下的年少之作,抒写的却是无尽的哀愁。但仔细读过《昨日之歌》的人就会发现,其中的孤寂与愁苦并不是一般少年的多愁善感,而是一个早慧少年的冷峻哲思。
首先,《昨日之歌》中爱情诗的基调都是悲剧性的。“续了又断了/是我的琴弦,/我放下又拾起/是你的眉盼——”(《在郊原》)《昨日之歌》中有不少爱情诗,写的内容往往不是爱的欢悦,不是爱的忧愁,不是多愁善感的痛苦,也不是春风秋月的无病呻吟。它们在表达青春年少的诗人对美丽爱情的憧憬与歌唱的同时,也流露出了诗人内心一种超出年龄的深刻的悲观。《问》中爱在时间中凋零;《秋千架上》爱像落日一般在暮霭里销沉,留下冷清清一片;《春的歌》当“我”“想为她唱些‘春的歌,无奈已近暮春的时候!”《我是一条小河》美丽的爱情被无情的现实“吹折了花冠,击碎了裙裳!”最后如同彩霞般幻散……卷下4首叙事诗,其中《吹箫人》《帷幔》《蚕马》等3首都是以民间爱情故事为原型的。《吹箫人》表现了艺术与爱情不能共存的悖论,《帷幔》与《蚕马》也是两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总之,无论是抒情诗的直接表现对爱情的悲观性体验,还是叙事诗对民间爱情故事的悲剧性演绎,都使冯至的爱情诗带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诗人以哲人般清醒的理智,冷静地说出自己的思考,它不会让我们感到欢欣,但也许更接近真实。
其次,《昨日之歌》有不少诗歌表现了一种人生的空茫感。诗人在《夜步》中忧伤地喟叹:“烛光啊,你永久苍苍,/星光啊,你永久茫茫:/我永久从这夜色中/拾来些空虚的惆怅!”在《永久》中追问:“我追寻我的永久的,/我的永久的可是你?/但是我怎样的走进呀,/永久里,永久里?”在《风夜》中静思被岁月掩埋的生命热情……个体生命莫名其妙地被置于苍茫的时空,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更不能自己安排方向。在无常的开始与结束、相信与绝望之间,一切都得不到解释,那种茫然而又无助的生命体验使冯至诗中还经常出现秋天与死亡的主题。在人生的战场上,诗人感到一种“天大的疲倦”,便唱出“为了死亡,为了秋天!”(《秋战》)诗中说一面“黑色的旗帜在面前飘荡”,这“黑色的旗帜”,就是“死”。如果说《秋战》多少还带着人间的苦闷引起的社会层面的思考的话,《在阴影中》则完全上升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它是在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灵魂向神灵发出的呼告。《“最后之歌”》这首诗叙述了他对于母亲死亡时的记忆和从儿时开始的隐藏于自己内心的深重的悲哀,其中生与死的主题,不再是亲人的经历和幻象的表达,而是自己的个人生命的存在和追求的一种方式。
另外,《昨日之歌》里的诗之所以没有在人生苍凉而无奈的空茫感中沦于灰色,是因为一种内在的追求,一种对终极的信赖,整部诗集也因此充满了精神张力。“灿乱的银花,/在晴朗的天空飘散;/黄金的阳光,/把屋顶树枝染遍。/驯美的白鸽儿/来自神的身旁,/它们引示我翘望着/迷的故乡。”(《归去》)这首写于18岁的诗中,冯至就昭告世人他的灵魂里有一个不变的守望,那个“迷的故乡”将是他一生的家园。他可以怀疑一切,他可以对一切悲观,但他的灵魂总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有时是“超脱了世上的荣华,同那些浮浅的悲哀”的琴瑟和谐的爱情(《满天星光》),有时是我“深深藏在怀里”的“一颗明珠”(《一颗明珠》),有时是深夜神能引我到的那个地方(《夜深了》),有时是姑娘面庞上摘下的“永不凋残的花朵”(《工作》),有时诗人干脆就把它叫做“永久”(《永久》)……当敏感而早慧的诗人把思绪牵向追问永恒时,一切都具有了形而上的哲学意味。
三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把冯至的《昨日之歌》放在1920年代的诗坛上做横向考察,其独特之处正在于曲折幽婉的情感表达和冷峻深沉的哲思凝想。对于前者,也许是诗人一种有意识的追求,而后者则更多的是诗人的个性气质使然,冯至本人也未必自觉。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其造成的客观效果就是:这两者的结合使冯至的诗风在当时的诗坛上令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昨日之歌》所呈现的诗风又无意中暗合了白话新诗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自古以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直是我们判断诗歌好坏的一个基本标准。换句话说,节制一向是诗歌艺术的基本要求。莱辛曾指出,艺术最美妙的时刻永远是到达顶点前的“顷刻”{5},因为一旦将情感推至顶点,就再也无路可走,前进也就意味着下滑。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优秀之作基本上都符合这样的审美范畴,再热烈的情感表达也要受押韵和平仄的限制。但自从现代的白话新诗出现后,诗歌在摆脱了语言和形式上的限制后,其情感表达的内在束缚机制也一同被抛弃了。另外,白话新诗出现的时代氛围使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诗人更是奔放恣肆、激情飞扬,郭沫若的《女神》集中体现了这种超越一切的张扬心态。
精神的张扬固然体现了被启蒙了的一代人的兴奋与豪情,但具体表现在诗歌中未免失于表达的直白与情感的歇斯底里。《女神》时代过后不久,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就重新提出从形式上对白话新诗进行规范的努力,这正是对现代白话新诗在完全解除韵律束缚后艺术性受到很大损害的一种反拨。至此,白话新诗才结束了初创期毫无规范的众声喧哗,从而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薄薄的一册《昨日之歌》,里面当然不是篇篇精品,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它都不能跟冯至日后的《十四行集》相比。它的意义,不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多少篇经典的白话诗歌,而在于在上述的新诗发展境遇中,它参与了这场对新诗发展方向进行反拨的努力。但与徐志摩、闻一多从形式上入手不同,冯至是从诗歌的表达方式与表现内容等更内在的层面实现了诗歌表达的节制与规范,通过曲折幽婉的情感表达和冷峻深沉的哲思凝想使诗歌形成一种内敛的风格和诗意的张力,这无疑给当时的白话诗坛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范式。还要强调的是,冯至把哲学思考带进白话诗歌,使它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新诗”,更是给新诗的发展内在地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
作者简介:黄玲,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①②③ 冯至:《冯至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第132页,第131页。
④ 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国里的哲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42页。
⑤ 莱辛:《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第18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