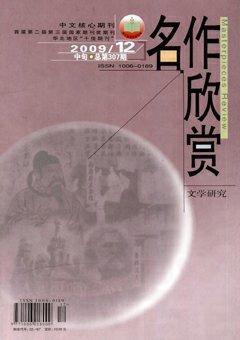美幻的迷梦与奇诡的异景
关键词:《野草》 色彩搭配 意象
摘 要:鲁迅在作品《野草》中,多处运用丰富的色彩搭配意象来表达独特的生命情怀和人生感受,在《好的故事》中,鲁迅以和谐的色彩配合营造了神往中的美的意境,而在《死火》中则以冲突性的对比色彩形成奇诡的异景来表达痛苦、激越的现实生命感受,对比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色彩搭配意象,能更真切地理解鲁迅的精神世界和生命哲学。
鲁迅在作品《野草》中,多处运用丰富的色彩搭配意象来表达独特的生命情怀和人生感受,这些色彩搭配各有意味指涉。一般来说,在作品通过色彩搭配达到情绪表达和情感暗示主要有两种方法,即色彩的调和与色彩的对比。前者表现为强调色彩的单纯和统一,而后者通过色相对比强调色彩的对立,从而达到具有心理冲击力的视觉效果,这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多有表现。如杜甫的《梦李白》:“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青”“黑”两色的素色协调、配合,不仅准确地描绘出自然景色,还把“魂来”“魂返”的凄凉、阴森气氛烘托尽致,暗示了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李白的悲剧命运,将诗人的忧思表现得逼真感人;又如白居易《问刘十九》诗中:“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红泥”与“绿蚁”相衬托,室内光彩与晚雪欲来相对比,将友人相聚的美好纵情倾泻而出。在《忆江南》中,“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将朝日东升、霞光万道、灿艳江花与绿树碧江并置,在对比辉映中跃动着充满生命力的江南春光美景。
《野草》中,鲁迅也运用了神奇的色彩想象来表情达意,他创造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在《好的故事》中,是以和谐的色彩配合营造了神往中的美的意境,而在《死火》中则以冲突性的对比色彩形成奇诡的异景来表达痛苦、激越的现实生命感受,对比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色彩搭配意象,能更真切地理解鲁迅的精神世界和生命哲学。
一、迷蒙的梦幻:和谐的色彩意象
鲁迅在《好的故事》中设置一种和谐的色彩意象来表现理想中的美好迷梦世界:
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流动的“云锦”是幻境中的幻景,美好的色彩黏着交融,在鲜艳、流丽的绚烂中,除了朦胧和陶醉,再没有任何别的清晰感觉了。“在睡觉的时候,人的下意识下降到了一种较低的水平,在这水平上,生活的情景并不是以抽象的概念呈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含义丰富的形象呈现出来的。睡觉在所有的人身上唤醒的创造性想象力,都会使人惊叹不止;而艺术家进行艺术创造时,也正是依靠了这种潜伏在深层意识中的绘画语言能力。”{1}鲁迅将梦中潜意识中的美好境界以神妙的色彩寓示出来,不很清晰,却达到了极致的心灵虚幻之美,而这种美在文本中还在进一步的渲染和铺排中延伸: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
此情此景完全是一幅光色交汇、流光溢彩的印象派画作。鲁迅在创作《野草》期间,阅读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因此《野草》的创作深受其象征主义风格影响。这里,鲁迅运用绘画的诗意美,以诸多物象绚丽、柔和的色彩配合激起视觉想象的回响,呈现出一个充满迷幻色彩的梦境。于是,“那些流动的蓝、黄、红、棕,一片阴影,一条直线,一团浓重的色块,正是这一切使我们注目神往,也正是这一切控制着造型美激起的想象。”{2}
这篇《好的故事》通篇都荡漾着梦幻般的色彩描写,也因此在鲁迅文本中成为独异的一篇:
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剌奔迸的红锦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在一瞬间,他们又将退缩了。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伸长,就要织进塔,村女,狗、茅屋,云里去。
为了表现梦境的特点,鲁迅除了运用色彩意象进行迷幻般的绚丽敷色,同时还利用了绘画的构图原理。一般来说,艺术家总要设法使一幅画或者一个式样的底部看上去重一些,也就是说,要使重心降低一些。而且,在风景画中,人物、地面上的动物以及它们周围的事物——建筑、田野、树林和发生的事件,大都集中在画的下半部,而上部往往是空旷的天空。尤其当需要现实主义地再现坚实的物体时,画家和雕塑家都是采用降低重心的方式构图,从而使自己的作品与物理空间的非对称性相一致。而当物体都似乎悬浮在半空之中,不与任何中心部位发生联系时,这种构图,就削弱了人世生活的重要性。它说明,作者已经从物质现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3}鲁迅摈弃空间感的细致描述,给我们一个堆积的色彩世界,通过梦幻般的色彩铺陈,使悬浮的色彩与现实人生产生了巨大的疏离感,向我们展示了鲁迅心中美好彼岸的缤纷景象。鲁迅通过无数细微的光谱色彩的组合达到完整、圆满的色彩世界,那充满丰富生命力的色彩通过无数玲珑的细节展示出来,它所产生的效果不是色彩之间的冲突,而是交融和谐。以精神分析派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观点看来,梦是白天受到压抑的愿望在夜晚得到了释放,鲁迅通过诗化的色彩朦胧地表达了心底的希望,勾画了一个完美、极致的色彩情境,在静谧、迷蒙中,这情境中每一抹色彩也变得意味深长。
二、奇诡的异景:冲突的色彩意象
《好的故事》通过美好的色彩搭配景象追念朦胧中的理想境界,以极致的美感诠释了鲁迅心底的一分情愫。然而从梦境中醒来、面对现实世界的不堪和自我精神世界的痛苦,《野草》的色彩搭配意象呈现出曼妙之感、和谐之意少,而紧张之情、奇兀之景多,这些奇诡、冲突的色彩搭配中还常常透露着浓烈的不安情绪和沉重意味。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一个人看到什么,完全要取决于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他对什么感兴趣,他过去的经验以及他怎样取决自己的注意角度。”{4}因此,这类冲突的色彩配合意象正是鲁迅充满伤痛的人生况味的象征,其间熔铸着鲁迅独特的生命哲学,因此同样也是鲁迅的情感抱慰,《死火》即是其中的代表:
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动摇,全体结冰,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
文中,鲁迅选择三种对比强烈、映照鲜明又相互难以协调的颜色——红、黑、白三色进行搭配,使“死火”的境界,在冲突性色彩、形影的交相辉映、互涉变幻中形成奇诡的异景。色彩理论认为,“某种混合色彩的表现性的大小{5},主要不是取决于其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色彩本身,而是取决于这种主要色彩所遭受到的‘苦恼的大小”,即某一种色彩向另一种色彩接近,两者相互影响所导致的色彩张力,如果两种色彩的色相、色度对比鲜明,互为矛盾,则会带给人强烈的心里激荡。在《死火》中,物象色彩发生着奇兀的改变,“红”“黑”“白”三种色块的大小不断变幻,色彩间相互侵犯,色彩遭受的“苦恼”程度被逐步强化,画面积蕴的紧张度也随之不断上升,最终达到情感喷发、力量充溢的极致效果,这恰是文本所表达的鲁迅内心的对立矛盾——“希望与绝望的这个两极矛盾”{6},和他以绝大的悲壮性格反抗绝望的心理和他生命哲学的诗化反映。死火是冻灭的热情,它选择“烧完”而把“我”救出冰谷,是一种富有启发力的象征物,它以富有张力、反复映射的动感色彩形象,和其所指涉的深邃思想意象交迭在一起,结晶为独特的艺术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死火》是鲁迅在1919年所做散文诗《火的冰》基础上的一次艺术再创造,在《火的冰》中作者写道:
流动的火,是熔化的珊瑚吗?/中间有些绿白,像珊瑚的心,浑身通红,像珊瑚的肉。外层带些黑,是珊瑚焦了。/好是好呵,可惜拿了要烫手。/遇着说不出的冷,火便结了冰了。/中间有些绿白,像珊瑚的心,浑身通红,像珊瑚的肉,外层带些黑,也还是珊瑚焦了。
在多年后鲁迅重新文本再创造、写作《死火》时,他将“绿白的心”删去,因为色彩的繁复会消解感觉注意力,其色度还具有调和性,会降低色彩“苦恼”的程度。改后,色彩搭配虽然较前显得单一了,但恰恰是单纯色彩的反复交迭使色彩意象和旨味更加鲜明,更加得到强化了。透明而炽艳、激荡而骇人的色彩搭配美与“死火”虽冷尤热的内在痛感合二为一,达到情感迸发的极点,蕴藏着巨大的力之“势”,恰是心里抱着“遇着说不出的冷”而结冻了的“火”之“火的冰的人”自知的生命况味。因此,鲁迅在色彩上删繁就简,是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深化,更突出了色彩的强度,从而增加了痛的深度。
鲁迅对“黑”、“红”配合引起的强力美感一直情有独钟,偏爱以红色的热烈、黑色的冷寂来突出自我的灵魂世界,具有强烈的艺术独创力,在作品中多有体现。鲁迅成长于古越文化的浸润之中,它铸就了鲁迅人格、思想和艺术之根,成年鲁迅多次引用王思任的话说明故乡的历史文化传统——“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并一再表示:“身为越人,未忘斯义”,鲁迅的个性之中就充溢着这种古越“浙东性”的剑气。在《野草·死火》中,鲁迅说:“当我幼小的时候,本就爱看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因此鲁迅写出这样大气魄、激切而浓烈的色彩图景其实是其灵魂的本质使然。
鲁迅曾经明白地告诉别人,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这些哲学是“韧性战斗的哲学”、“反抗绝望的哲学”、“向麻木复仇的哲学”。所以,使用冲突性的对比色彩搭配意象正是鲁迅生命哲学的视觉呈现。鲁迅对色彩的独特感知方式和其色彩想象凝结着创作主体的思考和人生体验,他以独异的色彩配合激起心灵的直觉,使审美感觉更鲜明、更炽烈,他将色的配合同激情、希望、忧惧和痛楚相联系,这些色彩因此具有了塑造精神意象的表现力,令我们在美丽、斑斓之后看到了一颗独特的心灵在怀疑与矛盾中依然执著前行。
作者简介:金禹彤,延边大学汉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③④⑤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36页。译者、出版社、版次下同。
② [美]欧文·埃德曼:《艺术与人》,任和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⑥ 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64页。
⑦ 参见拙著,《鲁迅作品绘画意象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⑧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鲁迅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4页。
⑨ 鲁迅:《书信·360210致黄苹荪》,《鲁迅全集》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