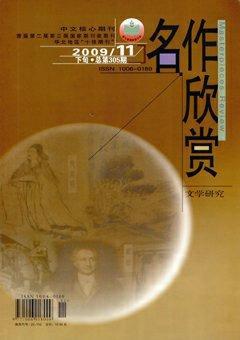帝王书画事
绘 事
帝王绘事者,以宋徽宗为最,其他仅此业余而已。
世人皆知顾恺之绘《洛神赋图》,殊不知晋明帝司马绍也画过《洛神赋图》,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录其作品多幅。明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帝皆喜绘事,尤以宣德为甚。徐沁《明画录·宸绘叙》云:“有明翰墨,莫尚于景陵(宣德),缣素点染,天机横溢,颁赐臣列,目以为荣。”今存辽宁博物馆的《万年松图》即是其为母亲祝寿而作。
乾隆帝广收天下书画名品,且设立如意馆,蓄养中西画士,每以风雅自赏,诗书几乎无日不作,偶有绘作,却也少见,盖自知眼高手低、笔力不济矣。《柳塘凫浴图》写柳塘浅草、游鸭泛水情景,说笔法拙涩、厚朴之趣可,说简约古雅、纯质无华便是勉强将就、穿凿附会了。图中一鸭鲁钝于水,水纹凝滞不畅,几石刻板于岸,孤柳僵梗其中,且干硕枝孱,畸若枯木,最是画角的题款,“春江水暖鸭先知”,出于童口,天真烂漫,无邪可人,题于此端,矫情装嫩,俗之又俗,东坡先生地下有知,也会无奈摇头矣。此句即为苏轼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中的一句。惠崇是位画僧,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称其“工画鹅雁鹭鹚,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萧洒虚旷之象”。乾隆此作是否临惠崇之本,不得而知。不过此作也收入到了《石渠宝笈》,皇上日常皆记录于起居档,况且是隆重绘事。从画面累累印玺中的“会心不远”一颗可知其自得之状。
其祖顺治也善绘事。彭孙贻《客舍偶闻》云:“世祖(顺治)幸阁中,中书盛际斯趋而过,世祖呼使前跪,熟视之,取笔画一际斯像,面如钱大,须眉毕肖,以示诸臣。”傅以渐考取状元后,顺治曾为其作《状元归去驴如飞》一图,尤为风趣。据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云:“顺治开科状元,为东昌傅相国(以渐)。相国尝扈随圣驾,骑蹇驴归行帐。上在高处眺望,摹写其形状,戏题云‘状元归去驴如飞。画幅二尺许,设色古茂。”
其实,对待帝王绘画,要求不必过高,其为闲情逸致、朝余之涉,意在陶冶性情,卑以自牧,若沉湎期间,乐此不疲,便会成为第二个徽宗了。宣和年间,徽宗越发沉溺于绘事,纵使国事蜩螗、天下纷扰,仍一叶障目,悠然忘返,朝政则全权交由太师蔡京处置。蔡京与童贯、梁师成等佞臣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因而,国之不国,朝之不朝。大兵压境之时,徽宗仍以太平为娱,大好河山终为之一毁,生民百姓,卒为之一难。鉴于此,帝王绘事,还是业余为好。术有专攻,业有专道,帝王之术,在政不在艺,正如艺人之业,在术而不在政。
书 事
旧时,毛笔乃日常所用,文事不能须臾离,书写更是等闲视之,日见不鲜。帝王披阅奏章、批复诰封、拟定谕旨、签押敕令,不论丹书墨书,皆毛笔挥就。虽如此,因炳蔚高妙、神乎其技,书写而成出类拔萃、卓尔翘楚书家者却也聊聊。
唐太宗李世民自幼戎马,舞枪弄棒多于舞文弄墨之时,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除却自身的天资聪慧、生性机敏之外,俱在奇崎独到、别出机杼之中。《晋祠铭》作于贞观晚年重游晋祠之时,李氏父子起兵太原,发迹于斯,故地宸游,旧交相逢,于垂暮间的李世民自然是思绪万端,感慨良多,或吟啸或昂扬、或喟然或沛然、或疲倦或振作、或反省或漠视,是也罢非也罢、得也罢失也罢、誉也罢毁也罢、直也罢曲也罢,皆在凝聚笔端、导之臂腕之时,当众援毫、搦管即成之间。这是幅颇具二王书风的行书作品,其点画适度,骨力劲健,起落转侧,干净利落,其结体章法,似欹反正,若断还连,疏不空洞,密不容光,后人惊呼其“字极精妙,妙绝千秋,风格秀异,若干将出匣,光芒射人”。行书介乎正书与草书间,如衣之轻装、食之便餐,为行文之惯常,手到擒来,允当省事,故凡行书精到者,必有正书的功底与草书的娴熟,《晋祠铭》的动中寓静、正而不板,足见太宗对于书法的喜好,以及在此做书的努力绝非叶公好龙,有名无实。后来,此书勒石立碑,成为自古行书入碑之第一通。也就只有帝王的襟怀、天子的气度方会有如此的逾常行为、出格表现,但帝王寻常有,有帝王器局宇量之帝王不常有,没有帝王的胆略心地、宏谟局度,何来才藻艳逸、经纶大展的帝王书法。
立碑之时,太宗又欣然写下了“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的额书,其字更为隶书飞白体。晋贤刘大鹏在《晋祠志》中赞之:“碑额九字,成为绝妙之书,飘若游云,激若惊雷,飞仙舞鹤之态,殆有类焉。”虽无类,却有例。武周圣历二年二月,武则天自洛阳赴登封封禅,留宿缑山君仙庙,感兴而撰文,并亲自书丹,同年六月,刻石成碑,曰《升仙太子之碑》。其书虽在行草间,却字字独立,笔断而意连,草而不乱,于婉约圆转中透得豪迈放达意态,于舒缓温润中显了内旷外疏质体。最是碑额的六个大字,也以飞白体行之。飞白书固然有“冥通飘渺,神仙之事也”之意境,恰与“升仙太子”之说吻合,却也不免有刻意模仿太宗之嫌,有“巾帼不让须眉”之赌气。尽管如此,这六个出自七十六岁老太太之手的别致大字,笔力雄健,意趣贞确,哪里有脂粉之气,哪里有妇道之象,全然仰首伸眉,盛唐本色。
唐玄宗李隆基的《纪泰山铭》为已知的最大幅摩崖石刻,其削山为壁、平壁为材而就,高达十三米,记述了开元十四年泰山封禅大典的全过程。其意可谓风发,其志可谓踌躇也。千余字个个榜书大写,通篇八分隶书,碑版峥嵘,气势恢恢,引得后人无限慨叹,明人王世贞赞之曰:“穹崖造天铭书,若鸾飞凤舞于烟云之表,为之色飞。”玄宗存世的另一书迹《石台孝经》,也为隶书,作于天宝四年。如果说书于李隆基嗣位前期的《纪泰山铭》尚有虎虎生机、奕奕神采,作于其执政后期的《石台孝经》已是一派光亮滑净、甜俗肥腻景象,不要说与古朴率真、浑然稚拙的汉隶相提,即便与之早年作品也无法并论。
宣和天子瘦金绝。宋徽宗赵佶所创瘦金体,屈铁断金、矗直挺拔,非功力与涵养极深者、非神志与精气极定者不能为。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对瘦金体推崇备至,称誉有加:“笔法遒劲,意度无成,非可以陈迹所求也。”蔡邕有“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之说,后世书家无不软中求怪,赵佶却反其道而行之,脱笔墨之畦径,硬毫瘦走,逞其斗能,直与鬼斧神工争胜,与镂月裁云赛美。如此极端,一则自信作祟,所谓艺高人胆大也,一则自尊夸示,以书艺之多能蔽治国之无谋也。从赵佶早期书迹看,虽有瘦金之意,却以模仿为主,少有越雷池之举,其初习山谷,后学褚薛,书风之立,立于登基之后。高宗赵构,书艺虽远逊乃父,却也不让时贤,《书史会要》评其书:“高宗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或云初学米芾,又辅六朝风骨,自成一家。”虽如此,后世对其书少有提及,倒是其《翰墨志》,在书学史上还占了一席之地。其书风走得是“二王”一路,而未“子承父意”,瘦金书随赵佶的遗尸北域而终成绝响。后人不习之,是修习者的功夫不达,还是忌讳创立者的亡国之运,不得而知。
明清帝王善书者夥,尤以康熙乾隆为甚。康熙帝的勤政历来罕有,而其学业上的用功也达到了下帷攻读、不舍分秒的地步,竟“无一日不写字,无一日不读书”。“朕自幼习书,毫素在侧,寒暑靡间”,推己及人,此时,书法也成了一项衡量人才优劣的要紧标准,这样的“书法用人观”虽说偏颇,却能为社会普遍认同。既为衡量标准,就要有标准的法度,这个标准就是为后人嗤之以鼻、深恶痛绝的馆阁体。科举招考官在阅卷时,“竟至一划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垢评第妍媸。”而康熙本人书法走得则是董其昌一路,但却雅致有余,素朴不足,工致有余,跌宕不足,其遒逸神韵、秀润如煦,甚至比不上同样脱胎于董书的崇祯书法。乃父顺治见过崇祯书法后,曾喟曰:“朕字何足尚,崇祯帝乃佳耳。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使人不觉酸楚耳。”乾隆所作御制诗的总数达四万余首,竟与《全唐诗》数量相当,其书法作品虽未见统计,却也不在少数。正如其诗虽多,而无一首传世,其书虽广,也无一纸流行。自古时间最公道,从来不留贵人头。乾隆竭力推崇赵孟頫之字,然模仿痕迹显然,未得赵书之髓,却有赵书之垢,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平庸刻板、珠圆玉润之余,质似蒲柳、弱不禁风之间,哪里还有天子的气宇轩昂、龙骧虎步,哪里还有帝王的特立独行、不拘一格。明末狂草书风盛行,名师巨匠辈出,然在不长的时间内,竟烟消云散处,恍若隔千年。思想钳制、文化禁锢的影响涉及深广,书法领域自然也不会放过。
帝王学书,客观上可以聘来最优的师傅,看到更多的真迹,只需稍用功,纵使资质中等、天赋平平,也能得一番景象,成几许面貌。帝王赐书大臣,大臣会视为至上荣耀,当作传家珍宝,帝王所题牌匾,或悬之名胜古迹,或奉之坊额楼头,碑之勒之,版之印之,故而传世有机遇,相袭多成习。然在改朝换代、兴衰更替之际,前度都城频频遭戮,禁苑屡屡被焚,帝王书法更在竭力毁坏、存心灭迹之列,一时沿与永世承,当朝颂与隔代扬,还在于贤佞明昏、治乱盛衰间,此乃书法之外的标准,亦笔墨以内的评判。
帝王好书,无下星散之赫赫书迹多辐辏内宫,麇集书房,虽便于存管,也易于趸毁。帝王好书,更在于倡导书风引领书尚。书法小道,因帝王摆布,也足以揄扬大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与玄宗同时代的韩择木、史维则、蔡有邻、李潮、徐浩、卢藏用、顾诫奢、梁升卿等人也舍楷择隶,群起效之,其丰容艳肌、字字珠圆、横平竖直、波挑规饬的集体无意识,最终导致了一字万同、一律千篇之隶书馆阁体的形成。
盖一艺之微,倡之者上,风靡者下也。天下以帝王好恶定一尊,岂仅在书法一项。
作者简介:介子平,编辑之友杂志社副主编。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