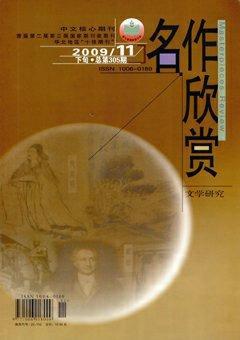论新写实主义的理论误区
关键词: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小说 零度情感 当代文学
摘 要:“新写实小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自觉的文学运动或流派,而只是一种“我行我素”的文学现象。由评论家一厢情愿地悬设倡扬的“新写实主义”理论只是一种自言自语的话语形式,是一种空洞的能指语符系统。“新写实主义”在概念定义上、理论阐述上以及对作家划分时表现出种种缺陷。方方等所谓新写实代表作家们的创作实例也充分证明评论家用“新写实主义”这个概念时所显示出的问题与不足。时隔二十年后再次反思,“新写实主义”不是理论而是现象。
我们并不反对评论家对文学进行各种各样的命名,但如果这种命名得不到读者甚至作家本人的赞同,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命名肯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新写实小说”曾经有过的“喧哗与骚动”已带着它所有的赞誉、被寄寓的厚望或遭受的批评而渐次沉寂,力图以理论标举和价值悬设引导文体创作潮流的“新写实小说”的鼓吹者沉默了,被他们划入“新写实小说家”行列的作家则纷纷“转型”了,一个个面目全非,越来越变得不像原先的那个“新写实小说家”了。也许,现在是到了平心静气地对“新写实小说”做一番反观、审视、总结,并给它划上句号的时候了。
事实上,“新写实小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自觉的文学运动或流派,而只是一种“我行我素”的文学现象。由评论家一厢情愿地悬设倡扬的“新写实主义”理论无疑是一种自言自语的话语形式,成为空洞的能指语符系统。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我们认为其存在许许多多的缺陷,这些缺陷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定义上的缺陷;二、理论上的缺陷;三、对作家划分的缺陷。本文要做的正是对这三大缺陷进行深入思考和剖析,进而得出新的结论。
一、定义上的缺陷
“新写实主义”作为一种文本模式,其本身就存在定义上的缺陷。考察其出现的历史渊源,不难发现它不过是一个舶来品,“新写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流派或创作倾向,最早产生于造型艺术。在造型艺术领域里,“新写实主义”(Nouveau Réalisme)这个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美术评论家雷斯塔尼(Pierre Restany)首创的,是针对1960年克莱因、汀凯力、阿尔曼、雷斯等人的美术创作流派而言的。他说:“新写实主义是不用任何争论,忠实地记录社会学的现实;不用表现主义或社会写实主义似的腔调叙述,而是毫无个性地把主题呈现出来。”{1}新写实主义在创作上反对抽象主义那种极端的主观性和脱离生活环境的倾向,提倡艺术向现实世界、特别是人的日常生活的回归。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新写实主义流派的造型艺术创作,常以日常生活用品和废物(如阳伞、碗盘、刀叉、烟蒂)等作为表现对象。通过对“新写实主义”这一概念的回顾及厘清,我们不难发现它不过是对某一造型艺术类型的概括,是国外一项艺术运动的名称。
我国文学中的“新写实主义”与西方造型艺术中的“新写实主义”是否有某种艺术思想联系,作家们是否有意借鉴他们的技巧?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必牵强附会去寻找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只能说是中国文学评论家囫囵吞枣把它直接挪用到了文学领域,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文学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伤害。然而在那个人人都想创新的时代,在那个“喧哗与骚动”的时代,没有谁会坐下来对文学进行深入思考,然后再划分归类。那些评论家要做的就是提出新名词、新理论,给一潭死水的中国文坛制造大量的肥皂泡话题。于是,“‘新写实终于以一个不可归属(主义?流派?创作方法?风格?)的概念引起了人们的瞩目和讨论”{2},冠之以“新写实主义小说”(丁帆、徐兆淮)也好,名之以“新写实主义”(雷达)、“后现实主义”(王干)或“现代现实主义”(陈骏涛)也罢,虽名称各异,阐释理解也不尽相同,但批评界还是逐渐取得了共识,名称最终确定为“新写实小说”并最终进入中国文学史,成为人们在谈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时一个无法回避的名词。
“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是在寻根小说和先锋文学的背景下‘回归写实的一股创作潮流,最初有评论家把它称为‘后现实主义或者‘新现实主义,也有人依据其题材上的特征称之为‘写生存状态或‘写生存本相的小说。自1989年6月《钟山》文学丛刊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以来,‘新写实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称谓。”{3}实在地说,关于新写实主义,其理论上的界定和阐释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和混乱:在定义和范畴上,形成多种旗号、主义、理论并存乃至互相对峙的局面。如果再仔细回顾文学史并深入思考,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的新写实主义不过是评论家和《钟山》等各大刊物为了推出作家的一种炒作方式,与现在的许多文学炒作方式并无本质区别。因为正是在这一理论口号下,不止一个刊物为新写实小说开辟出专栏,或者刊载专题论文。
学者南帆就曾经这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新写实主义)是一次别具一格的小说聚会,一个精明的办刊策略,一个审时度势之后文学话题的设计,一种机智的广告术,一种美学偶像的塑造,一次文学批评的力比多宣泄。”{4}一些读者也这样认为:“‘新写实主义这个概念的提出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定义与理论说明。它更像是刊物策划的一个活动。这使得‘新写实主义这个概念在使用中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破绽,以致最后人们不仅根本搞不清‘新写实主义究竟意谓什么,而且它在世俗层面的操作姿态,根本经受不起它那种所谓的‘新写实理论的种种考验。所谓的既‘实又‘新的文学内核与所谓的中国式现代主义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理论上不太成熟的杂交胎生儿,大而无当。”{5}
虽然读者与学者的学识水平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他们对评论家命名“新写实主义”这一现象的看法却趋于一致。即这一命名不过是刊物和文学评论家炒作、推出作家的一种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这一名词在理论上的基本缺陷,即评论家命名这一理论的初始目的并不是为了指导文学的创作,而是为了制造一个话题。
青年学者杨俊蕾则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一书中更深刻地指出了提出诸如“新写实主义”理论的这些评论家的心理:“他们(评论家)误以为词语的新变就是思想的新进,尤其是对同种现象如果可以使用陌生新奇的术语加以解释的话,似乎陡然就拥有了最高解释权而占尽先机。”{6}但事实上显然并非如此,这种让名词引导现象的炒作方法,并不能够深入文学的本质,并不能够反过来指导文学的写作,仅仅从语言层面上大量挪用西方新鲜术语的做法并不能够深层次地把中国文学的问题挖掘出来,最后给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的不过是一堆空心肥皂泡,看似五光十色,其实什么都没有。学者潘凯雄先生说得好:“归在新写实名下的作品相当芜杂,简直成了无边的新写实,其基本命题也越来越模糊,这种现象的出现,理论界有一定的责任。我们需要的是以科学的态度来认真地进行探讨,分析作品,而不能只凭感觉。乱提什么主义有害无利。”{7}
如果说这种挪用和炒作的做法直接证明了“新写实主义”在定义上的缺陷,那么,它在理论上显示出来的缺陷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所谓的理论并非理论而是现象。
二、理论上的缺陷
审察“新写实主义”这五个字,我们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偏正词语,由“新”和“写实主义”两个部分组成。写实主义,众所周知,它基本上可以和现实主义划等号。所以,在考察新写实主义理论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发现所有的评论家在阐释这一理论时,都不过是对现实主义进行某种矫正。“新写实小说之‘新,在于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即改变了小说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及反映方式”,“它最基本的创作特征是还原生活本相,或者说是在作品中表现出生活的‘纯态事实。无论是还原生活本相,还是纯态事实,其实都只能看作是作家故意选择的一种相对‘客观的创作态度,但其意图所在却明显是要清除观念形态(尤其是政治权力意识)对现实生活的遮蔽,消解强加在生活现象之上的所谓‘本质,以求复原出一个未经权力观念解释、加工处理过的生活的本来面貌。”{8}虽然评论家为这个“新”字增添了许多看似新鲜的花环,描绘了许多看似华丽的图景,勾兑了许多看似醇美的好酒,但却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现实主义的魔影。这也就注定了新写实主义只能够用一句俗语来形容——新瓶装旧酒。关于新写实作品的特征,代表作家池莉如是说:“我觉得作家有责任让越来越多的人读小说,通过小说唤醒周围的人,让他们觉得生活是不是应该更好一些,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文明一些。而要让读者接受你的劝告,你就必须很亲切地接近他们,深入地表现他们的生活,目的是使整个人类的素质得到提高。”{9}这哪是说新写实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特征,活脱脱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书”!
“新写实主义”理论对于艺术真实有自己特定的认识和看法,那就是“零度情感”,即作者在创作中回避激情,避免主观情感的介入,抑制对描写的人物和事件做出直露的评价,取退出作品的“不动情观照”的方式叙述故事。“以往那种随作者而来的主观好恶、价值判断、情感评价在叙述过程中被完全消解了,呈现出来的是不受作家‘精神污染的生活现象和生活事实的原始面貌,原始发生状态,从而达到一种客观的真实。”{10}有人则用“中止判断”来概括和肯定这样一种反映现实描写生活的写作态度,说:“新写实主义作家强调乃至放弃了作品的倾向性,‘中止判断成为新写实主义一个响亮的口号。作家在作品中不褒贬人物……作者并不想通过这些描述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理解,所以读者也无从通过对作品的解剖来了解作家的主观意图。”“作家把一切都写在作品里,读者在读作品时也能分析出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意味来,但读者绝不能说这个意义是作家想要表达的,因为作家在作品中什么都没说,他只是展示了生活。”{11}然而,按照美国文论家布斯的解释,小说就是一种修辞,“无论我们关于讲述故事的自然技法的概念是怎样的,每当作者把所谓真实生活中没人能知道的东西讲述给我们时,人为性就会清楚地出现。”{12}即使作者只是想精确地复述一个故事,“也必然存在用哪一种流行的形式来讲述的选择问题,他对他所讲的东西做出的选择还是要暴露给读者。”{13}所以,任何一部作品,作者的倾向性总是存在的,所谓“零度情感”也好,“中止判断”也罢,都是不可能的。在《单位》和《一地鸡毛》中,作者倾注在“小林”身上的主观同情和偏爱相当明显和主观随意,《故乡天下黄花》中对民族之间争权夺利的历史作者持非常严肃认真的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完全是按先入的理念或既定的原则来截取生活,并让笔下的人物和那些密集得过度的戏剧性细节都负载起某种历史和哲学的使命,成为某种作家急于表达观念的“传声筒”。再以方方的《风景》为例,小说以死去的小八子作为文本叙述者,为故事增添了悲剧的效果,沉郁苍凉的意味一直弥漫在文本中。虽然小说的最后一句说“而我和七哥不一样。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冷静而恒久地去看山下那变幻无穷的最美丽的风景”。如果硬要抛开这种悲剧和苍凉,我们似乎也可以依据小说最后那个“冷静”的词语来认定文本叙述者的“零度情感”,但如果以小八子这个文本叙述者的“零度情感”来认定作者的“零度情感”,这显然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错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评论家正是在这里犯了这个基本的错误,把小八子的冷静理解成了作者的冷静,把小八子的“零度情感”理解成了作者的“零度情感”,进而认定《风景》是“新写实主义”的开山之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荒谬。
事实上,《风景》文本所具有的存在哲学意味很难让人接受这是“零度情感”。而方方在参加叶立文的访谈时也明确指出:“其实《风景》并不是什么反拨先锋文学的‘新写实小说,像小八子这个人物是完全虚构的,他虽然是个死者,但并不具有多大的魔幻色彩。倒是从七哥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我对现实的处理方式,他的性格压抑感,甚至变态心理都使他在寻求一种突破。七哥的梦游,实际上就是他突破压抑的方法。而且梦游的情节还表现了人物内心深处的生存欲望,这种生存欲望说明人始终有反抗存在困境的本性,同时也说明现实的丰富与复杂。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风景》里写了城市下层人的住房、家庭环境,就说它是新写实的,也要看到它对人的梦境与现实交错的描写,很多评论者都忽略了这一点。”{14}当评论家把“新写实主义”这顶美丽的光环免费送给作家,作家却表示拒绝时,不用怀疑,这种所谓的“理论”肯定有缺陷。
如果这种理论上的缺陷还不足以推翻所谓的“新写实主义”是理论这一结论,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寻找它在对作家划分时所表现出来的尴尬。
三、对作家划分的缺陷
在创作实践中,事实上,被文学评论家命名为“新写实主义”的这群作家,他(她)们在写作的时候,不过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吸取了某些思想观念和表现手法,如生命意识和生存境遇的观念、荒诞和虚无的观念、无意识和非理性的观念及反讽、引喻、象征、拼贴、滑稽模仿、黑色幽默等手法,让传统现实主义从观念到手法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更新。又或者,他(她)们只不过是有意无意地借鉴了自然主义的某些艺术特点,如力图巨细无遗地描绘现实,排斥虚幻的想象,从而给人一种实录生活和照相式的印象,淡化情节,不去追求戏剧性的曲折变化,主张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反映现实。这些作家的作品根本就谈不上成熟,更别说标新立异,创立一种新的文学潮流。
作家方方就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这样说道:“自己独出心裁的东西并不多,更多的则是一种模仿,甚至是刻意地模仿和追求某种风格。号称是摸索,其实是陷入混沌迷茫中不知自己失落在何处。看似追求一种新意,其实是落入一种更深更隐晦的俗套。”{15}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面前,刚登上文坛不久的方方在写作时心中其实并无定数。她的小说实际上是不同程度地对西方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模仿,甚至是对中国作家王安忆的模仿。先锋文学作家余华也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则更小。”{16}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被评论家命名为“新写实主义”的这群作家在写作时不过是对西方自然主义、现代主义作品的模仿和借鉴。虽然评论家对他们的写作总是冠以“创新”之名,为他们披上“新写实主义”、“先锋文学”的外衣,但这并不能够掩盖这群作家的创作是对西方作品的模仿和借鉴这样一种本质。
我们无意反对这样一种模仿和借鉴——事实上,中国文学自“五四运动”以来从来都不过是在西方文学的背影下亦步亦趋。而“文革”以后的80年代文学中,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从西方的作品和理论中吸取养料。从寻根文学思潮到先锋文学思潮再到新写实小说思潮;从韩少功的《爸爸爸》、《马桥词典》到马原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再到刘恒的《伏羲伏羲》、《白涡》等;我们都可以看到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影子。其中,韩少功的《爸爸爸》分明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而他的《马桥词典》则又显然模仿了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否则也不会在1997年惹出“剽窃”官司。马原在2000年与张英的一次访谈中也明确表示美国的海明威、欧·亨利、奥康纳、霍桑、麦尔维尔、克里斯蒂、纪德、雨果等作家都对他的创作形成过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刘恒的《伏羲伏羲》、《白涡》、《虚证》等一大批探讨性心理阴暗与痛苦的小说,则无疑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被评论家命名为“新写实主义”的作家群,他(她)们在写作时,基本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的模仿和借鉴,所以他(她)们写出来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西方作品和理论的烙印,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一些相同的色彩(当然,在模仿和借鉴的过程中,由于作家个人特性的不同和借鉴作品的不同,他们的作品也表现出了各自的异质,所表现出来的文本特征也有所不同)。就是这样一种模仿和借鉴却被中国所谓的评论家们冠以“新写实主义”的美名。然而,这样一种命名的实质不过是一种“术语换班”,或者说是一种“名词轰炸”,并不能够给中国文坛带来真正的东西,最多,不过是给读者一种文坛热闹浮华的错觉。
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那些鼓吹“新写实主义”理论的评论家仍然没有提出一个严格的理论尺度(更别谈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场),所以当他们运用这样一种时隔二十年尚未成熟的理论对作家进行划分时必然会漏洞百出。叶兆言与苏童就曾经毫不讳言地宣称,“新写实是被评论家制造出来的,前几年文坛太冷清了,于是便制造出这么一种文学现象,热热闹闹,使人们对文学重新感兴趣。新写实是评论家和读者的事,作者要站稳立场,不能被这些热闹的景象所迷惑。如果一个作家被划入一个流派便意味着这个作家的活力的丧失。”{17}路遥也直言不讳地说,“这种或左或右的文学风潮所产生的某些‘著名理论或‘著名作品其实名不副实,很难令人信服。”{18}以被评论家们标榜为“新写实主义”开山之作的《风景》为例,一直觉得该作品并非典型的“新写实小说”,作者方方更像一个受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并带上中国式的玩世不恭和“黑色幽默”的“现代派”作家,比之与池莉,她与刘索拉、徐星似乎更接近。深入文本底层探究,我们发现对于道德的拯救和存在价值的思考才是这篇经典之作的理性界定,作者对作品中的人物大都充满了同情和理解,而远非如评论家所说的“零度情感”。作者在《我眼中的风景》一文中就曾经这样说过:“七哥们的奋斗也许是不高尚的,但比起那些不劳而获者,七哥们倒也显得高尚得多。毕竟,他们花费过心机且劳碌过一番。”{19}对生长七哥们的土壤则采取了批判和责难的态度,在《仅谈七哥》一文中作者就这样指出:“该责难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20}这种批判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新写实主义”标榜的“零度情感”。
在对方方其他作品的阅读中,我们发现沉重是她作品一贯的基调。她的“风景”系列小说如《黑洞》、《落日》等似乎都与“新写实主义”相去甚远,作品表现出来的那种揭示人生无奈与冷酷的调侃之笔显然不是“零度情感”所能包含的。她的知识分子系列小说,如《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定数》等都深刻描绘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畸形和转型时期的生存窘态,特别是《祖父在父亲心中》,文中凝重、悲怆的笔调无法不让读者理解成是对“新写实主义”理论的反叛,文中时刻洋溢着的那种理想主义激情无法不让读者理解成是对新写实主义理论的嘲弄。而爱情系列小说如《桃花灿烂》中那种感伤而悲凉的文风与“新写实主义”理论所标榜的“零度情感”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可以说,“新写实主义”理论在对作家划分时所显现出来的那种缺陷因为时间的推延而更加明显。那些提出“新写实主义”理论的评论家为了给自己的理论找到足够的证据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扩大理论的外延,不得不把许多风格迥异的作家和作品拉扯在一起{21},从而让这一理论越来越显示出荒唐的一面。以被评论家标榜为“新写实主义”两面旗帜人物的池莉和方方为例,前者因为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的认同和赞美(这种认同和赞美同样是对“零度情感”的反叛和嘲弄)而获得了“平民作家”的称号,甚至,在往后的写作中,她的作品一路下滑,直至陷进媚俗的深渊。然而后者却从始至终都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写作,即使是在写作小市民题材的小说时,那种批判的主观色彩仍然隐含在文本深处。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她们的作品风格完全有着质的区别。但就是这两位有着质的区别的作家却硬是被评论家拉扯在一起,并驾齐驱,成了新写实主义的两位代表性作家,这不能不说是“新写实主义”理论的最大败笔。
重返文学史现场,我们会发现那些所谓“新写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根本就无法认识,无从区别。那个时代的作家在写作时所表现出来的千变万化或者说在对西方作品的多角度模仿中显露出来的那种特质,并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新名词、新术语“新写实主义”概括。更何况,“新写实主义”这一理论从开始命名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一直都没有一个基本范围的界定,这一所谓的理论二十年来从来都未明确和清晰过。所以,评论家用这一时隔二十年尚未成熟的理论对作家进行划分所表现出来的必然是荒唐,它遭到作家的反对也就不足为奇。
四、结语:现象而非理论
站在二十年后的21世纪,反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段文学浪潮,经过深入思考和分析,我们认为“新写实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现象。它那种挪用和炒作的做法除了给文学史留下一场“喧哗和骚动”外,并没有给文学带来别的什么。评论家所标榜的那些诸如“零度情感”之类的理论并没有给作家的创作以指导,相反,我们常常会发现,评论家所吹捧的“新写实小说家”在写作时经常有意无意地对那些所谓的理论进行反叛和嘲弄。评论家提出的那些条条框框并不能够对作家进行一种真正的划分,相反,它引起的是许多读者和作家的反对。它不过是刊物和评论家制造的一个话题,并没有深入20世纪80年代末那段文学浪潮的灵魂深处。这种让名词引导现象的做法并没有给文学带来多少好处,相反,它让本就浮躁的文坛更加浮躁。
别林斯基曾经这样指出:“要写作一部俄国文学史,这就意味着要显示出:俄国文学,作为彼得大帝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的结果,怎样从盲目模仿外国范本,采取纯粹雕琢辞藻开始,后来怎样逐渐地力求从形式主义中摆脱出来,为自己获得生命力因素和独立性,最后怎样发展到十足的艺术的高度,成为社会生活的表现,变成俄国的东西。”{22}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文中也曾经这样指出:“对我国刚刚兴起的文学思潮,理论批评首先有责任分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模仿甚至是变相照抄,然后才有可能估价其真正的价值。”{23}只有用这样一种严肃的观点来审视中国二十年前的那段文学思潮,来要求中国现阶段的文学,中国文学才有可能重新获得生命,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涅槃。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需要不断地深入思考,需要不断地去伪存真,甚至需要不断地“重写”。只有这样,中国作家在创作时才能够走出盲目模仿外国文学范本的误区,中国评论家在阐发理论时才能够避免盲目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甚至一些本不是文学理论的理论。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有可能去掉那些浮华的泡沫,中国文学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中国文学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复兴。
作者简介:马建高,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美学与基础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① Willy Rotzler.新写实主义[A].物体艺术[C].吴玛俐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② 汪政,晓华.关于“新写实”的几点讨论[J].文艺评论,1990年,第1期.
③ 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M].下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④ 南帆.新写实主义:叙事的幻觉[J].文艺争鸣,1992年,第5期.
⑤⑦⑨{17} 丁永强.新写实作家、批评家谈新写实[J].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⑥ 杨俊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⑧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第307页.
⑩ 王干.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J].北京文学,1989年,第6期.
{11}丁永强.现实主义与新写实主义[J].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4期.
{12}{13} 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第22页.
{14} 方方,叶立文.为自己的内心写作——方方访谈[J].小说评论,2002年,第1期.
{15} 方方.怎么舒服怎么写[J].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16} 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J].作家,1996年,第3期.
{18} 路遥.路遥全集[Z].散文、随笔、书信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
{19} 方方.我眼中的风景[J].小说选刊,1988年,第5期.
{20} 方方.仅谈七哥[J].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5期.
{21} 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被归入到“新写实主义”门之下的作家非常广泛,包括刘震云、方方、池莉、范小青、苏童、叶兆言、刘恒、王安忆、李晓、杨争光、赵本夫、周梅森、朱苏进等等,几乎包括了“寻根文学”以后文坛上最活跃的一批作家;见李怡.文艺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国现实——《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代序[J].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该文更是将“文革”后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统统纳入“新写实文学”的帐下。
{22}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M].第3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
{23}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Z].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责任编辑: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