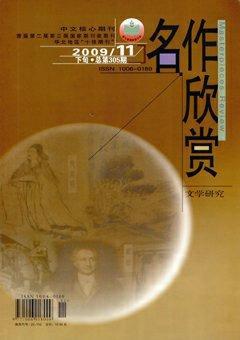继承与颠覆
张 罗 吴庆宏
关键词:迈尔斯·弗兰克林 《我的光辉生涯》 19世纪澳大利亚女性小说
摘 要:澳大利亚女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的小说《我的光辉生涯》在继承19世纪女性文学传统的同时,不满于中产阶级女作家脱离丛林实际生活的浪漫化、理想化创作模式,从叙事手法、人物形象、婚姻主题等几个方面改写了19世纪女性小说模式,开创了澳洲女性文学新的发展方向。
《我的光辉生涯》(My Brilliant Career)是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1879-1954)的成名之作,因其具有鲜明的“澳大利亚”特色,曾被澳大利亚最早的职业文学评论家A.G.斯蒂芬誉为“第一部澳大利亚小说”。我国学者黄源深1989年发表的中译本一经问世,也吸引了广大中国读者。本文将聚焦弗兰克林与19世纪澳大利亚女性小说家创作上的异同,以突出其对女性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
《我的光辉生涯》最早发表于1901年,当时弗兰克林年仅21岁。此前,澳大利亚小说在19世纪后期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许多杂志刊登的连载故事,既培养了读者的趣味,也扶持了本土作家,特别像《澳大利亚杂志》(Australia Journal)之类的期刊还登载了许多女作家的作品,以至于澳大利亚涌现出一批职业女作家,包括阿达·坎布里奇(Ada Cambridge, 1844-1926)、凯瑟琳·海伦·斯彭斯(Catherine Helen Spence, 1825-1910)、罗莎·坎贝尔·普里德夫人(Mrs Rosa Campbell Praed,1851-1935)、塔斯玛(Tasma, 1848-1897)等。所以,弗兰克林的创作并非像一些人所宣称的那样,是在只有欧洲女性作家先驱或只有男性澳大利亚作家为榜样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的澳大利亚并不缺乏女性文学的传统,只是19世纪澳大利亚女性小说家长期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遭到了忽视或贬损。对于她们创作的近300部小说和无数小故事,弗兰克林绝不可能一无所知,例如《我的光辉生涯》中的女主人公西比拉所读的《澳大利亚人》杂志就曾在19世纪70和80年代连载了许多阿达·坎布里奇及其他澳大利亚女作家的作品。不过,弗兰克林未囿于19世纪澳大利亚女性小说的传统,尽管她仍与自己的女前辈们一样,在小说中继续探讨女性问题,但是她却采用了“改写”的策略,使《我的光辉生涯》在叙事手法、人物塑造和主题探讨等方面颠覆了19世纪澳大利亚女性小说的传统模式,为澳大利亚女性小说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1.叙事手法
19世纪澳大利亚女性小说家大多深受奥斯丁等英国女作家的影响,将小说场景设定为中产阶级妇女的小生活圈子,以女主人公对爱情和婚姻的选择作为小说主题。如斯彭斯的代表作《克拉拉·莫里森》(Clara Morrison)模仿奥斯丁的反讽写法,描绘了一个姑娘在做家庭教师的理想破灭后,宁愿自降身份去做女佣的故事;普里德夫人的小说多以澳大利亚为背景,记叙女主人公历经波折最终找到真爱的故事。坎布里奇的小说,如《结婚典礼》(The Marriage Ceremony, 1894),仍以“爱情和婚姻”为主线,围绕男女主人公是否该为遗产而结婚的话题展开讨论,对人性进行剖析,内涵显得更为深刻。
《我的光辉生涯》粗看起来似乎并没有跳脱这类浪漫爱情故事的定式,也描述到女主人公西比拉与多位求婚者的交往。其中,年轻绅士埃弗雷德·格雷是在悉尼工作的律师,对艺术有很高的品味;牧羊徒工弗兰克·霍登虽然粗俗,但很快将从英国继承一大笔遗产;年轻牧场主哈罗德·比彻姆虽然寡言少语,却是位非常善良正直的丛林人。最后,西比拉实际爱上了比彻姆,并在比彻姆突然破产时答应嫁给他。之后,西比拉为了生计不得不去给人做家庭教师,她和比彻姆的恋爱因此也经受了许多挫折。比彻姆的财产不久失而复得,他因此准备迎娶西比拉。这些情节似乎都只是先前女作家笔下通俗爱情小说的俗套。倘若真是这样的话,《我的光辉生涯》又何以轰动澳大利亚文坛呢?
其实,弗兰克林试图通过戏仿19世纪澳大利亚女性小说家的作品,暴露其前辈的不足。她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一个真实的故事”,并特别提醒读者,在她的作品里没有落日的美丽和轻风的低吟之类的浪漫小调,有的只是丛林环境所带给她的愤懑、烦躁和痛苦。与之相应,她的小说没有情节,因为“生活中并没有情节”。
她们至多在感到痛苦或压抑时,把丛林作为庇护所,弗兰克林还声称,她“试图对通常的自传形式做一改进”。尽管她没有明指,但熟悉通俗女性小说的读者不难发现她的靶子。众所周知,奥斯丁式的传统女性小说,总是以第三人称叙事,作者隐藏自我意识,借人物的讥诮来含蓄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看似客观中立的风格,更能为男性读者所接受,却遭到部分激进女作家的反对。在《我的光辉生涯》中,她没有沿袭先前澳大利亚女作家常用的第三人称叙事,而是以女主人公西比拉的第一人称自我叙述来展开整个故事。在前言中,弗兰克林毫不讳言自己要在作品中表现女性的自我中心。这样的改变,与其说是视角变换,不如说弗兰克林选择了直接表露她强烈的自我意识。例如,在面临旱灾时,西比拉感慨生活的迷茫:“疲倦啊,疲倦!这就是生活——我的生活——我的生涯,我的光辉生涯!”只有借这样的“呐喊”,西比拉才能道尽心中的愤懑,而这是第三人称叙事所无法完成的。通过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让女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完全释放,弗兰克林把读者带进了丛林女性的真实内心世界。
2.人物塑造
叙事手法的改变只是弗兰克林改写传统女性文学的第一步,她对澳大利亚女性文学的最大改变在于:她以现实的丛林女性形象,取代了先前女性小说中虚幻的中产阶级女性形象。
在19世纪澳洲文学中,丛林是常见的元素。当时,一些男性作家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有意识地将艰苦的丛林创业理想化,试图以勤劳勇敢的男子汉形象作为澳大利亚民族精神的象征。丛林妇女后来也逐渐成为他们新的歌颂对象,因为随着19世纪中期“淘金热”的兴起,许多丛林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妇女不得不承担本应由男子完成的苦力活。在男作家笔下,澳大利亚妇女往往被描绘成一个自力更生的人物,当丈夫外出淘金或务工时,她独立照顾一大群孩子,面对丛林里的各种可能灾难而泰然自若。然而,这样的女性英雄形象其实只是男性拓荒者形象的翻版。她们仿佛已完全脱去维多利亚小说中上层女性的柔弱气质,成为男性力量缺席时的替代品。
另一方面,19世纪澳大利亚女小说家仍有不少继续以英国中产阶级生活为范本,对她们而言,丛林女性似乎并不适合作为她们小说的主人公。例如,塔斯玛的作品只涉及墨尔本的上流社会家庭;普里德把丛林作为衬托文明社会的背景;而阿达的小说并没有表现出环境对人的影响,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只不过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英国式知识分子,她们至多在感到痛苦或压抑时,把丛林作为庇护所,试图到大自然中寻求安慰;至于那些改由丛林女性为描述对象的女小说家,她们一般塑造的都是虚幻的理想化女性人物——天生温文尔雅,却能承担沉重的生活负担,而不失淑女风范。小说《一个女人如何保守其承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女主人公玛格丽特下嫁后,通过起早贪黑地辛勤劳作,不断改造丈夫,不仅维持了稳定的家庭生活,还保留了其原有的阶级地位,成为令人尊敬的女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9世纪澳大利亚女性小说与英美女性小说一样,试图表现维多利亚时期盛行的男女属于不同领域的观念,而把家庭描绘成女性享有权力和影响的场所。但是在《我的光辉生涯》中,这种稳固的女性世界幻象破灭了。
与大多数19世纪的男性或女性作家不同,弗兰克林拒绝歌颂丛林生活,拒绝歪曲女性的生活现实。她在《我的光辉生涯》里,尖锐地表现了丛林生活的艰苦和对女性的摧残,她笔下西比拉的母亲露西的形象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露西原本是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姐,“天使般甜美、迷人、温柔、快乐”的姑娘,婚后却要照顾丈夫和八个子女,整日忙于生计,最终“由于无穷无尽的操劳,由于在贫穷中徒劳挣扎而皮肤粗糙、脾气暴躁”。弗兰克林还借女佣之口嘲讽了那些以英雄自居的男性拓荒者:“他们让女人太辛苦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疲倦的女人……在这儿,她们什么都干,挤牛奶呀,喂猪啊,喂才生下来的小牲口啊,简直使我作呕。”尽管丛林女性无偿地付出了一切辛劳,她们却没有独立的权利,家里的收入全由丈夫支配,“女人不过是男人无能为力的工具——环境的动物”。所以,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先驱路易莎·劳森(Louisa Lawson)曾质问道:“男人难道不应该允许妻子得到规定的休息时间、合理的报酬、公正体贴的对待吗?妻子们的工作时间总是无止境的。”
为打破19世纪女性小说中理想化美丽贤淑的女主人公形象,弗兰克林笔下的女主人公西比拉不仅相貌平平,而且极具个性和叛逆精神。她幼时爬树掏鸟窝,与小狗嬉闹,骑马,游泳,是父亲的丛林好“伙伴”。稍大后,她就开始喂牲口,挤羊奶,擦地板。原始的丛林环境和艰难的物质生活锻造了她粗犷、泼辣,近乎男子汉的性格,她厌恶贫困、单调、乏味的生活和精神的空虚,渴望一种更丰富多彩更有意义的生活。为此,她一有空就阅读各种文学名著,并常在夜深人静时握笔学写小说,希望在文学创作上显示自己的才华。她不愿重蹈母亲的覆辙,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艺术追求,甚至坚决拒绝婚姻。而婚姻在先前的女性小说中,一直是女人唯一的出路。所以,“西比拉是澳大利亚文学上第一个具有本地特色而又内涵丰富的女性形象。……她是身上散发着丛林气息、胸怀远大抱负的澳洲丛林知识女性”。
毋庸置疑,弗兰克林的女性人物塑造反映了一种激进的女性主义立场,有力地推动了女性主题的探讨。
3.主题探讨
爱情与婚姻一向是女性小说探讨的重大主题。简·奥斯丁曾在《傲慢与偏见》里评论道:“大凡家境不好而又受到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总是把结婚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尽管结婚并不一定叫人幸福,但总算给她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不致挨冻受饥。”婚姻在19世纪仍然是女性获得生活保障的唯一途径,即使因丛林生活的特殊性而使婚姻成为女性的痛苦根源之一,女性还是不得不接受婚姻。
于是,19世纪澳大利亚女性小说总体上还是秉承了这种妥协态度,以阿达·坎布里奇和普里德夫人为首的多数女作家在小说里尽管质疑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束缚,但仍然赞美理想婚姻,教育年轻女性要选择真爱。典型的例子是坎布里奇的中篇小说《女孩的理想爱人》(A Girls Ideal,1881)。小说的女主人公玛丽·汉密尔顿一再拒绝年轻绅士多纳德·麦克劳德的求婚,一心等待自己所爱慕的船长。经过几番波折,玛丽终于发现船长爱的是她的钱,而不是她本人,而麦克劳德才是她的真爱。坎布里奇把最后一章冠名为“学到的一个教训”,玛丽对麦克劳德承认自己“一直都在犯错误”,两人最终成就美满婚姻。
当然,也有个别女作家从切身体验出发,强烈反对现行的婚姻制度。斯宾塞(Catherine Helen Spence)认为,婚姻制度应该修改,甚至废除。她在1879年完成的小说《婚约》(Handfasted),因为思想过于激进,一再被编辑拒绝。直到1984年才获得出版。凯瑟琳·马丁(Catherine Martin)的小说《一个澳大利亚女孩》(An Australia Girl, 1890)则把婚姻称之为“最愚蠢的、错误的古老制度”。女主人公的丈夫在社会地位和智力才能上都不如她,还有酗酒和暴力的恶习,但她却无法提出离婚,只能一心投入自己所喜欢的人种研究,以此作为反抗。
在《我的光辉生涯》里,弗兰克林采取了同样激进却更为现实的态度。在她看来,先前的女性小说中所宣扬的浪漫爱情,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她在小说中借西比拉之口说道:“想象中和歌声中的爱情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在平凡的现实中,爱情是最低级的激情,被最艺术的鼻子和嘴巴所点燃。”她意识到,修改婚姻制度,改善女性地位绝非一时所能完成。要想避免婚姻悲剧,最现实的途径就是保持单身,拒绝婚姻。她本人就是终身未婚,因此小说中西比拉的心声也正是弗兰克林本人的态度:“结婚就是陷入可怕的羁绊,就是女人过不公平的生活。”她决定“永远、永远、永远不结婚”。即使是面对她内心深处已经爱上的比彻姆,西比拉还坚持说:“我已下定决心——肯定不同你结婚。……并不是我不喜欢你,我爱你甚过于爱任何我所见过的男人,但是我从来不想嫁人。”对西比拉来说,如果嫁给比彻姆,尽管衣食无忧,却需要操持管理一大片牧场,要生育十几个孩子,这样的生活对渴望艺术、热爱写作的她来说,无疑是折磨。波伏娃曾指出,生育是女性遭受奴役的重要原因。而西比尔所追求的,就是要成为波伏娃所提倡的无子女不结婚的“独立女性”。评论家蒂莉·奥尔森也曾指出,在女性取得独立之前,几乎所有的卓越成就都是由无子女的妇女取得的。
《我的光辉生涯》最终因其在女性婚恋主题上的大胆探讨吸引了批评界日益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在20世纪女性主义第二波浪潮兴起后,它那深刻的女性洞察视角使读者深受启迪,以至它在1979年被改编成剧本搬上了荧幕。
《我的光辉生涯》对19世纪女性小说创作模式的颠覆标志着澳洲女性文学的重大转折。
进入20世纪后,坎布里奇等19世纪女作家所创作的曾经流行一时的女性浪漫传奇渐渐湮没在文学史中,直到80年代才被重新发掘。而弗兰克林所开创的丛林生活题材,由苏珊娜·普理查德(Katherine
Susannah Prichard)等人继承和发扬,成为当代澳大利亚女性文学的重要部分。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07年科研基金项目“澳大利亚女性文学溯源”(项目编号07SJB750016)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 罗,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吴庆宏,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参考文献:
[1] 陈茂庆.在丛林里挣扎的年轻艺术家——评析《我的光辉生涯》中的女主人公形象[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87-91.
[2] 陈茂庆.反抗婚姻的丛林少女——小说《我的光辉生涯》女主人公形象剖析[J].西华大学学报,2007(4):1-6.
[3] 田耀,李典.根植于丛林中的不羁灵魂——浅析《我的光辉生涯》中西比拉的异样人格[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9):69-71.
[4] 石发林,于美琴.论《我的光辉生涯》中女主人公形象[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3):83-85.
[5] Frances McInherny,Miles Franklin, My Brilliant Career and the Female Tradition, 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 vol.9, no.3,1980: 275.
[6]Susan Gardner, My Brilliant Career: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Wild Colonial Girl, in Carole Ferrier ed.,Gender, Politics and Ficition.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85:22.
[7] 迈尔斯·弗兰克林.我的光辉生涯[M].黄源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8] 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9] Conway, Jill. Gender in Australia[J]. Daedalus, 114. 1 (Winter, 1985): 343-368.
[10]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92-94.
[11]Michael Ackland, ed. The Penguin Book of 19th Century Australian Literature [M]. Penguin Books Australia Ltd. 1993.
[12]Cambridge, Ada. A Girls Ideal [A]. in Dale Spender, ed. The Penguin Anthology of Australian Womens Writing. Penguin Books Australia. 1988: 156-284.
[13]Spender, Dale. Writing A New World: Two Centuries of Australian Women Writers [M]. London: Pandora Press, 1988.
[14]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5]张岩冰.女性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水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