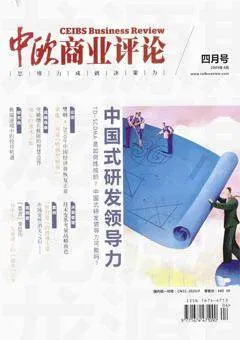在不确定中前行
在不确定中执著前行吧,就像马云说的那样,不要倒在光明到来的前一天晚上。
在上一期杂志中,我提出除了工具理性之外,还必须回到管理的原点,从企业特定的情境出发,系统地思考管理问题。现在,我们对中国式管理特质的追问还在继续,尽管这种追问似乎笼罩了不确定性的色彩:
先是易中天来中欧演讲,说起中国的传统思想学说产生不了革命性的思想,因此中国老在产权不清的社会与政权里反复更替,由于产权不清而没有明晰的私权,没有私权就谈不上道德,没有道德就谈不上信任,没有信任就谈不上代理,没有代理,企业怎么搞得好呢?
接着是访谈来自中国台湾的蔡舒恒先生。蔡先生认为,即使在管理相对现代化的中国台湾,实际上继承的仍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儒家基础的企业,吸收了西方文化基础的方法论后要完美融合,就得花更多时间去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工作,以这种人际关系来弥补文化基础上的差异,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台湾式企业会做得比西方企业更辛苦,但是效果好像也没超过西方。
然后就是中欧的肖知兴先生,提出中国人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相比西方更有感情之心(heart),却少了思考之心(mind)和灵魂之心(soul)。少了思考之心,就解决不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就难以发达:少了灵魂之心,就解决不好人与自我的关系,以感情之心维系的人际伦理、道德原则就容易经受不住种种诱惑而塌陷。
肖先生谈的是创新之痛,应该也是企业管理之痛。任何管理理念与方法,都必然以特定的价值观与思想为基础,而任何管理价值观与思想,又必然是社会整体价值观的一个构成部分或体现。由此,这些看似有点悲观的色彩,似乎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式管理”的基础:我们并不具备建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文化和思想根基,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是一条艰辛的未知之路。
然而本刊编辑部并不会停止思考与追寻的脚步:即使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管理理论,也不是朝夕得来,而是有着漫长的进化与结晶历程;中国企业环境的差异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却正好形成洼地效应,文化价值观的成形如我们的批判一般将以更加深刻的方式呈现。
况且,“中国式管理”本身已春寒破土。例如,继华为的“知识力密集型企业”模式之后,我们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第一个世界通信标准TD-SCDMA的成功提出并实现商业化的案例,继续追问“中国式研发领导力”的内涵,并以此作为本期杂志的封面专题。同时,本期我们还请中欧的梁能教授分析了中国本土管理教学中案例内容方面的变化,提出需警惕西学之误;由本刊高级记者朱琼深入分析了海尔学习苹果公司的商业模式转型可能存在的踏空风险;多方碰撞了首席战略官的中国式尴尬;摘录了易中天教授讲解的先秦诸子的“救市”理念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