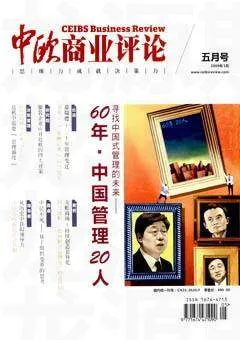领袖的两面性
我们需要领袖吗?在将互联网作为意识形态的网络一代眼中,人人都可以成为领袖,因而谁也不是领袖。但是,奥巴马的上台再次证明,领袖的确在网络时代中不可缺少。早在维多刺亚时代,托马斯-卡莱尔就提出:“一个渺小而狭隘的人所做的最悲哀的事情就是对伟人的不信任。”人类社会对领袖的需求是自始至终的,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却羞于对这种心理的自我认同。
在现实中,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标榜可以惠及最普罗大众利益的组织里,充斥着狂热的偶像崇拜气氛;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具有自组织意义的团队里,却有某种“触媒”人物的存在;一场以人民的名义发动的战争,到头来才发现是某位团队领袖的垄断意志;在互联网世界里,众声喧哗之后依然有一位领袖站了起来。
弗格森教授在和狄洛夫交谈时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两个层面的意义:领导力是一个人成为领袖的主要基石,历史从来都是垂青于领袖的;当一个人占据领导者的位置之后,他的领导力行为将被一种制度性的存在所左右。
在第一个层面里,“领导力”是一种才能。这种才能是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信仰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综合素质。如同英国历史学者安德鲁·罗伯茨认为的那样,只有当信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时候,领袖才会不复存在。因此,如同“勇气”一样,领导才能是没有“善”、“恶”之分的。阿道夫·希特勒凭借着自己的执著和对种族主义的信仰,站到了权力之巅;基地组织在本·拉登个人魅力的感召之下,成为了总能死而复生“海星”。尽管这是两个极端的人物,但却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究领袖如何向组织成员传达自己理念,从而形成了强大甚至是令人恐惧的号召力。
当获取了最高权力之后,组织的最终归宿除了和领导者个人能力相关之外,还掺杂进了更多的制度和道德因素。比如在评价B9aRR9jJp+HFvw9E+3ERIw==希特勒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在感叹他卓越的煽情能力,一方面又要对其品质和思想进行鉴别。在弗格森教授眼里,导致领导力道德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组织是否具有良好的分权体系,以及当权者本人是否具有分权意识。希特勒和丘吉尔无疑是最能说明两类人的典型。两个人都是对权力追逐不加掩饰的人,但是希特勒的权力观是突出自己在组织中的决策作用,而丘吉尔的权力观则是权力属于众议院,自己的工作是要说服他们。两种权力思维最终造就了两个结果:希特勒无休止地介入到了纳粹军队的战略甚至是战术制定中去,直接导致了德军在多次关键战役中错失良机;丘吉尔事无巨细地关注着战场的每一个细节,但他更多的是做一个记录者和观察者。他信赖自己的将领,他用强大的演讲而不是干预来取得人民的支持。
成功的领导还是失败的领导,这个命题也因为弗格森数授的观点而更具深意。对于“成功”和“失败”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到领导者个人县面的素质,而是应该看到领导力的两面性:领导者自身的道德渴望和组织的制度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