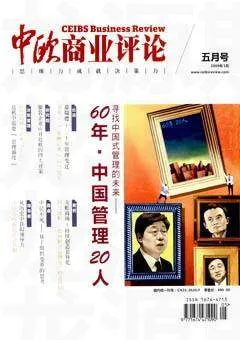周伟焜:15年后重新出发
蓝海六个月之后就可能变成红海,我们永远生活在红海里面,所以要一直保持创新的步伐。
对于很多公司来说,2009年都是一个特别的年份,IBM也不例外。
在经历了开始试探、全面投资、整合进入全球体系三个阶段之后,2009年成为IBM在中国市场重新出发的新一轮周期的开始。
现年63岁的周伟煜自1995年以来一直担任IBM大中华区董事长,15年来应对中国市场的不断挑战,没有蓝海,永远生活在红海里面。这一经历不仅是他个人的财富,也值得许多经理人借鉴。《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IBH从1979年进入中国市场至今已有30年,几乎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为什么2009年要“重新出发”?
周伟焜:IBM在中国市场之前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90年,当时主要是试探市场,那时候外资企业还不能直接开分公司,只能成立办事处。
第二阶段是1990年到2000年,这是我们全面投资中国市场的阶段。在短短的10年内,我们建立了研究院,建立了软件开发、销售、服务、租赁等部门,所有政府允许投资的,我们都去投资。当时,IBM所有的高级副总裁一定要来中国,那时候还有一个笑话,一群高级副总裁来了,我必须依次给他们盖个章,证明他们来过了。
第三阶段是2000年到2008年,这时,我们已经开始考虑怎样将中国部署在IBM全球一盘棋里,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中国市场因而成长为IBM非常重要的研究、生产、服务枢纽。
现在世界经济增长放慢,中国、印度就成了增长的尖兵,必须给予很高的重视。所以我们从2009年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重新出发。
CBR:从理论上说,一个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的管理人员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市场坚持这么多年?
周伟焜:是的。我个人从第二阶段后期过来后就再也没离开过,但坦率地说,我认为很多公司在经历这些不同的阶段是要换人的,因为每个阶段需要不一样的人。
在第一阶段,我们主要找一些很有经验、深得公司信任的员工来开发市场,开玩笑地说,最好是从美国西部找些牛仔来,他们最有创业和开拓精神;而第二阶段要找有眼光、立足成长的人。他必须能够很快融入市场并了解市场的重点在哪里,当与总部意见相左的时候,他必须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协调能力,从而能够放手创造一个新世界;第三阶段要找到一个整合者,要有办法跟总部进行很好的沟通,让总部把更多的工作和职能交过来。现在第四个阶段,需要和第二阶段差不多的人,但是必须有驾驭一个更大组织的能力,因为现在的组织比10年前大得多了,而且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必须把自己的想法和总部进行很好的沟通,甚至要劝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想法。
我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但我也一直在学习怎样调整自己的作风和做事的方式,因此有机会在中国市场工作十几年。
CBR:根据你这十几年的经验,外企高管在经营中国市场时碰到的最大困难或挑战是什么?
周伟焜:主要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把董事会的期望值调校到一个合理水平。我刚来的时候,(时任IBM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郭士纳的要求是每年翻番的增长。来了以后我发现达不到他的要求,必须重新确定符合实际的目标。但这目标也不能调得太低,否则就很难得到总部资源上的支持。调整预期并说服董事会接受,我觉得这个很困难。
第二个困难在于人才,这个困难从我接手工作到目前为止一直都存在,持续了10多年。我们不喜欢从外面聘请很多高管,而希望用自己训练出来的人,但是业务成长速度比培养人的速度快多了,这是我们的最大挑战。
CBR:那么你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先说第一个,当初你是如何说服总部调低期望值的?
周伟焜:这个要慢慢地沟通,最重要的是第一年做不到增长翻番不会被枪毙。当然沟通也需要一些技巧,有一次适当的机会,我坦诚地和郭士纳讲,翻番很难,但大概每年可以平均增长45%~50%。
不过,无论如何必须确保企业的增长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一开始我们低估了中国市场的成长速度,而高估了我们的能力,也就是低估了在中国市场做生意的难度。整个20世纪90年代,情况都是这样。我还记得刚开始我们做了一个估计,说到某一个时间,业务量做到10亿美元,将会占市场份额的25%。那年我们确实做到了10亿美元,但市场已经是70亿美元的规模了。
还有一年,我们取得45%的成长,觉得很不错了,总部也说我们做得不错,但那年市场调查的数字说市场成长46%。如果企业发展速度不如市场发展速度,我们就有很大问题了,而且也没法赖账。CBR:再谈第二个问题。几乎所有的企业老总,无论外企还是本土企业,都谈到人才问题是他们最为关切和头疼的问题。你能否给他们提供一些IBM在这方面的经验?
周伟焜:有三条经验我可以和你分享一下。首先,在市场开拓之初,要有一个基础团队来帮助管理,否则临时在本地聘请一个人事经理,聘完了再培养,一下子就需要三年。第二,必须加快训练本地的员工工,我来中国市场的那年年底,我们庆祝培养出10位本地的经理,现在我们的本地经理已经超过1000位了,都是自己培训出来的,一线、二线、三线都是本地管理,这是十年做出来的。很多人觉得我们的人才本地化做得很成功。第三,我们现在又开始追求人才多元化,近期我把一些有可能不懂中文、但在一些领域里经验丰富的外国主管调进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高管基本上可以全部用普通话开会,但现在则要全部改为用英文开会。譬如,现在负责服务的两位管理人员,一个美国人、一个加拿大人,他们一个是以前负责全球战略服务的,一个供职于IBM加拿大服务部门,很有经验。他们带来很多新的经验和做法。
人才的问题是不断变化的,你不能一直在自己的框框里无法突破。
CBR:在中国做生意,政府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环节。你处理政府关系的方法和经验是什么?
周伟焜:中国本土的成功企业家很善于运用政府的政策,很多成功的本土公司能够了解政策,在政策上拿到竞争优势,在这点上我们和他们比差得远了。不要小看这个,这对很多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早期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对政府的看法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我们自己做生意好了,不用理会政府,有这种想法的企业大多失败了。第二类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政府是万能的,凡事要依赖政府关系,但这样同样不行。
一个外国企业必须充分了解中国政府要什么,它在做什么,你能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么,你不能要求它做什么,等等。我们在过去十多年时间内正在慢慢学会这些,现在,我不会向政府领导要项目,但是我会说,我们看到一些经济领域的变化趋势,我可以帮助你做点什么。和政府打交道要往这样的方向去努力。
CBR:先是在P C行业做到全球翘楚,然后转型IT服务,现在又提出“智慧的地球”理念,IBM一直以来都奉行领先市场的差异化、前瞻性战略。你们是怎样做到的?
周伟焜:我讲一下我们战略管理的思维和经验。第一,不要试图去做每件事,要挑可以做得好的、客户也愿意付出价值的事,所以IBM挑了服务和软件。第二,很多时候可以做到后来居上。比如PC,别人做了,但我们做得更好,不少技术也是如此。因此不要只寄希望发明了一个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就可以雄霸市场。相反,我们需要假定,如果找不到某个独一无二的技术,我们要怎样活下去?要活下去,一定需要办法创造市场,创造一些新的想法、用法,从而把整个IT行业带动起来。
1995年左右我们就看到了互联网技术,当时我们提出电子商务的概念,很多人问:“电子商务有什么产品吗?”我们说没有产品。“在其他人的机器上是否可以做?”我们说可以。“那你为什么讲这个概念?”我们说因为我们的能力比别人强。运用我们的能力,把市场这块饼放大,放大之后,我有能力在里面争取到更大的份额,而不是光想着抢别人的饼吃。
CBR:这就是所谓的蓝海战略?
周伟焜:也不是蓝海战略,我认为没有蓝海存在。蓝海六个月之后就可能变成红海,我们永远生活在红海里面,所以要一直保持创新的步伐。
CBR:说到创新,很多中国公司简单地认为创新就是工程师、高管脑子当中灵光一闪,IBH如何保持创新的持续性和系统性?
周伟焜:这个问题很好。第一,谈创新的时候,我们坚持创新一定不能局限于实验室。如果一家公司只是把创新的任务交给科学家和开发人员,那一定有问题,因为发明不一定代表创新,IBM每年有几千个专利,有多少可以赚钱?美国《商业周刊》连续两三年都把我们放在十大创新公司里面,这并不是我们的发明多,而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创新的想法、理念和能力。
第二,要有办法鼓励员工把他们的想法说出来,而且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想法会被接受。如果一家公司是所谓的“一言堂”,那么创新就只能在老板的脑海里面“灵光一闪”了。
第三,要有办法把创新的想法落实,而且有办法衡量它是否可以成功。很多时候一家公司都有短期目标和一些长期的想法,也希望做一些立足长远的事情,但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办法把想法变成能够按部就班去落实的实际行动,有没有这种人才、文化去实现想法。很多企业正是在这里迷路了。
举个例子,10年前我们提出向服务转型的时候,中国有很多企业也说要做服务,从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当时声称自己要做服务的企业是76家。但最终大部分的公司都回去做产品,或者消失了。
想法要实现,首先必须变成一个战略,然后由战略变成业务模式,由业务模式变成一个一个节点,CEO可以一步步去盯,直到它们成为现实。
CBR:在前瞻性战略和持续性创新的推动下,未来的IBH会是什么样子?
周伟焜:未来是两个方面能力的加强。第一,我们要超越信息公司的范畴。过去大家认为我们是一家信息公司,我们的谈话对象是CIO。现在则要迈进到更广、更宽的领域,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努力加强的地方。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战略集成的顾问,但我们要有能力离开我们所谓的计算机机房。
第二个能力就是全球运作能力的加强。要有办法运用全球能力来帮助解决问题,灵活调度IBM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希望在未来,我在中国给客户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可以很快把美国、欧洲、日本等不同地区的专家调进来,群策群力。如果有能力顺畅地实现这一点,竞争对手就很难和我们竞争。当然,这是不容易的。这将是我们最重要的两个未来发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