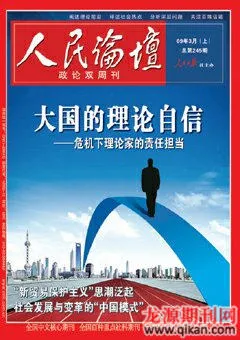“网络知情权”,一场虚幻的狂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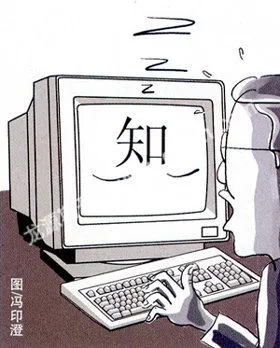
网络知情权不过是充满了崇高幻觉的虚拟权利
近几年来,网络一下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灿烂耀眼起来,仿佛没有了网络参与的社会政治,就不再可能可信、公正。很多人把社会政治民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网络信息的公开化上面。越来越多的人们觉得,网络信息不仅可以平等交流、自由公开,而且,因为允许普通民众的参与,它还可以突破一般的文化管制,打破传统媒介的信息垄断。无形中,网络信息变成了“新闻自由”的代名词了,无论什么事,最终是骡子是马,拉到网上溜溜。
但是最近的一件事情,似乎一下子打击了人们的网络热情:为了查清楚云南一家看守所“神秘死亡”的被拘押人的死因,消除网民对公安局对此事件调查结果的质疑,政府部门组织了一个网民调查团,让自愿组成的这支队伍,到现场去亲自查看。由耳闻到亲临现场、由网络监督到实际查看,大家于是觉得这确实是一种值得庆幸的进步。首先,人们千呼万唤的“知情权”终于被重视了;其次,网络监督显示了充分的重要性;再次,虽有官方邀请,终究代表民间,不是民主胜似民主。但是,网民调查团的实际调查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网民调查团更被指责未揭开真相而遭到广泛质疑。
且不管这件事情的种种曲折,单说网民们信誓旦旦地去现场查看这件事情,就足以看到网民的伟大自信。挥斥方遒、书生意气,似乎有了可以人肉搜索的“网络”、手机视频的“网民”,天下大事自然也就水浅鱼少、一目了然了。“网络”把“网民”塑造成了有这充分良好感觉的族群,把他们预设为“天然公正”、“纯粹道德”和“客观理性”的化身。可是,“‘躲猫猫’网络调查团”这件事,无形中却透露了另外一种信息:人们信以为真的网络知情权不仅不彻底,而且,也无法真正自主实现;更进一步说,网络的轰炸式绽开的信息,让人们做“网民”时觉得飞沙走石无所不能,做“公民”时依旧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我提醒大家不要把“网络知情权”当了真。简单地说,网络知情权不是具有现实性的政治权利,而不过是一种充满了崇高幻觉的虚拟权利。与之相应,把网络看作是获得政府公信力的终极平台,这也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是什么造就了人们对网络信息的偏爱
作为一种新媒介,网络文化和传统媒介文化之间确实存在裂痕。正是这种裂痕造就了人们对网络信息的偏听偏爱。
在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两种对立的文化生产方式,也就不得不处在两种矛盾着的文化生存之中:新媒介——私人娱乐;大众媒介——国家体验。
事实上,新媒介不断地鼓励着“私人娱乐”。新媒介也就成为“私媒介”。
与之相对,大众媒介则由广播、电视、报刊等等组成,由国家或者集团控制。由电话到手机,由有线网络到无线网络,由集体广场上面的游戏厅到个人手中的PSP,“私媒”不断地强化媒介产品的“追身”功能。作为一种商业叙事,“私媒”的基本原则就是日益把自我当作一个神话来进行叙述。这种私人神话与传统大众文化媒介对大众神话的支配形成有趣的对照。
换句通俗的话来说,网络媒介的特点就是自己娱乐自己。
在这里,“私媒”养育了这样一种狂热:每个人是如此的独特,自我是如此独立。“我”在这样的空间里面能够塑造出“真我”。
而与之相对,大众传媒则努力把这个“真我”纳入到“大我”之中去。事实上,大众传媒对“现实”的“反映”,很多时候是在进行“修改”和“重塑”。在这种修改和重塑中,“现实”的景象也就不自觉地被“魅力化”了。
不妨说,传统的大众传媒是典型的消费型文化传媒,商业利润成为直接的支配性力量。在这种利润主导、政治引领的文化中,一定程度上保证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指数的就是“社会的稳定感”。只有消费者具有了“稳定感”,他才不会囤积和保守,才会成为市场的有力支持。
显然,“个人娱乐”成为新传媒活动的基本动力,新传媒的使用者与制造者的区分被混淆了。信息的私人交换与免费使用,使得新传媒的文化传播大致“逃离”了市场与利润的直接捆绑,从而有可能成为对消费文化的一种反叛。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传媒已经分裂为两种基本形式:与国家叙事紧密关联的传统传媒(主流传媒),与私人叙事紧密关联的新传媒。前者立足于“消费意识形态”,后者则逐渐形成一种“娱乐意识形态”。而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媒体注重承担社会责任,而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它的社会责任感亟待加强。
所以,我说网络信息提供的知情权乃是一种幻觉,就是因为这种“知情权”说白了来自于“自娱冲动”。
“网络知情权”的生产逻辑:“娱乐化”大于“社会化”
人们在网络发布各种信息、相信各种信息,乃是出于对民主、公正的需求,确实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不能排除一部分人乃是出于一种“哄客”心态,一种“以对抗主流媒介为乐趣”的姿态。
其实,“网络知情权”的生产逻辑也并不崇高到哪里去,至少有两点非常值得关注。
首先,网络信息的生产具有“全球脑”的特点。这使得网络信息看起来丰富多姿,其实却千篇一律,乃是“千篇一律的个性”。美国学者彼特·鲁塞尔在1983年出版了一本叫做《全球脑》的著作。在这本书里面,他描绘了这样一种情景:全球的人们因为网络的使用而最终变成了共同拥有一个大脑——全球脑。这就是说,电脑和网络存储的信息和知识将影响人类的智力,也最终影响人们的体验。无论是艳照门事件还是周老虎事件,都显现了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我们共同关注网络的信息,也就共同成为这个信息的智力奴隶。
其次,网络知识的“传染性”大于“真理性”,网络舆情的“娱乐化”大于“社会化”。如果一味相信网络舆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仅不能带来执政公信力的提升,反而会被误导,会丧失接触真实社会生存的机会。事实上,“网络知情权”的虚弱,已经在这次“躲猫猫事件”中显露无疑了。不管你在网络上面怎样造次,也不过是创造了一个自以为苍茫大地我主沉浮的幻觉。这种幻觉用来自娱娱人足矣,用来指导社会,却立刻显示了它的无力和苍白。
有趣的是,对于网络知情权的偏执信念,反过来却滋生了一种新的不负责任的网络信息发布方式。有的政府部门认为,只要信息在网上公开,我们就公正合理、万事大吉了。殊不知, “质疑”已经无奈地植入到了网络信息的公众心理之中了,只要是政府部门发布,那就是不信、不理、不认。网络知情权已经在逐渐蜕变为大众的政治娱乐与政府部门的说教教条共同搭建的游戏。用网络知情权的方式代替真正社会权利的实现,这一点正是网络时代政治文化生活中值得警惕的地方。(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