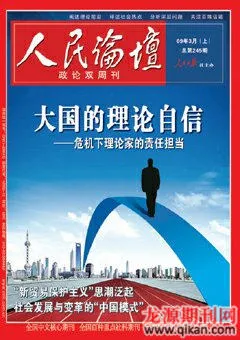农村基层治理再次走到变革关口

村民自治不应被斥为“民主的怪胎”
从1987年算起,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实施已有20多年。20多年来,有的人对村民自治的实践兴高采烈,他们在此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有的则嗤之以鼻,认为此举无足轻重,甚至斥之为一种“民主的怪胎”;还有的人则对村民自治的成效痛心疾首。
的确,村民自治及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远不是完美的,与法律的要求和人们的期望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各地村民自治的发展不平衡,实践成效迥异;真正严格依法实行民主直选、全面落实村务公开以及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的村数量依然有限;一些地方选举流于形式,压制、阻挠村民自由民主选举的事件屡屡发生,各种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有的地方村民自治甚至村民委员会组织本身也名存实亡。也正因如此,一些人对村民自治的实践及前景表现出深深的怀疑、忧虑、悲观甚至否定。
从实践来看,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国农村普遍完成了从人民公社制向村民自治制的制度性转换。作为农民群众的自治组织,也是农村基层基本的组织与管理制度,村民委员会已经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起来。尤其值得关注和肯定的是,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制度日益规范,村级民主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基层政权组织的民主日益显现出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中,村民自治制度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村民自治是在20世纪末我国改革之初及人民公社解体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制度特点:
其一是“城乡分离”。改革之初的村民自治没有改变城乡二元化的组织与管理体制,事实上延续了这一体制。
其二是“村社一体”。从实践来看,大多数村根据中央的规定,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实行“两块牌子,一班人马,交叉任职”。
其三是“组织封闭”。基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及承包关系,农民归属于一定的“集体”,享有相应的权利。村委会组织及党支部组织也是在这种集体范围内组建起来的。
构建城乡一体的社区制度,将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变革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天的村民自治已经面临全然不同的背景和条件,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面临新的变革。
首先,国家城乡发展战略从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要求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改革以来的村民自治的实施并没有改变城乡二元化的组织与管理体制,事实上延续了这一体制。不过,改革以后,党和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废除了城乡二元的粮食供应制度,改革户籍管理方式,鼓励农民进城及劳动力自由流动,推进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渐打破了长期城乡隔绝的局面,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特别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的同时,强调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其实质就在于党和国家正加大改革的力度,构建城乡一体的社区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
其次,不断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服务从农民自我服务为主向社会公共服务为主转变。随着我国农村政策从“资源索取”到“反哺农村”的战略转变,传统村民自治所承担的公共服务及公益事业将更多地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中央和地方也将更多地承担村民自治的财政及运行成本,乡村组织的工作内容和重点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的功能和作用也将进行重新定位。
第三,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过去,村民自治仅仅是拥有村集体产权的“村民”的自治。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逐步放开了市场,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及乡村内部的流动日益加快。农地流转的不断增多,不少人务工经商或移民城镇放弃土地经营,也有不少人远赴他乡承包经营,而一个村庄的居民也不再是世代聚居的“本村村民”,传统封闭的村落和集体组织日趋瓦解。随着农村社区体制的建设,我国的村民自治也将向居民自治转变。
最后,农村社区与经济组织逐渐分离,农村社区从生产和行政共同体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变。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打破了传统单一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或者说人们不再从属于单一的集体经济组织,社区也将不再是一种集体经济组织或生产共同体,而是从事多种经营、多种职业的人们的生活聚居地或社会生活共同体。
从历史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管理体制经过了从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制”到村民自治时期的“村组制”两次重大变革。如果说社队制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及城乡分离的需要而建立的话,村民自治及村组制就是在改革和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及打破城乡分割的过程中建立的。随着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及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历史性变革的重要关口: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的社区制度,将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变革。(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