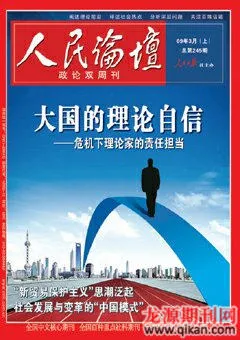寻求私权与公权的和谐
法律上把权利分为公共权利和私有权利两种。当公权与私权出现利益冲突时,公权无疑是重要的,但私权同样是一个公法主体不可侵犯的权利。
完善法律是消除公权侵害私权的必然选择
就公权与私权所涉及的“权力与权利”而言,我们能够在“权利”发生冲突中构建一种“国家与社会”、“个人与政府”互为对峙的解释格局。显而易见,在上述二元对峙格局中,私权并不是道义上的优位者。因而在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他们承担不等的义务,享有不等的权利,不能作为共同的群体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
在法治社会里,当私法主体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运用诉讼手段获得法律的救济,是值得赞赏的行为。但在实际情况中,当国家机关行使公权救济私权时,一些私有权利却需要我们出让。“上访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权利。法律赋予了公民上访权和诉讼权,但是如果公民的生命、健康、自由等权利因此受到公权侵害,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却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并不利于建立良好的执法环境和市场经济制度。国家机关在行使公有权利时如果由于采取了不当行为,进而侵害了私有权利,完全应该适用除《国家赔偿法》之外没有加以规定的其它私法,如《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
此外,行政与司法执法机关在对事实证明力的判断上,执法中工作人员有太多的难题(主观因素),立法既定的规则是无能为力的。恰因如此,对私有权利的判断也成为了执法工作中最能体现人的智慧的阶段。工作人员在行使国家的公有权力时,能否正确运用关乎法律与私法主体的命运。与此同时,这也使得国家机关在行使公有权利时将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执法官员个人素质较低无法确保公正;大量外化活动影响和干扰了执法者的客观与公正,使执法存在间接性和隐秘性;以及执法官员评判认定证据时存在误认事实的危险等等。因此,完善法律是消除公权侵害私权的必然选择。
在法治国家中,通过分权制度来划定和规范公共权力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权力,用法律确定权力角色,保证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权力,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只有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和个人都严守权力界限,才能形成井然有序的法律秩序,也才能出现理想的良好司法环境。故意曲解法律的执法者,其以执法为借口侵害私有权利的行为会伤害法律的威严。
让公权与私权在新的层面上更加和谐、完美地运行,已经成为新的时代课题
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生存体,私权与公权的和谐共处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必须。我国现行宪法将实行法治和保障人权确定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治国方略。这就意味着国家要以法律和制度规范公权力的行使,防止公权力滥用和对私权利的侵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共权利的行使往往会与个人权利的行使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有时甚至要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公权轻私权的传统使私权长期以来没有生长、发展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政企分家、还权于民,使得市民社会逐步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然而,由于我国受传统的影响过深,加之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直接转变而来的,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因此在市民社会生活领域仍然留有大量的公权力,使得弱小的私权利时时受到强大公权力的威胁,结果导致公权力的庞大与私权利的弱小并存,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介入与私权利对公权力的依附并存,公众对公权力的敬畏与对私权利的漠视并存。这也就使得人们在享受发展带来的丰厚成果的同时,无法回避公权与私权在社会发展转型相伴而生的问题、缺憾乃至阵痛。
30年来,我国因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日趋暖和,社会和谐方面表现出的问题正日益凸显和复杂。尤其在社会启动新一轮增长和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公权与私权交替运行的情况下,这种和谐的要求和感受愈加急迫。得到保障的公共权利,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权利,从根本上讲这二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让公权与私权在新的层面上更加和谐、完美地运行,已经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也正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共识和日益迫切的愿望。
实现公权与私权的更加和谐,不仅包括经济、阶层、政务等方面的和谐,还包括区域、城乡、文化以及生态的和谐等一系列更具体的内容
社会公共权利如果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的公共权利与个人权利定会实现和谐的统一。这正是法制精神之所在。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要实现公权与私权的更加和谐,还有一条漫漫长路要走。这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经济的和谐、阶层的和谐、政务的和谐这些最基本的部分,更包括区域的和谐、城乡的和谐、文化的和谐、代际的和谐以及生态的和谐等一系列更具体的内容。就目前情况而言,虽然我们已对很多方面的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并已在进行调整和改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在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各个环节,还没有达到有机的衔接,运转顺畅,尚需进一步调整和理顺;在直接关系到政府形象、行政效率、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的政务和谐方面,虽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且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框架,但是执行、落实和完善上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城乡之间,无论生存环境还是生活质量,差别还很明显;各阶层之间,新的阶层分化已渐成轮廓,各阶层成员的利益关系亟须调整,就业再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弱势群体的日趋边缘化等都对社会构成愈益明显的压力;在文化环境方面,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接受文化教育的条件还不容乐观;在生态方面,不少人的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还很淡薄,为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经济指数而急功近利的做法还很普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依然相当严重,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仍旧遭遇无法承受之重;有法不依、执法不公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随时都有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干扰社会和谐,乃至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构建社会和谐任务还相当繁重,它需要整个社会各个阶层、所有群体的智慧和合力,既需要政府的策略、措施、决心和力度,更需要全社会每一个个体的重视、协作、行动和努力。(作为分别为中国人事出版社副编审,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