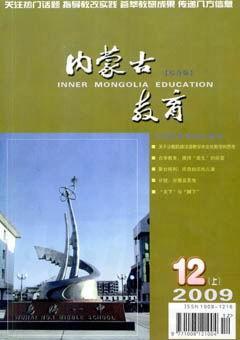瓦楞草
包光潜
旧房子越来越少了,瓦楞草也越来越少见了。每次回家或者游历乡村,我总是要寻觅那些褪去了火性的老屋,尽管满目沧桑,但我还是执着地用锥子一般的目光勘探那岁月的流痕,凝望瓦沟里摇曳的瓦楞草。
瓦楞草最旺的时期应该是在夏天。进入雨季之后,老屋顶上终日湿漉漉的,雨水中溶解了大量的矿物质,随着雨水慢慢地渗入瓦片中。然后一点一滴地再往瓦沟中转移。瓦楞草似营养不良的小孩子突然有人馈赠了上等的牛奶,它便迫不及待地吮吸起来,让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着营养,这叫肥得冒油,富得淌水。因此,一个雨季之后,瓦楞草挺拔地站在屋顶上,当让你刮目相看了。大多数人不会在意屋顶上那些没有作用的瓦楞草的。瓦楞草总是在人们的记忆之外,不为人所注意,更不会引人注目了。我从小就在孤寂的环境中生长的,许多行为习惯有别于常人。这种在旁人看来纯属标新立异的行为至今如此。俗话说,生成的像,晒成的酱,想改变也是非常困难的。我常常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很喜欢伏在窗台上,两眼望着窗外,看雨是如何织成密而不透的帘的。然后透过雨帘,仰望别人家屋顶上的瓦楞草。雨中的瓦楞草往往并非你想像中那么好看。其实也是很狼狈的。不是被风吹过去,就是被雨帘裹着往下垂坠,甚至耷拉着趴在瓦背上。但雨水之后,它们个个都鲜活过来。被雨水浸润过的绿比阳光下的绿更加水灵,让人的身体产生饱胀的感觉。看着瓦楞草茁壮成长,而我的身体愈发单薄、孱弱,我的目光自然地垂落下来。我明明知道,雨季之后,瓦楞草好景不长,等待它们的是秋风萧瑟、冬风猎猎。但我还是想,如果有一场雨能够让我的身体也茁壮成长起来,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其实,我是很幼稚的。人的生命无论如何是强不过任何一种草的。要不然怎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
我在皖南行走时,对那些古旧的徽派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高的马头墙,青青的瓦当,以及浸渍了岁月风流的砖雕、木雕和我的家乡屋宇有异曲同工之妙。只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古旧的屋宇是同门同宗、同流同派的,只是在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实用性的变化。我家的老屋原来也属于徽派建筑。我容不得的是那些仿古的徽派建筑。连瓦当都是用水泥造的。不要说久年风化之后,有种子生根发芽了,就连种子停留的时间都不会给予的。这样的房子,即使千年流蚀,也不能生出瓦楞草的。没有瓦楞草的老屋总是令人别扭的。也许威猛高大,却生不出亲和力,只好敬而远之。
也许在别人眼里,瓦楞草在屋宇上摇摆有失风雅,不如剪去,或者从根本上不给它生存的地方,让它没处着落,无处生根。可是,我不这样以为。无论是徽派建筑,还是其他什么流派,有了瓦楞草,才说明它已经有了年代了。一个有了年代的房子,才会有生灵。就连那些卜居在此的蛇们都被称为家蛇了,何况是人呢?
瓦楞草当然有它衰败的时候,甚至衰败得一塌糊涂,但它们绝不会死亡。它们就像冬眠的动物蛰伏起来贮存能量,让弱如游丝的生命延续下去。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递的。瓦楞草生命历程似乎向我们人类昭示着什么。昭示着什么呢?
瓦楞草在炊烟中见证了活生生的历史。只要我看见那些老房子,我必定在寻觅瓦楞草。
——兼论《园冶·屋宇》书写中造园者与工匠之间的主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