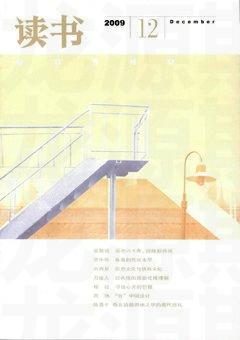寻找心灵的慰藉
程 虹
“一只苍鹭独立于湖畔,神态安详。风攀上了她的后背,掀起几缕羽毛,但她纹丝不动。这是一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鸟。她已久经风霜。经历了大洪水,现在湖水已经回落,这只纯种的苍鹭一直守候在家园。或许,这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站姿,一种家族门第的遗产。” 当代美国作家及博物学家特丽·T.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 1955— )在其代表作 《心灵的慰藉》中,以大苍鹭为参照物,寥寥数笔揭示了人类在变幻莫测的现代社会中应当具有的一种将身心与自然界融为一体的定力。她提醒我们,这种内心的定力实际上是人类自身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只是被现代的色彩冲淡了。
《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Refuge: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1991),被誉为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它讲述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当人类面对诸多不稳定的因素,甚至灾难和人生悲剧时,如何从自然中寻求慰藉。
威廉斯生长于美国犹他州的大盐湖畔。大盐湖是一片超现实的风景,沙漠中无法饮用的一池碧水。然而,这貌似无用的湖泊却与美国最大的水禽保护区——熊河候鸟保护区的鸟类密切相连。如同绿宝石般环绕着大盐湖的湿地,为北美的水禽和沙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自然繁殖地,那里有二百多种鸟,是春秋之季鸟类迁徙中数百万只鸟的栖息之地。这些鸟类与作者共同拥有着一部自然史。作为摩门教徒,威廉斯家族已经在盐湖畔繁衍了六代。但是,由于位于美国核试验基地的下风口,作者家族的女性多半都患有乳腺癌。她的祖母、外祖母、母亲及六位姑姨都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其中的七人最终死于癌症。因此,作者称自己的家族为“单乳女性家族”。与此同时,威廉斯发现盐湖水在不断地上涨,从而使熊河候鸟保护区的鸟类受到威胁,有些鸟类可能从此消失。人类的悲剧与自然界的悲剧同时上演。
此情此景,使作者在写作中把内心的情感世界与自然的变化联系在了一起。这些类似日记的优美散文,记述了作者陪同已处于癌症晚期的母亲在大盐湖畔走过人生最后一程的经历,母女二人通过在盐湖畔观察自然界的动植物如何应对残酷命运的过程,来面对个人的悲剧,抚慰受伤的身心。湖、鸟、人作为不可分离的总体,成为这部书的主角。自然不再是陪衬或背景。
这是一本动人的书。当作者动手整理在盐湖畔的日记,准备出书时,她本人也被确诊为乳腺癌,年仅三十四岁。她翻开这些记录母亲弥留人世时的日记,鸟的羽毛、盐湖畔的细沙、鼠尾草的叶片纷纷从日记本中落下,触动了她内心的悲痛。如她本人所述:“我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医治自己,是为了面对我尚无法理解的事物,是为了给自己铺一条回家的路,因为我认为,‘记忆是唯一的回归家园之路。我一直在避难,这个故事是我的归程。”
一
故事的开端是大盐湖涨水了,它的湖面海拔即将超过熊河候鸟保护区的海拔,这意味着熊河候鸟保护区将被淹没,那里的鸟类将沦落为“仓皇逃离的难民”。与此同时,作者身患乳腺癌的母亲黛安娜病情恶化,癌症转移到了腹部。可是她并没有及时就医,而是隐瞒病情,去了大峡谷。因为,对她而言,在大峡谷及科罗拉多河上度过的日子会带来一种精神的复活。穿过古老的岩石群的经历赋予她希望,使她能够承受任何必须面对的事实。在坚强地挺过手术之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黛安娜决定做化疗。透过母女二人的对话,可见她们应对病魔的独特之处。母亲对女儿说:
或许,你能帮我想象一条河——我可以把化疗想象为一条河,它能够穿过我的身体,把癌细胞冲走。特丽,你说,是哪条河?
“科罗拉多河怎么样?”我说。
几周来,我第一次看到母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大自然赋予她们母女战胜病魔的定力和毅力。母亲在与癌症搏斗之中感到生命得以浓缩,每天都在用心生活。作者看到母亲从自然界汲取的开朗达观,看到母亲全部的生命节奏都在加速,看到母亲“是一只翱翔于天地之间的鸟,羽翼上承载着新获取的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
然而,随着大盐湖水位涨高,湿地被淹没,熊河候鸟保护区办公室被迫关闭。与此同时,作者母亲的病情再度恶化。在强撑病体,为全家人准备并度过了最后一次圣诞节聚餐之后,作者的母亲在家中病逝。然而,在作者的笔下,母亲的离世是一种平静的、闪烁着精神升华的过程。守着奄奄一息的母亲,作者感到房间里的光暗淡下来,她突然想到母亲会等到日落之后再过世,而那天的落日绝妙无比。一片杏黄色的光闪烁在窗外远处紫色的群山上。她告诉母亲那是多么美丽的日落——她想起了母亲曾为壮美的日落而拍手赞叹,母女二人曾在夕阳下携手行走在齐肩深的向日葵中。
母亲是笑着离去的。在母亲去世的当天晚上,作者走到室外,眺望夜空,将她内心的感触浓缩为这样两句话:“一轮满月悬挂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中。那是母亲的脸在闪闪发光。”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那首描述寒崖夜景的诗:“众星罗列夜明深,崖点孤灯月未沉。圆满光华不磨莹,挂在青天是我心。”东西方文化的相同之处在于,人类及人类的情感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才能达到升华和永恒。威廉斯感叹道:“我那拥有肉体的母亲已经走了。我精神的母亲依然存在。”
母亲去世后,作者发现了家中男人们的变化,她的父亲和弟弟再也不打猎了,“他们的悲伤之情已经变成了怜悯之心”。大悲之后呼唤出的是大爱。他们从个人的情感世界走向了容纳万物的慈爱境界。
最后,大盐湖的水位终于得以控制并回落,在春季的鸟类迁徙开始之时,作者与丈夫荡舟于大盐湖。她想起了去墨西哥过亡灵节的经历:在墓地,一位手捧万寿菊的老妇人,她的五六位亲人都长眠于此。老妇人将手挥向天空,用西班牙语告诉作者—— “非常漂亮……我们头上的蓝天……飘浮着玫瑰般的云朵……亡者的灵魂与我们同在。”离别时,老妇人送她一支万寿菊。那是作者的母亲每年春天都种的花。在大盐湖的中心,作者取出精心保存的万寿菊花瓣,撒入大盐湖。逝去的亲人将与自然界的山水同在!大盐湖,“承载我忧伤的港湾。我心灵的慰藉”。
二
在《心灵的慰藉》正文之前,作者引用了美国诗人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1935— )的诗《雁群》。这首诗勾勒了一幅生动的图像:地球在运行,太阳正在越过风景如画的大地,高高飞翔于碧空中的雁群,正在匆匆地赶着回家的路程。一个完整的世界展现于你的面前,它像雁群那样向你呼唤,反反复复地提醒你,你是家中的一员。可以说,这首诗已经暗示了此书的主题:自然界是一个血脉相连的生态体系,所有的成员都共同栖生于这个大家庭之中。现代文明应当重新唤起人类与土地的联系,人类与整个生态体系的联系,并从中找出一种平衡的生活方式。
人类过于强势的发展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甚至给自己带来病患。博物馆被抽空的鸟蛋标本使作者联想到如今被人类过度利用的地球,几乎也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如同她那身患子宫癌的祖母所说:“空空的鸟壳意味着空空的子宫。大地出了毛病,而我们也不健康。我从地球的状态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体状态。”
从椋鸟的行为中,作者看到了人类自身:“我们的人数之多、我们的争强好斗、我们的贪得无厌以及我们的冷酷无情。像椋鸟一样,我们独霸世界。”她生动地描述道:“如同赶走‘低收入的房客一样,我们已经把野生动物赶出了城区。”
威廉斯关注的还有鸟类赖以生存的湿地。湿地是地球上最具繁殖力的生态系统,也是受到威胁最大的生态系统。水禽生物学家告诫说,在大盐湖退水之后,熊河湿地的重现需要三至七年,而全面恢复的过程需要十五至二十年。但事实上,那里的生态系统是不能复位的。陆地上任何其他的生态系统都无法取代或吸收这片复杂的湿地。如同专家所言:“有一种临界,我们一旦跨越,便无法恢复。”
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最缺乏的另一种力量则是沉静。远离自然和安宁的生活,悬浮在路上或是空中,大地和空气都充满着躁动。威廉斯对此深有体会:“我感到恐惧是因为与整个自然界相隔离。我感到沉静是因为置身于天人合一的孤寂之中。” 从加拿大黑雁的夜间飞行中,她领悟到,驱使它们向前的是沉静。如果说,美国自然文学的先驱梭罗在荒野中看到了希望,那么威廉斯则信奉:“沉静是我们内在生活的力量。”
三
《心灵的慰藉》之独特,不仅在于威廉斯的特殊经历。她独树一帜,将不同的鸟类作为每一章的章题,鸟与湖和人共同编织着一部大地的故事。
第十章《雪》将自然的风景与心灵的风景巧妙地融为一体。威廉斯母女二人来到冰封的大盐湖畔。那片冰天雪地令母亲想起了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上天有眼,暂时不言》。小说的主人公被诬陷为杀人犯,在西伯利亚犯人集中营度过了余生。母亲让女儿看看这个小说,并解释道:“我们每个人都得面对我们自己的西伯利亚……我们必须与自身内心的孤独无助和平共处。没人能解救我们。我的癌症就是我的西伯利亚。”此时,突然有两只像燕雀大小的白鸟飞入她们的视线,在融化的雪地边上觅食。当确信眼前的鸟就是繁殖地在北极冻原地带的雪时,母亲在沉思中问女儿:“你说托尔斯泰是否也知道这些鸟呢?”母亲的思维是跳跃性的,作者的想象力亦极为丰富。在另一章 《小天鹅》中,威廉斯在盐湖畔耗时许久,精心装饰了一只被洪水淹死的白天鹅,可以说,那是她为即将逝去的母亲准备葬礼。然后她躺在它的身旁,想象着这只白色的大鸟展翅飞翔的情景:“我想象它们飞向南方时在秋天晴朗的夜空所看到的璀璨的星光。我想象着它们在飞过一轮明月时的身影。我想象着湖光潋滟的大盐湖像母亲般地呼唤着天鹅,而突如其来的风暴使得它们生离死别,造成千古遗恨。” 在暮色中,她终于离开了那只天鹅,因为“它像耶稣遇难的十字架,留在沙滩上。我不忍回头”。母亲去世后,威廉斯从自然界又找回了母亲的身影。在处理遗物时,母亲的梳子上那一团黑色的短发,不由使她想起了外面的鸟。母亲生前曾提到死后想变成一个鸟巢,她成全了母亲的遗愿:“我轻轻地推开玻璃门,走过雪地,将母亲的那团头发铺在白杨树的枝头——
为了鸟儿——
为了它们的小巢——
当春天来临时。”
威廉斯的文字令人回味无穷,同时又给我们以希望。“当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写道:‘希望是只鸟儿,栖在心灵的枝头时,她是在像鸟类那样提醒我们,要放飞我们心中的希望,并梦想成真。”
威廉斯现为犹他州自然史博物馆的驻馆博物学家及犹他大学兼职教授。曾获美国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荣誉奖、华莱士·斯蒂格 (Wallace Stegner) 文学奖以及美国联邦国家野生动物保护特殊成就奖,是美国自然文学、生态批评及环境保护等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她的特殊的经历及丰富的想象力使其作品跳跃性很大,这就为翻译甚至阅读她的这部作品增添了难度。不过,作品的魅力还是吸引着我们追随作者的情感一路领悟下去,难以舍弃。或许,我们还会在威廉斯的感召下,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的慰藉”,如她所述:“那些我们熟悉并时常回顾的风景成为抚慰我们心灵的地方。那些地方之所以令我们心驰神往,是因为它们所讲述的故事,它们所拥有的记忆或仅仅是由于风景的美丽,而不停地召唤我们频频回返。”
(《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及家族史》,特丽·T. 威廉斯著,程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