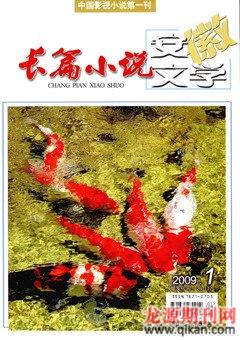河边的小屋
高建新
月光追逐着我。
我的女友就像月光般洁白且又可望而不可及,可是我们今晚就要在小屋里相见,而小屋也已近在眼前。我心儿乱跳,战战兢兢,甚至有一种负罪感,因为,我比她大多了。
小屋的木门虚掩着,没上锁,我轻轻一推,门开了。这是一间仅有三架的低矮小屋,圈里养着两只猪崽,堆放着锄头钉耙之类。猪宝宝听见有人进来,以为主人来喂食,高兴得叫唤了起来。我吓了一跳,但不久它们就平息了,也许它们一眼看出我并不是它们盼望的人,更没有带来好吃的,而使它们大失所望。我定下神来,仔细察看小屋的每个角落,并没有发现我年轻的姑娘,显然,她是迟到了。
我赶紧把门关上,将自己关在屋里。我记得很清楚,她反复叮咛我,必须在晚上八点半以后到达约会地点,只可推迟,不可提前。因为,在此之前,她的阿爹或阿妈必定要到小屋里来喂食,如果被撞见,肯定要被当作小偷抓起来,到时,也许会立即令她的两个哥哥将我生擒,吊着打。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立即擦亮火柴棒捧照手表,啊!七点五十五分,来得太早了。好险,真的好险啊!
小屋门前是一条小路,仅隔这条路,就是她家的正屋——三间平房的后门。从门缝里,能清楚看见对面的动静。我希望那扇后门现在最好不要打开,因为万一她老爸拎着猪食桶拿着铜勺来喂猪咋办,我总不能往猪圈里跳吧!
突然,我听见后门吱呀一声,门开了。我的心猛跳,慌乱起来,但没等我弄清楚怎么回事,后门又关上了。我在门缝里隐约见到,原来是她妈妈出来倒洗碗水。
我终于松了口气,又观察了一会儿,没有一丝动静。我想,躲在这里毕竟撞见的危险系数比较高,还是到外面转转再来,但又一想,万一碰上行人、熟人或邻居怎么办?说到底还是这里安全些。
不知过了多久,还是不见我的女友。她今天是怎么了?难道她记错日期或时间了吗?不!不会的,这时间地点都是她定的,如果记错的话,也只会是我自己。唉,是不是变卦了?前期听梅私下对我说,一个在海军部队当兵的小伙子,他父母托人找上门来,说是要看看小姐。梅说,我还小,不等五年不谈这事。那媒人说,五年太晚了,那时,说不定我家小官人已经退伍,或者早就升官了。她妈说,还是升了官再来说亲的好。小兵复员还是回家种田,我家丫头兄妹五个,她最小,是“末梢把”,娇得很,又不会种田。那媒人听罢,再也没上门。
我思量,要真的变卦了,梅会把这绝密情报透露给我吗?不可能!又一想,是不是那军哥鸿运当道,官运亨通,突然提干了呢?但提干又有什么了不起?梅会这样势利?不会的!
正想着,我从门缝里见对面后门慢慢打开来,但不见人影,只有地面上一个东西向前移动。我睁大眼睛,原来是只小黄狗,它专程出来撒尿的,但似乎尿还没撒完,小黄狗就对着小屋门嗅了几下,好像发现了敌情似的,狂叫起来。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后门开了,并射出一道柔和的灯光。我分明见得一个五十来岁的短发妇女走出来,环顾四周,对狗喝道:“没人没鬼的,你发什么狗疯?快回来!”如此一喝,小黄狗乖乖地跟她进了屋。
我双腿一软,靠在门边上瘫了下来,头一晕,似乎要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黑暗中,一只柔嫩的小手伸过来,拉住我的手,小声问道:“嘿!你晚饭吃了没有?”
“什么?”我好像在做梦,“吃过了,噢,还没呢!”我语无伦次。这才想起自己晚饭还没有吃。如此激动,自觉好笑。
“你先吃点馄饨,”女孩说,“刚从锅里捞上来的,太烫,我把它放灶面砖头上凉了一会儿,快吃吧!”
“没有筷子怎么吃法?”我很为难。她却说:“用手抓着吃就是了,只要不吃到鼻子里去就行。”
我便用手抓着吃,像泰国人吃抓饭似的,不过我是吃的抓馄饨。女孩又问好吃伐?我说好吃。女孩便向我解释迟到的缘由。原来,今天她的几个同学来玩,大家便动手洗菜、择菜,围在一起裹馄饨,费了许多时间,吃好了,又要讲讲话,所以弄得晚了。她估计我早已来了,但只有将同学们送走才能赴约,没法子,只好让我苦等。不过,她早已主动去将猪仔喂饱了,避免她父母到小屋去,将风险降到最低。因为,与其说我胆大,不如说她心细。我还没吃完,只听女孩说,不早了,我要回屋了。我说还没跟你说几句话呢!她说,见着面就好了,还要多讲什么?
我们依依惜别,带着无比的浪漫和幸福。在返回途中,月光没有追我,只是给了我更多的抚慰。后来,我问女孩,为什么月光老是盯着我?而有时很严厉,有时又很温柔?女孩立即答道:“月中有玉兔,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属兔的吗?”我恍然大悟。
这便是我难忘的初恋。
后来,我跟那女孩结了婚,过着幸福的日子。许多年后,我的夫人对我说,你还记得那次小屋惊险的约会吗?其实,我妈知道你躲在小屋里,只是恐怕你尴尬,有意不点穿罢了,你回过头去想想,是不是?
我的岳母已去世数年,而那小屋也早就拆除。我怀念岳母,也怀念小屋。幸福是一种感觉。我们没有过高的期望,只求平平安安,所以幸福总会常相伴。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