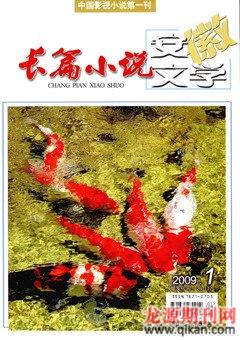精短散文二题
姚克连
钓黑鱼的人
他,是城南郊区有名的钓黑鱼的人。
长长的竹竿扛在他的左肩上,竿梢上不长的比一般人钓鱼线稍粗的线头上还拴着半条青蛙腿。半截子蓑衣披在那件老蓝布装上,雨水沥沥地往下滴。“狗日的,今天倒霉、倒霉。”他一边往回走,—边自言自语地骂着。
我知道,他今天未钓到一条黑鱼,心里窝着气。他就住在隔我家一个汪塘的那条小街上。女人算半个街混子,好吃懒做,每天下午都要弄个小纸牌看看,烟瘾也大(当然只有块把钱的一包烟);生两男一女,女儿外出打工嫁人了;两个儿子都只小学毕业,大儿子三十大几仍是光棍,靠拖板车挣点钱,二儿子则在火葬场给死人忙活,混口饭吃。
几年前夏天一个中午,他扛着鱼竿从我家门前经过,兴许他喝了几杯酒,脸红红的,一屁股坐在我家的大门槛上。他对我说,我已钓了好多年黑鱼了。春天里黑鱼下崽,是我最高兴的季节,我站在芦苇丛里,只要把小青蛙往钩子上一吊,在小乌子(即刚生的小黑鱼苗子)群不远的地方抖几抖,一条黑鱼就能拽上来。最大的,我钓过7斤6两一条的,那时黑鱼便宜,拿市场卖了,也够我一家人过十来天日子。他还对我说,夏、秋季节仍能钓到黑鱼,只不过现在城市扩大,不少沟塘被填了,水域越来越小了,污染也越来越厉害了。我想到离城更远点的地方去钓。
大前年春月,那天一早他就在我家不远的东南角池塘里转来转去,待我下班回来,我看见他那根有点发黑的竹竿拎起来,一条摆弄着小扇子般尾巴的黑鱼被他提到旁边的草丛里。我说,“钓黑鱼专家”今天又有肉吃了!他笑眯眯地用芦苇从鱼腮穿进去,拎在手里,一路颠簸着回家了。
秋雨凉凉的。我蓦地发现,他那远去的背影,已被风雨弯成了一张弓子,就跟他的钓鱼钩似的。
北戴河沙滩的夜晚
明天,由诗刊社举办的“北戴河之夏全国诗歌笔会”就结束了。今晚一吃过晚饭,我们便三三两两向海边走去,想尽情领略北戴河沙滩的风情。
火红的太阳沉入了海底,岸边各式华灯齐放光彩。一线数里长的沙滩上、浴场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像是千万只海豚随着涌动的波浪追逐着、跃动着、戏嬉着、喧闹着;男女老幼都是海无拘无束的孩子、海随意绽开的浪花。那一双双胳膊、一双双脚在划动着、拍打着,那一个个救生圈在漂浮着、转悠着,海水被他们玩得上下跳跃,左右闪晃,不住地向沙滩送来潮水般的笑声。年纪大点的人坐在沙滩上,任潮水一次次抚弄着自己的双腿,年轻的女孩子把身体埋在沙里,享受那份潮湿、那份清逸……
我没有下海,只能卷起裤脚,站在开始涨潮的沙滩上。无边无际的海给我送来一阵阵咸咸的湿湿的凉凉的风,此刻,我再也感觉不到酷暑盛夏的炎势,只觉得我的身体里注入了从未有过的温馨;海潮已经打湿了我,我的一双光脚就一动不动地踩在沙子上,一个潮的浪头从脚面打过去,马上又从脚面上回下去,间隔几秒就这样一个来回;当潮水从身后顺着沙子慢慢退下时,我就感到有种无形的手把我脚底的沙子一点点掏空,弄得脚板痒痒的、酥酥的。我随着不住涨潮的水向后移动,就让一只只无形的小手不住地掏我脚底下的细沙子。
不知不觉中,已快夜晚12点了。来到岸上,各种表演正在热闹着。人、沙滩、海,共同演奏生命的恋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