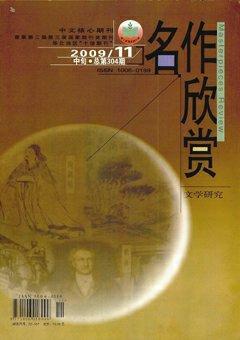梦幻与追寻
路 遥 倪素梅
关键词:梦幻 寻找 精神追寻 形而上意味
摘 要:须一瓜《穿过欲望的洒水车》在叩问人生、寻找爱情的精神层面上构成了对理想世界的想象与观照,言说与烛照了一种较为“纯粹”的精神品质,从梦幻与追寻的角度传递给我们一种富含哲理却又令人痛楚的形而上意味。
小说在揭示生活的“真实性”与“可能性”两者之间,我们可以并不臆断地说,追求小说真实性(人性的真实、经验的真实、生活的真实等)者居多,而言说小说“可能性”的作品仍居少数。许多小说因囿于“存在”、局限于“真实性”而过分关注世俗的“此岸”世界,从而使作品缺乏对理想的“彼岸”世界的想象与观照,不能引领我们的灵魂在异度空间上升、如蝶般飞舞翔弋。
须一瓜《穿过欲望的洒水车》剥离当前平面化的形而下,展现“和欢”梦幻般的对一分情感的焦灼坚守与执拗等待及找寻。在极度物欲的纷纭现实中,这篇小说的写作进入了富含哲理的形而上层面,在叩问生命、找寻爱情的精神界面上构成对别样人生的真实言说,在梦幻与追寻中,烛照的是一种较为“纯粹”的精神品质,通过文本传递给我们的是寻找中令人痛楚的无尽“意味”。
《穿过欲望的洒水车》讲述的是一个妻子寻找丈夫的故事。和欢的丈夫祝安在一次离家之后就失踪了,在无数次的出资寻找过程中和欢均寄予着虽渺茫却坚定的期冀,然而小说最后无情的现实——即小说中的真相──是丈夫死于一次车祸,简简单单即可以搞清的事实却被不负责任地延误四年才得以揭示。双重的事实真相于和欢而言是一个惨痛的打击,一个无法承受“生命之轻”的重创!于是和欢驾车开往大海之中走向绝望后的死亡!
须一瓜小说中的人物经常被置于各种悖论式的极端情境之中。《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的和欢亦是如此。和欢几乎日日在寻找失踪的丈夫,在为和欢的执著和追求而有些感慨唏嘘的同时,我们却又发现她在“精神追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灵与肉的剥离:作为清洁工的和欢属于下层劳动者,但她身上却有很多的都市色彩与超越她身份的浪漫情调(如打唿哨、做爱时咯咯笑、常坐在林木掩映的园中静思等),她有对爱情的“找寻”,有生活在喧嚣都市中的漂泊感及内心的孤独与“焦灼”以及寄予其中的对于爱情的无望的甚至是绝望的“坚守”——对失踪丈夫长达四年的痴痴的找寻与等待;但和欢对爱情坚守却将精神与肉体分开来,一方面她拒绝一贯对她很好而又优秀的吴杰豪的求婚,但另一方面,她又与一些在这个都市流浪的陌生男人在那个充满浪漫情趣的“世外桃源”式的小木屋淋漓恣肆地放纵着自己的身体与来自肉体的不可抗拒的欲望。于是她执著追寻的精神与其生理的欲望形成了一种对立。过于圣洁的形而上的精神的烛照并没有消解掉来自肉体上的骚动,而且和欢常为了维护一分圣洁和纯正、拒斥来自肉体的冲动,以防肉体之需对安宁的心灵世界造成侵扰,这确实是一对矛盾,和欢即被置于这一悖论的尴尬情境之中。复杂的内心世界便在这让人难过伤感心痛怜惜之中尽情呈露无遗,而叙事中的张力亦因此趋于极致。
小说以“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为题,无疑是一种隐喻。“穿越”“欲望”,要寻找什么?被欲望左右的红尘中芸芸众生内心的渴望是什么?从文中的描述中不难发现,那是一种对自然对淳朴的向往和追寻,是身居现代化喧嚣都市身心漂泊无归的人们寻找心灵安宁的梦想。
首先,在小说描写中不难发现的是,和欢用来暂时栖居之所,位于闹市区为外界喧闹繁杂所遮蔽不会被人“轻易”发现的类似于“世外桃源”式的小花园内,“这里就像城市里的村庄。非常小的村庄”,“有时高高的小叶桉树梢会越过一些汽车的喧嚣,但经层层树木花草的过滤之后,反而显得有点不真实”,在这“树木深处”“花草深处”的是一个由“扎成X图形的及膝竹篱笆”围就的栽着“各色三角梅”的小院;这儿弥散的是淡淡的乡村田园味儿的诗意,以及充满古典与原始情韵的木小屋;有带着太阳味道的碎瓦片和碎瓦片缝隙中的青草以及有点潮湿的泥土;有月色星光掩映令和欢舒缓节奏享受独自遐思的旧躺椅,有可以纵情的放松与无所顾忌的自由及解除一切禁忌后的恬淡与闲静;透过此种“安然”与“静谧”我们似乎看到了城市中的“桃花源”——那一美好、和谐、纯净的令人神往的世界。
其次,在文本中贯穿始终的即和欢做爱时“掩面格格格地大笑”(笑个不停)的细节可能会令人思之而不得其解。作者反复提及这一细节是否另有寓意?是对过于约束人的行为的当下规则及无视人的各种天然而正当的权利的社会规则的一种颠覆,还是对无拘无束的一种古老原始的纯净生活的向往?再次,小说中有一细节即“和欢”将“园”中钥匙真诚而慷慨地交给一对正在相爱着的青年男女,告诉他们,这一夜可尽情使用,之后将钥匙放在门前花盆下即可。这一暗示性的细节似乎含有“天作之合”的隐喻。令人想起《诗经》中之“仲春二月”,男女携手踏青郊游,相悦后乃做“天作之合”的浪漫、天然与纯真。这一“和谐欢乐”之景的回望与期冀其实是对现实即现代社会的无奈与失望,流露出作者对“桃花源”式田园生活的留恋以及一种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对“桃花源”式田园生活的扼杀与摧毁的反叛!小说在叙述和描写到和欢的工作性质时,我们会注意到文本中不断出现的字眼是“梦”及“梦幻”。“寂静的大街像残梦一样简单”,“在空无人迹的大街,她把车慢慢地、轻轻地——突突突突地开进每个人的梦的边缘”,“把水均匀地洒过去时,整个大街的马路,就像梦一样黑黑得发亮了”,“坐在驾驶室的和欢总会通过后视镜往后看,一直往后看,就像紧贴着梦的感觉”。同样我们可以藉此观察出作者对曾有的美好梦幻在现实面前不得不幻灭的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与来自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忍舍弃。在《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看似不急不徐柔婉恬淡的叙述与描写中其实包含着作者须一瓜对“失乐园”的深沉浓烈的感怀与哀伤。
《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和欢的“洒水车”也极具象征意义。或许是欲望的喷射吧,但我更愿意相信它的另一种隐喻即冲洗作用——对污浊的冲洗,那是对这个欲望肮脏的世界的不断冲刷。欲望时代不仅是外化的而且也是内在的,我们都深陷在欲望中,甚而至于不能自拔。在《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我们从和欢身上确乎看到了这种分裂—— 一种身心的分裂。文本中有三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一,面对车身广告上的女模特,“有一天,她忽然觉得没错,这个女人就是她。身首异处的女人就是她”。这一细节可以看做是对和欢“轻浮洒脱”的表面与负重坚韧笼着圣洁光环的内心之间有着巨大反差的一种解释;其二,和欢被司机圭母踢裂脾脏,杰豪来看望,她并未表现出柔弱,也未哭泣,和欢这种无所谓的“笑嘻嘻”(反复多次)和轻浮放浪的唿哨令杰豪反感与吃惊,其实,这恰是和欢身心分裂的痛苦表征;其三,小说最后一部分临近结尾时,和欢把左右两侧的洒水开关均变为冲水开关,且将冲水转速和车辆时速打到极限,目视这辆飚行的洒水车,公交车上有人急急关窗,于是,那个曾经“身首分离的美丽的女模特儿变成一个完整的身姿”。在丈夫失踪的几年里,和欢虽把陌生男人带进家,内心深处却始终守护着一分爱的追求,这种怀有希望的、执著得令人赞服的“精神”与具有生物属性的肉体的“割裂”,在梦幻彻底破灭后终于真正摆脱了长期身心分裂的苦痛,完成了一次身与心的和谐与超越。这种“割裂”同样“痛彻”地展示了精神追寻中的另一种意味—— 一种别样的可能更实在、更痛楚却更引人深思的形而上的意味。
另一位女作家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在主题与情节上与这篇小说有同工异曲之处。同样也是一个寻找的故事,不同的是《寻找妻子古菜花》中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富贵寻找妻子古菜花——无果——妻不知下落;一条是奈月追寻李富贵——有果——却弃富贵而去、亦不知下落。两条线索表述的寻找过程相异,不管有果无果,结局却是异常的相似:两个女人均如石沉大海烟消云散再无踪影不知去往何处。与北北《寻找妻子古菜花》有意模糊人物心理不同,须一瓜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在小说的形式上有所突破。她更注意人物的心理事件,将人物的种种心理隐秘插入和缠绕在行动的叙述之中,其对人物心理世界的细腻描写以及近似李商隐诗歌意象的致密罗列使《穿过欲望的洒水车》充满唯美情调与诗化意味,为小说笼上了一层婉约的韵味。
作者简介:路遥,太原师范学院基础部讲师;倪素梅,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南帆.日常的奇异与奇异的日常[J].山花,2003(12).
[2] [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C].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72.
[4] 王宁,孙书建主编.易卜生与中国:走向一种美学建构[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15.
[5] 毛丹武.须一瓜小说简论[J].当代作家评论,2005(3).
(责任编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