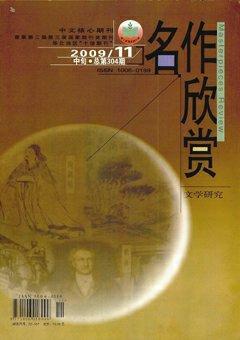自己的文章 自己的文艺观
关键词:张爱玲 “力”与“美” 参差对照
摘 要: 《自己的文章》被看做是张爱玲为了应对傅雷先生的批评而成的佳作。历来学者在解读此篇时都重点解说张对傅文的反驳,却忽略了本文正是张爱玲文学创作观的一次综合阐述。在本文中,张爱玲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对一系列文学创作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述。
一般以为,名篇《自己的文章》是张爱玲为了应对傅雷先生的批评而成的佳作。在文章中,少年得志的张爱玲对于傅雷先生的批评不以为然,采用了上海话中“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之意作为此篇的题目,以示自己的反驳。诚然,《自己的文章》一文的出现与傅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是,对傅文的反驳仅仅是此篇的一个发轫。文中张爱玲更多的是谈对于文学创作的看法和理解,是张爱玲文学创作观层面的阐述。对于创作中的三个问题,张爱玲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给出了自己的论述。
一、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外评论家和作家所关注的论题。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阐述了她独到的看法:“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张爱玲的这一看法是相当独到而有意义的。从“五四”新文学起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似乎都有这样一个模式:文学的创作大多有意识地以某种外国引进的理论去“指导”而进行创作。甚至,对于同一种理论的引进往往由于引进者理解的差异而出现不同的理论阐释。如:君彦用“非物质主义”{1}一词对法国诗歌进行解说,而周作人则就当时对波德莱尔的误解进行阐发用了“恶魔主义”{2}一词,许多作家在写诗做文的同时也写了大量的文学理论著作。评论家进行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创作,文学团体通过理论性文字去阐述自己的观点,本身是正常而有必要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本就是文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然而,当时的中国在吸收外国创作理论时(包括吸收部分外国理论,自己加以改造)过度地去考虑一些主义(在此理解为文学理论的另一个词),他们“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3},“而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4}。这样的主义(理论)到底能不能作为写文章的指导呢?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5}。理论,尤其是文学理论的本身只是对于习作者的一点建议与参照,倘若认为坚持了某种文学理论,坚信了某种主义,便可以有好的作品问世,那无疑是文学门外汉的一种荒谬了,“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6},断不是大的作家、优秀的作品是受某种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产物,与之相反的是,往往许多文学理论是由于优秀文学作品的产生从而形成的相关的理论,而这部作品往往即是这种理论的最具代表的作品。后来者往往妄图借助于这种衍生的理论去写出原作品那种优秀的作品,甚至写出超越原作品的作品,那是很困难的,因为还没有进行创作,创作者已经陷入文学理论的泥沼,而将文学自身规律性的灵感抹杀,这种创作理念下是不可能出现优秀的文学作品的。
张爱玲认为: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是平等的两个实体,文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文学创作有借鉴意义,却“并非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只是与文学创作对等的另一面,如此而已。这种文艺理论观是正确而有见地的,对于“主义”泛滥的民国文学,尤见得可贵。
二、“力”与“美”的辩证关系
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一再地强调了这样的一个观念:“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这里,张爱玲首先表明了“人生安稳的一面”与“人生飞扬的一面”两者之间的关系,两者不仅仅表现在一般学者所认为的对立层面,更多的是一种唇齿相依的联系。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铜币的两面。张爱玲认为虽然“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这样,从一开始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张爱玲就将“安稳的底子”放在一个十分必要的位置:在张看来,缺少底子的文章是浮在空中的,虽然或许外表看来是飞扬的,实质却是虚化的,空有个大而空的虚壳而已。在此基础上,张爱玲更加地指出:“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空中楼阁,在张看来自是失败的。更为可贵的是,“飞扬”和“安稳”的关系在张爱玲这里被运用“美”与“力”的比较而重新加以阐释:“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张爱玲一再强调“力”只有与“美”结合才会有好的作品出现。换而言之,“力”要有“美”的底子才显得动人。张爱玲举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诗。这首诗的动人之处正是在于它不仅仅在“力”的层面去写生死离别,去写天长地久,而是写了诗歌内在的一种“悲哀”,写了“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正是这种悲哀的“美”做了底子,这首诗才那样地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倾城之恋》中也引用了此诗,给流苏的人物增添了几分哀叹之色。较之此文,更显出“美”的本色。其实,张爱玲所论述的“力”与“美”所表现出来的联系正是“飞扬”与“安稳”之间互相衬托的关系:没有“美”的“力”,在张看来,是空虚的;而只有“飞扬的一面”,没有“安稳的一面”的文章自不是好的作品。
在阅读《自己的文章》时,可以发现:张爱玲尤为看重对“美”的表现:“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对于只看重人生“飞扬的一面”的“力”文艺观张爱玲做出批评。而另一方面,张的小说本身又是充满修饰和机智的。张认为,缺少“飞扬的一面”的描写,光有个素朴的底子一样算不上好的作品,她说:“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素朴的底子是为了衬托飞扬的一面而存在的,倘若,飞扬不存在了,那么底子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将这一关系推之到“力”与“美”的关系:“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起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张爱玲明确阐述了“美”的本身并不是缺点,“力”的本身亦不是缺点,只有失去底子衬托的“美”和“力”才显得单薄。并且,张爱玲再次强调了“美”的重要:“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张爱玲正是“用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朴素”。虽然,这样她“容易被人看做”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然而,这正是张氏文学的一个风格,并且,在张看来,这样的一种处理,才是她所要表现的。
三、参差对照的写法
在阐述“力”与“美”的辩证关系时,张爱玲言道:“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在这里,张爱玲阐述了她自己一种独特的创作方法:“参差对照的写法”。对于“参差对照的写法”,《自己的文章》中给出了这样的叙述:“我用的是参差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顺着这个思路推下去可以得知:参差对照是完全不同于二元简单对分的一种彻底的写作方法,它是不彻底的,并且,喜欢这种不彻底的参差对照的写法,是“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文中举了流苏的例子:“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然而,张认为:“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不能出于强烈对照的考虑,非让流苏“大彻大悟”成为革命女性——因为现实中“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因而,强烈的对照是不切合的一种拔高,要想正确地反映生活真实的本身,参差对照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参差对照的写法反映出的真实还隐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
1、启示。“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苍凉”的底蕴是张更为喜爱和擅长的,虽然“人们急于要求完成……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然而“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的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张爱玲反对那种“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嗜好”的写法,她认为尊重现实的本身才是一个小说家该做的。不应按照自己的喜好或者某种“崇高”而拔高文学本身“力”的成分。按客观事实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正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写作初衷。
2、主题的不鲜明。因为张爱玲“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所以张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然而,这在张爱玲看来并不是文章的诟病。相反,她对文章的主题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更进一步,张爱玲认为:“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也就是说,在张爱玲看来,文学作品本身在创作过程中是可以不必有确切的主题的。即便是作者对于作品限定了主题,结果往往也是不如所想的(如果作家考虑作品是以作品的文学性优先出发的话),往往会出现原先所设定主题之偏离现象。文中列举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与《战争与和平》的例子,张爱玲认为《战争与和平》是明显高于前者的,其过人之处正是在于“主题是”“很模糊的”,这种主题的不鲜明正是尊重事实的参差对照写法的结果。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的起始就言称:“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这样看来,这篇讨论了若干文学理论的文章就更显得珍贵了。在看待这篇名作的时候,不能仅仅从“论战”的角度去看到它应对傅雷先生批评的一面,更应该从文本本身出发,去探寻张爱玲的文学创作观。
作者简介:高佳嘉,四川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
{1} 君彦.法国近代诗概观[N].小说月报.1924年4月,第15卷号外.
{2} 周作人.三个文学家的纪念[N].晨报副刊.1921年11月14日.
{3}{4}{5}{6}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A].见: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56.
(责任编辑: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