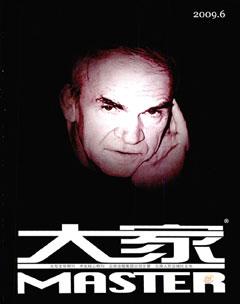意蕴的深化和叙事的诗意
何开四
郭严隶把她的小说定名为《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颇具诗情画意。姚黄魏紫、色彩缤纷,这是何等美丽的图景。但你读完小说并不轻松,乃至感到心灵的悸动和灵魂的战栗。作品独特的意蕴和艺术传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小说以当下社会生活为题材,以叙事者雕刻家“我”寻找雕刻灵石“白珍珠”为贯穿性的线索,展示了三个“家庭”及人物的不同命运。慈悲山市的文化局副局长向文登借腹生子,孩子取名“喜儿”,但悲喜两重天,“喜儿”的命运定格在终身为向家看守祠堂的陋习上。身为文化局的领导,最具反文化的倾向,这是一个反讽。另一个故事是有关农民工的话题。老区农民童木偶因儿子打工在失修的小桥上不幸夭亡,童木偶悲痛欲绝,先是毁桥,后经过心灵的蜕变又走上了修桥的路,童木偶在这一过程中本身也获得了灵性。第三个故事是雕刻家“我”的离异。其悲剧性在于,女儿青叶仅仅成为“拜金的、不读书”的男方的“战利品”,终身被褫夺了母爱的权利和家庭的温馨。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如果从故事层面看,小说无疑有社会批判的色彩。在我们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和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各种欲望有了前所未有的释放空间,这是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沉渣泛起,各种丑恶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也严重地侵蚀着我们健康的肌体,其危害之烈,波及之广,令人触目惊心。三个“家庭”的畸形,有典型的意义。作者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示和抨击也表现了一个作家的正义感。但仅作如是观,尚浅乎言之。小说还有深层的意蕴,那就是“救救孩子”!
“救救孩子”是鲁迅《狂人日记》上的箴言。如先生所说,小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表现了鲁迅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振聋发聩的号角。“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不有?”这是鲁迅忧愤的深广,他看到了孩子的被戕害,也看到了被戕害的孩子也会吃人,所以他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在这里,救救孩子和救救中国是等义的。歌德说过,“一种思想往往能改变整个世纪的面貌,而某些个别的人物往往能凭借他们创造的成果,给他们那个时代打下烙印,使后人永记不忘,继续发生着有益的影响”。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依然言犹在耳,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实际上,从解释学的角度看,“救救孩子”的这一命题并没有终极的答案,每个时代都会生成新的意义。《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承继了鲁迅先生人道主义思想和深广的忧愤。郭严隶并以一个女作家特有的敏锐鞭辟入里地揭示了时下某些社会层面野蛮对文明的亵渎、金钱对人的异化以及愚昧造成的畸形。以向文登“借腹生子”为例,这种恶行,不只是一个腐败官员的个人行为,而是从根本上摧毁了一个孩子的未来,在喜儿的生理和心理都种下了恶果。作品中的喜儿是一个丑孩子,“丑得令人难过”,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而为向家祠堂“殉葬”,则是生命文化意义的彻底毁灭。“救救孩子”不是在当代的回音壁上响起么?不要以为这是个别的丑恶现象,我们在童子和青叶的命运中,进而在广大底层孩子的生存状态中,也依稀看到了喜儿的影子。作者的思考是异常严肃的,女作家独有的敏锐和理性思考的延伸,绽放出心灵的鲜花,且看郭严隶如是说:
我想,这世界表面看是男人的,根本处却是女人的较量,因为所有的男人都出于女人,通过女人而走向世界,对于一个男人,一生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是他的母亲,一是他的妻子。看一个男人,只消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母亲,一个什么样的妻子。个体与个体,家庭与家庭,民族与民族,所有的较量都是母亲的较量。我多么向往那些伟大的母亲呵!我多么希望所有女人都朝向伟大!
这是一个女作家的女权宣言!确实,母亲是民族的图腾,只有母亲的伟大,才有民族的伟大。母亲沦落风尘,则必定酿成民族的悲剧。当我们抨击应试教育的弊端呼吁“救救孩子”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看到“在被时代飓风的手强劲抚摸着的广袤大地上,所有的城市中,有那么多的年轻女子,她们在小姐的生涯中流转。尽管这是被相对合理化的存在,但是,这存在中,能没有悲伤吗?”母亲的救赎,是“救救孩子”的前提。郭严隶的倾诉,彰显的是一个作家的良知和正义。小说中多次出现摩西和摩西十诫的典故,绝不是偶然的。摩西是犹太民族的伟大先知,《圣经》中的仁者和智者。摩西引领犹太人出埃及是人类的救赎。摩西目睹犹太人围绕金牛犊狂舞,愤怒地摔碎圣十诫板,则是对人类堕落的愤怒。《摩西十诫》其中有一诫就是“不准崇拜金钱”,它总结的是埃及人腐败的教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以金钱拜物教为圭臬,必然腐败,其前途岌岌乎殆哉!但是作者面对金钱和权力媾和下的丑恶现象并不像通常小说中那样作踔厉发扬、疾言厉色的情感发泄,作“愤怒出诗人”状,而是有更高层次的思考和对艺术深入的理解,她追求的是美学的崇高。就像米开朗琪罗创作《摩西》塑像时,并不摔碎圣十诫板,而是让愤怒、轻蔑、痛苦,所有这些激烈的感情最终凝固成庄严和宁静。“庄严和宁静”,这是宗教的情怀,也是艺术的境界。它升华的是作家的使命意识。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悲天悯人的崇高,没有灵魂的疼痛,那他至多是个写手,是不配作家称号的。救救孩子,让所有花朵开满春天,这就是作家郭严隶的愿景,也是作品抵达的境界!
和作品的内容相应,《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在艺术传达上也别具一格。其中诗意的叙事构成了小说最大的特色。兹拈出三点,以概其余。
首先,小说的意匠经营不在于情节和故事的铺陈,而在于诗意的营造。作品经过情感浸润的文字,以独白和倾诉的方式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但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是情感的表露十分有节制,从容澹定。揣其用意,一是和全篇“庄严和宁静”的主旨吻合,表现出作家济世的情怀。另一方面则是作品艺术审美的考虑。艺术中情感的宣泄和生活中不一样,它不能任情感泛滥,一泻无余。就像黑格尔所说,“把痛苦和欢乐尽量叫喊出来并不是音乐”,“没有思考和分析,艺术家就无法驾驭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意蕴)”。运冷静之心思,写热烈之情感,让理和情交融,如“水中盐,密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这是这篇作品叙事的艺术走向,也构成了这篇小说特有的美学追求。
其次,作品叙事注重诗歌意象的建构。荷花、月光、小桥、清风等是小说章节的标题,也是作品中出现最多的意象。这些既是叙事的空间,也是审美意象。作家以最富审美的意象书写罪恶和苦难,形成巨大的艺术张力。这很像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阐释的“冤亲词”(oxymoron),即将两个所指反差甚大的表意单元同置,如汉语中的“痛快”,莎士比亚戏剧中常见的“沉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之类,从而表达出爱恨交加及其他丰富的“杂糅情感”。这种词语里的矛盾表意,郭严隶把它从一般的修辞扩大为小说的叙事和谋篇布局,这是颇具新意的。
再次,小说的叙事,大量采用了诗歌的暗喻手法。古人云,“不学博依,不得安诗”,即诗歌中必须运用比喻,这是诗歌的一个基本属性。作家深谙此理,在从容的小说叙事中,蕴含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姑举两例,以畅其旨。作品以雕刻家“我”寻找灵石“白珍珠”贯穿全篇,它的“原型”则是米开朗琪罗雕刻《摩西》的故事。相传米开朗琪罗雕刻《摩西》颇费周章,最后终于在意大利的一个石矿看到一个巨大的石头,他抚摸着这块石头,仿佛从里面看到了圣贤摩西的精神。中外两个故事的叠合,就像电影的蒙太奇,生成了新的境界,耐人寻味。“白珍珠”谓何?是灵石,是公理,是正义,是作家的使命,是宗教情怀……作品没有答案,甚至“白珍珠”在小说中最终也没有下落,但它留下的未定点和空白度,却隽永有致,发人深省。又如童木偶从毁桥到修桥的过程,也是一个暗喻。在民间修桥筑路从来是修善积德之举。而桥是“此岸”和“彼岸”的津梁,从木偶到人灵性的复归,就是一个救赎的过程,其蕴含之深,不言而喻。
《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是一篇具有丰富审美信息的作品,有震撼灵魂,净化心灵的艺术感染力,其意蕴和艺术表现都给我们以启示,值得深入挖掘。郭严隶是一位严肃的作家,对艺术有宗教般的虔诚。多年来,她潜心创作,自觉追求作品的品位和艺术审美的精致。这种创作的姿态,值得肯定。祝严隶今后的创作更上层楼,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插图摄影:付汝平
责任编辑:玉波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