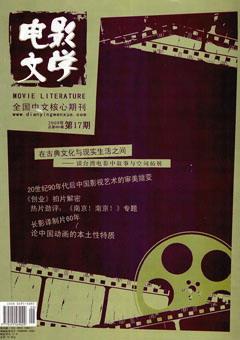《爱的流刑地》:爱与杀的日本式迷恋
徐舫州 谢 璐
[摘要]《爱的流刑地》这部日本影片,片名就直白地透射着爱的柔情与冷峻的死亡气息,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爱是与性爱和死亡三位一体的,笔者试图从日本文化艺术史中的情色现象、日本人的物哀意识、日本人对樱花的独特情感、日本人的地理危机以及弗洛伊德对生本能和死本能的阐述为切入点,通过一定剖析研究,解密该部影片中爱与杀的日本式迷恋。
[关键词]《爱的流刑地》;日本;爱;死亡
爱,人类共同的美好情感。
流刑,古代将犯人流放远地的一种刑罚。《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仅次于死刑。
爱的流刑地,直白地袒露着爱的柔情与冷峻的死亡气息。
《爱的流刑地》,一部日本影片,一部诠释爱与杀的日本影片,一部诠释根植于大和民族内心深处的爱与杀的日本影片。
说到爱与杀,很自然地便会想到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一书中提出的“生本能”和“死本能”概念。“生本能”包括人的自卫本能和性本能,最后都是指向生命的生长和增进。“死本能”指的是每个人都有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冲动。死本能向外表现,就体现为伤害他人,而以人类战争的最高形式达到顶峰;死本能向内发展就表现为对自我生命的否定、自毁和自杀。生本能,是生活和生长的原则,它是爱和建设的动力;死本能,是衰退和死亡的原则,它是恨和破坏的动力。死本能多半不是表现为一种求死的欲望,而是表现为一种求杀的欲望。弗洛伊德认为,人不可抗拒要走向死亡,一切生命的目标就是死亡。简单地说,生本能指向的是性、是爱,死本能指向的便是杀。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还只是人类20世纪的探究成果,而那种对爱与杀的迷恋,自古就能在大和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中得到普遍印证。
日本这个国度,似乎有着强烈的关注情爱欲望的民族传统,有着强烈的生殖崇拜和性开放意识。日本的情色文艺源远流长。史前绳纹末期的大量女性形象的土偶就十分夸张与突出人物的生殖器官;奈良时代男女可以自由恋爱,男人可以与他人之妻恋爱,而身为人妻的女人也可以与其他男人恋爱;
《源氏物语》,在日本的地位相当《红楼梦》之于中国,其间充满男女之间的花柳韵事,不伦的爱欲生活更是随处可见;江户时期的井原西鹤,以反映町人享乐思想的“好色物”著名,描写男女性爱肉欲是其主题,例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好色五人女》等。情色,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最代表日本传统审美文化的浮世绘中也有情色画,精致的茶道传统中也有艺妓的影子(虽然不同于妓女,但同样暗示的是色情)。即便是现代,指向色情的AV女优和“援助交际”乃是日本语汇中的特有名词。
在电影领域,日本是世界情色电影的出口大国,二战后的60-80年代是日本情色电影的繁荣期,日活公司成立,带动了情色电影的潮流,拍摄R级、P级浪漫性爱黄色电影的“日活路线”被大众普遍认可,一度创作出世界顶级的情色作品,培养了日本四大情色大师——寺山修司、神代辰己、若松孝二、大岛渚。
性爱这个话题,早就已经渗透进日本生活的各个角落,早就融合进日本人民骨髓的每一个分子。《爱的流刑地》中对男女主人公视觉化的性爱描写尤为突出,有一种唯美化、唯情化,甚至于是弥漫着歌颂色彩,荡气回肠,令观者也不免为他们的融合而动容。这种融合更是让女主人公冬香心醉神迷,她称自己是“飞舞到天上的女人”。酒吧女老板说:“女人分两种,知道这个的和不知道的。”“男人也分两种,会引导的和不会引导的。”显然,冬香属于前者,男主人公村尾菊治也属于前者,他们是幸福的。
导演在用心琢刻着这一段段爱的影像,暖暖的色调、仿佛颂歌般的哼唱、细腻的镜头,把人物在情爱呢哺中的各种情感体验传达得活色生香。还有那玫瑰色的晨日、绚烂的烟花,以及美到奢靡的漫漫樱花。
樱花,盛开时灿烂华美,然而看似柔弱的娇花却有着刚烈的性格,不会等到枯萎而是在樱满枝头时华丽飘落,几乎一夜散尽,落英漫天。日本人把樱花看作大和民族的象征,可以说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如满樱一般绚烂飘落的死亡方式正是他们所深深崇尚的。在日本的和歌集《万叶集》中,“樱”用来比喻为情所困、最后选择死亡的美丽少女形象。可见,在日本的文化里,“樱花”很早就与死亡建立了某种联系。日本现代著名女诗人茨木则子有一首诗,名字就叫《樱花》,在诗的结尾部分有这样几句话:“信步在缤纷的落英下/瞬间/我有如名僧顿悟/惟有死亡才是常态/生不过是可怜的海市蜃楼”。
烟花,又何不如此呢?绽放时绚烂、旖旎,刹那间也就灰飞烟灭,而灿烂的死去不能不说恰好符合日本人的生死理想。他们对于生命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态度——选择年华正灿烂之时死去,将时间永远滞于最美好的瞬间。
物哀是日本的一种传统审美观念,有感慨、感动、哀伤、壮美的含义。《源氏物语》研究者认为,《源氏物语》并非以道德的眼光看待和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恋情,而是意欲以此引发读者的兴叹、感动、产生“物哀”之情。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说过:“日语的美是同悲哀相通的。”对日本文化有深入研究的鲁斯·本尼迪克认为,当我们在品味日本的文学和电影时,首先吸引我们的就是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强烈自杀情结。当然,这种自杀情结的体现并不仅局限于“自杀”这一具体行为,它更流露于日本文艺作品在叙事中体现出的对自杀的赞颂和对死亡的敬意。画家古贺春江有句名言:
“再也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死就是生。”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同样不乏死亡,在《挪威森林》中有这样一句话,“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然而在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国家中,自杀被认为是懦夫的表现。《圣经》中,自杀的人是不能上天堂的。日本人则将自杀者如英雄般敬仰,对死亡毫无畏退,将死亡看得平淡异常,这种民族性格与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又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带,拥有全球十分之一的火山,这使得岛国时时处于台风、海啸、地震的淫威之下,令人民赖以生存的渔业、种植业始终面临着大自然的威胁。另外,频繁的战争也让死亡时刻笼罩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这些,都使日本人认为一切美好虚浮易逝,难于把握,惟有死亡才是永恒。他们一方面不舍美好事物,一方面又对死亡疯狂迷恋,从而形成通过永恒的死亡留住易逝美好的独特生死观。
《爱的流刑地》将爱推到了顶点,遂将死推到了高峰。
电影的小说原作者渡边淳一语出惊人,他认为真正的纯爱就是“不伦之恋”。他坦言,现在日本电视剧中上演的各种所谓“纯爱”根本就不是完整的爱。真正的爱绝对需要灵与肉的完全统一。向来被世俗视为不伦之恋的婚外恋情正因为是没有未来的苦恋,才使得双方饱受灵欲的痛苦折磨,徘徊在情感与理智的边缘,进退两难。这种苦恋没有婚姻带来的太深重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只是因为彼此相爱,碰巧对方又已经结婚罢了,这种被社会所不容的苦恋才是真正的成人纯爱。正是这样的一种“纯爱”,令冬
香想要死一幸福得想死。
从男女主人公的相识、相爱、相别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冬香选择死亡的情感堆积。她说她“幸福得连死都愿意”,并且“随时都能死”。在冬香决定死去的那一晚,灿烂的烟花、静美的和服以及精心装扮的面容,让这一晚看起来是如此的神圣,神圣得就像一场仪式,冬香选择死亡的仪式,亦是冬香升华自我人性的仪式。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爱是与性和死三者一体的。正如日本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今道友信所写,爱在某种意义上与性和死相关。亦如法国民谣中所唱:
“爱就是一点一点地死去。”真正的爱就是将自己牺牲,达到自己死的彼岸。
从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角度,同样能够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生本能和死本能的相互转换。人在极度开心时会哭出来、极度幸福时会希望死去,极度绝望时会焕发出强有力的生的力量。生本能和死本能的转换构成了人的生命过程的全部内容。当人们面对美丽的景色心中格外欣悦之时,都可能会有希望个体消失、消融在景色中的冲动。人们内心中爱的本能达到一定强度值会希望用死亡去定格它,就像用照相机定格一样,爱本能就是人的生本能最重要的表现,这里用照相机的定格来比喻很是形象。只有死亡,才能做到一生一次,所以心灵纯净又单一的人,想用这种做法成就自己的惟一,冬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总是无比坚定地说“幸福得连死都愿意”的女子,用自己的死铸造了一座“爱的墓碑”,以此来表达她对爱的笃定,来定格他们的爱。她心甘情愿地用死成为男子的惟一,不想给任何人。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在他的笔下,死亡和生存一样美丽,将死亡赋予了许多美丽的令人向往的色彩。
日本人将性和死亡看作人生的至高境界。1969年《情死天网岛》的治兵卫和小春,双双削去头发后殉情。1978年《爱的亡灵》中丰次和阿石被处极刑。1983年《槽山节考》中母亲面对即将到来的“朝山”的坦然态度。1986年《台风俱乐部》恭一纵身跳下窗予,希望他的死能让大家活下去。1997年,《花火》西佳敬与妻子在海边的两声枪响。同样是渡边淳一的《失乐园》饮罢毒酒,缠绵死去……这种种的死,都不只是死本身。日本人对待它有更高级别的态度,是高于一切的崇高,坦然地面对死亡,甚至于欣赏死亡是日本民族的一个特性。
冬香对死亡也是向往的。外表纯钝的她,早在18岁读过菊治的《爱的墓碑》后,就将爱的墓碑奠基于心底,她羡慕里面那个娇艳、自由有个性的少女并一心想成为那样的女子。似乎家庭生活牢牢禁锢了她的这一个性,她甚至不肯写丈夫的姓(在日本,女子出嫁后要随丈夫的姓氏)。菊治的女儿高子也深谙这部小说的魅力,她问父亲:“是成为预期的好孩子,还是显露真正的自己,让人认为是坏孩子?”冬香的死同样表明她也在追求这种个性中的自我。那个女监察官不也羡慕冬香吗?她说她也想被掐死,但是她没有勇气去争取她的自我,甚至刻意回避遮掩。《爱的流刑地》通过主人公的婚外恋情,引发了一种前面提到的“物哀”之隋,让观者内心超越伦理的束缚,得到美的升华,将人世的情欲和对死亡的崇敬升华为审美对象。
日本,以它独有的悲剧气质,上演着一个个爱与杀的故事。或许这爱,与这杀都是一回事。既然生命无常,那么让死亡永远将爱定格,是不是也是对爱的珍重呢?而这种对爱与杀的迷恋,或许也正是日本人的智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