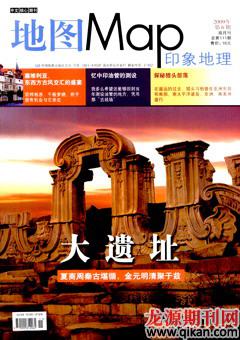探秘猎头部落
郭 晶 顾建豪
初识龙摩爷
2009年8月,我们终于来到了佤山。在过去,对于一个外族人来说,要进入佤山绝对是一次疯狂的冒险。现今,深入那些散落在大山深处的佤寨已不用再面对被猎杀的恐惧,仅仅只需经受住道路和体力的考验就可以了。
到了佤山,顾不上休整,我们便决定前往“龙摩爷”,因为早在昆明时就曾听说“龙摩爷”是佤族举行剽牛祭鼓仪式的圣地,也是供奉人头、祭祀神灵的“鬼林”,因此,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探访猎头部落的第一站。
八月的佤山,一派苍翠。在县文化馆馆员岩飘的引领下,我们穿过勐梭湖畔的芦苇丛,大约十来分钟,便进入通往“龙摩爷”的林间小道,顿觉暑热退去,凉风袭来。缘山谷而上,高大的树冠遮避了阳光,林中愈发显得宁静和幽暗。很快,我们爬上了一块只有几平方米的石台,抬眼望去,一幅令人震撼的景象呈现在眼前。山谷两旁的悬崖、岩石、树干、木桩、祭台上全都挂满了牛头,足有上千个。白骨森森的牛头在昏暗的环境中,显得庄严、肃穆甚至阴森。在牛头包围中,三五成组地矗立着两丈来高的木桩,顶部扎着锥形竹笼。我们从岩馆员那里得知,这便是传说中的人头桩,它们大多立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粗大的木竿早已老旧,而顶部曾经盛着人头的竹笼似乎还散发着血腥味,让人不寒而栗。岩馆员告诉我们,过去每个佤寨都有这样的人头桩,有的多达几百个,每个人头桩上都盛着人头。1958年猎头习俗被废止后,佤族人才用另一供奉物——牛头代替了人头。现今,许多佤寨仍然还有供奉木鼓的木鼓房,周围高高地耸立着人头桩。每逢节庆,佤族人仍会到这些地方来祭祀,祈求五谷丰登,岁岁吉祥。


在县图书馆,我们查到了关于猎头习俗的资料。猎头习俗起源于人类早期的“血祭”,“血祭”是世界各民族都曾经历过的一个历史阶段。当代学者通常把猎头习俗解释为原始的灵魂崇拜,也就是说,人们通常认为人头中包含着某种“灵魂物质”,通过占有它,便能获取超凡的能力。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我们得知,在遥远的过去,猎头习俗曾在亚洲东部和南部、南太平洋诸岛、非洲、南美洲以及古代欧洲的凯尔特和斯基泰人中盛行;在我国东汉时期的铜扣饰上,也出现过砍头祭祀的场面;在古滇国,“血祭”是一种最高规格的祭祀,凡遇重大节庆,必用人头祭祀……在佤山,猎头习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毛泽东主席与西盟佤族大头人岩坎商量能不能不砍头,用别的东西代替。岩坎的第一反应是,祖上留下的规矩,不砍不行。据史料记载,后来岩坎和中央政府经过反复协商,终于让佤族的猎头习俗终止于1958年。
猎人头的记忆
我们在岳宋乡堆翁寨见到了岩转老人,他对当年“猎人头”时惊心动魄的场面仍记忆犹新。每到播种或收获时节,“猎头英雄”便埋伏在山路旁,等长着毛胡子的人路过时,便一跃而起、手起刀落。人头提回村寨后,要抬着它绕木鼓房转九圈,同时还要向人头抛撒米或火灰。在人头进入木鼓房祭祀之前,手上沾的鲜血不能洗去,沽了血的米和灰要撒在每家的谷子地里,人头则由“窝朗”(管鬼和木鼓房的人)供入木鼓房,一段时间后再移送到“鬼林”当中,陈列在人头桩上。
“为了得吃高粱饭,为了得偿小米粥,我们才去砍木鼓,我们才去打冤家(猎头)。红懋树阿茫呵,黄葛树女王,赐我们丰收,赐我们富有……”老人向我们唱起了这首当年的木鼓祭词。老人还说,“长着络腮胡子的行人常常成为最中意的猎头目标,密密的胡须象征着茂盛的谷穗,用来祭祀最好。”
20世纪40年代,由于社会动乱,佤族猎头习俗常常与部族仇杀混杂在一起。一时间,木鼓响起,人头落地,木鼓声不再是催生稻谷的新生之曲,而成了遭遇不测的死亡之音。“收获和播种时都要敲木鼓,敲木鼓就意味着村村寨寨要警惕,不要说老百姓紧张,连我都紧张。防止你来杀我,我来杀你。”说起佤族的猎头习俗,曾在西盟边防团工作的李忠秀老人仍心有余悸。他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西盟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猎头事件:1946年的一天清晨,马散佤族袭击了勐梭地区的戈里佤寨,寨子里的68人,被砍杀67人,用8头牛才将全部人头驮走;1956年,西盟地区灾害频发,粮食锐减,猎头祭鼓的阴云再起,导致村与村之间相互猎杀,就连进驻佤山的解放军战士也遭到不幸,昆明军区测绘队当年在佤族地区进行测绘工作时,就有两名测绘队战士被杀害了……


佤族的猎头习俗是和拉木鼓、砍人头、洗刀等一整套宗教仪式紧密相连的。第一年是拉木鼓,第二年是砍人头,第三年是洗刀,这是一轮。完成一轮,第四年又开始新的一轮。每个村寨都经过这样的轮回,无数条生命被吞噬。在无休止的猎头祭祀中,砍头多的人竟成了“英雄”。我们曾在临沧市档案馆里见过两幅照片:一幅是“猎头英雄”,另一幅则是一户人家被砍得只剩下一个小孩。于希歉先生在《中国南方鼓文化与地域社区生活》一书中曾对猎头习俗作过一番人类学阐释:“猎到异寨的人头是最令全寨兴奋的事情,猎到的人头要接受人们供奉鸡肉、米饭、水酒等丰盛食物,整个祭祀过程,把离群的危险、恐惧和苦难以最富刺激性的方式呈现在众人眼前,任何置身这种场合的人自然会想到,如果自己不与全体寨民保持行动一致,难说某一天自己的头颅也会被供奉在异寨的祭坛上任人摆布。个人只有依靠集体才能得以生存,合群才会有安全和幸福的意识自然在内心深处产生,朴素的集体观念在趋利避害的本能驱使下,与追求有吃有穿、兴旺吉祥的目标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或许说出了猎头习俗之所以在佤山盛行的真正原因。
走进木鼓房
在结束对“龙摩爷”的探访后,我们决定前往勐梭镇,听说那里有佤山最大的木鼓和最后的木鼓房。陪同我们的岩太,是远近有名的“摩巴”(即通神的人),现被县旅游局聘为“龙摩爷”景点的工作人员,专门为游客作通神祈福表演。他向我们介绍说,木鼓本是佤族的乐器和祭器,后来也用做战争报警、跳舞伴奏、部族议事时的信号。过去,佤族新建村寨,都要先拉木鼓、盖木鼓房,据说只有拉了木鼓,请“木依吉”(佤族传说中的天神)进寨保佑,才能建村立寨。因此,木鼓也被佤族视为“一寨之母”。建一座佤族寨子,一要选好水源,二要选好木鼓房的基址。佤族人相信“生命源于水,灵魂来自鼓”。过去,每个佤寨都有两个“窝朗”,一个管木鼓,一个管水源。管木鼓的“窝朗”地位高于管水源的。管木鼓的“窝朗”每年举行两次木鼓祭,一是制作木鼓,一是盖木鼓房。管水源的“窝朗”则负责村寨集体祭水仪式。岩太还告诉我们,在佤族社会中,木鼓具有非常神圣的地位。佤族支系中的勒佤人在佤历一月欢度接新水节时,第一杯新水首先要献给木鼓;庆祝新米节,第一碗新米饭也要献给木鼓。在佤寨,每个较大的姓氏都有自己的木鼓房,一个寨子由几个主要姓氏构成,单看有几座木鼓房便知道了。
在岩太的陪同下,我们走进了勐梭镇的一座木鼓房。初看上去,这座木鼓房不过是一间面积十来平方米的茅草棚,房顶成人字形,房架用牛角叉和竹子架成,四周无墙。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岩太所说的“全世界最大的木鼓”,这个木鼓确实很大,直径足有两米,不过谁都能一眼看出,它是为了吸引游客而制作的仿制品。“经历‘文革之后,这恐怕是整个佤山唯一的木鼓房了。”岩太不无惋惜地说:“木鼓没有了,镇不住鬼,外人来得多也带来了不好的东西。”木鼓是佤族心目中的通天神器,常常被供奉在寨子中心,有喜事要告诉它,有大事要通报它,猎头祭谷要敲响它,可以说,木鼓是佤文化的核心。“但木鼓必须经过人头祭祀才有灵性,”岩太告诉我们,“传说佤族来自一个名叫‘司岗里的山洞,自称‘里佤,很早以前就有木鼓,当时不砍人头,谷子长不好,人和家畜也病死了很多。人们用狗头,猴头祭祀都不行,最后砍人头来祭才好了。”在佤山,木鼓无形中就是砍头的代名词。所以,拉木鼓便是寨里的头等大事,也是附近村民的危险时期,佤山曾流传着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谚语;“木鼓响、人头痒”。第三任老县长张岩松说:“从小我老是害怕木鼓声。如果不是逢年过节,木鼓声一响,不得了,有意外事了……木鼓在佤山已销声匿迹多年,但走在佤山,我还是觉得隐隐约约像是有敲鼓的声音,闷闷的,藏在老林里,让人心惊肉跳。”
岳宋乡岳洛寨是靠近缅甸的一个佤寨,也是西盟少数几个至今仍维持佤族原貌的村寨。在这里,我们专程拜访了岩文老人,据说他是寨子里惟一一个当年曾经参与过“拉木鼓”的人。他向我们介绍了木鼓的制作过程。他说,木鼓制作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其间伴随着各种祭祀活动。佤历“格瑞月”(相当于公历12月)是各村各寨“拉木鼓”的时节。节日头一天,头人和“摩巴”要带人乘夜色赶到事先选好的高大红毛树下,在举行一番祭祀后,连夜将树伐倒。第二天清晨,全寨人一起上山拉木鼓。木鼓毛坯拉到寨门外要停放三天,由“摩巴”杀鸡祭祀后,才交给木匠制作。“拉木鼓时,青年男女挤在一起,是谈情说爱的好时机。”说起往事,老人一脸的甜蜜。每个村寨管理木鼓的“窝朗”凭借他们在族人中的威望,遵照传统道德及习惯法办事,也往往通过木鼓依靠神的权威使习惯法得到彻底的执行,因此说木鼓也是权势和财富的象征。岩文还告诉我们,在佤山,木鼓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祭器,还是一种重要的礼器,若有德高望重的老人辞世,断气时就要敲木鼓、放铜炮枪,而一般人则没有这样的礼遇,通常只是单纯地放铜炮枪。
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山区,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依靠个人、家庭的力量难以生存,人们只有联合起来,形成团体,才能战胜自然界的诸多困难。人们结成大大小小的共同体之后,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来维系群心。在无文字的时代,鼓便被赋予了这种特殊的作用,成为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象征物。
木鼓声再次响起
1958年猎头祭谷习俗废止后,猎人头的木鼓声就再没有在佤山响起过,木鼓和木鼓房也被毁弃。“文革”后人们曾将很多优秀的佤文化与猎头习俗一并革除。如今,在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过程中,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很多少数民族的民间传统节日结合现代民俗旅游热热闹闹地过了起来。2003年,首届木鼓节在西盟隆重举行。在木鼓撼动山谷的节奏中,佤族人再次找到了释放激情的方式,找回了民族文化的自信。“这太重要了!”老县长隋嘎回忆起那段燃情岁月时感慨万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就没有精神、没有理想,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今天,西盟又提出了“阿佤文化兴县”,重新认识“江山木落”、重新品读《司岗里传说》,并建起了司岗里文化生态村、“龙摩爷”旅游区等旅游景点……在充分挖掘古朴神秘的佤文化内涵的同时,充分发挥了西盟生态自然风光、边境异国风光的优势,民族文化旅游业前景看好。
离开佤山的日子终于来临,透过车窗我们再次深情地回望佤山,回望宁静的勐梭龙潭,回望庄严的“龙摩爷”,回望神秘的木鼓房以及薄暮中的太阳……还是这轮金色的太阳,它映照过猎头部落往日的沧桑,映照过佤山人民今天的变迁。我们暗想,昨天的太阳已然落下,今天的太阳才刚刚升起。阳光下的佤山,将会在新一代佤族人的手中建设得更加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