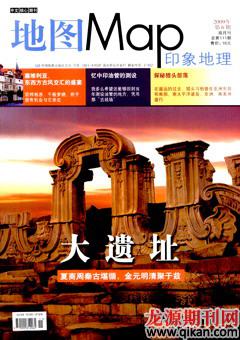忆中印油管的测设:这世上只剩我一人了
高时浏
1943~1944年是抗日战争最危急、最紧张的时刻。日本侵略军攻陷了缅甸仰光,从利多、密支那长驱直入龙陵,占领松山,威胁保山及昆明。日寇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攻占重庆,我国援缅远征军不得不炸掉惠通桥。史迪威公路被切断后,中国几乎成了瓮中之鳖,盟军不得已启动驼峰计划,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飞越驼峰押送援华物资。那是既不经济,又延误时间的,有人说运送一吨汽油到中国就要消耗一吨汽油,人员伤亡又极其惨烈。故消灭滇缅路段上的日军,抢修公路,架设通讯线杆,铺设和联通中印油管成为当时西南后方最迫切的军事行动。
我就是在1944年下半年日本对贵州独山发动进攻时,离开贵阳前国防部中央测量学校,应聘去交通部滇缅路油管工程处工作。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充满激情和喜悦,艰苦和危险,高待遇,高福利,既冒险又浪漫。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测量三人队,油管工程处的组成
据我所了解,滇缅路油管工程处是战时应急由中美联合组成的。除职工的工资由中国政府支付外,其他工程器材、铺设油管的劳工工资及野外工作人员的午餐均由美方支付及供应。由于当时非常迫切地需要测绘及施工的技术人员,所以油管工程处的下属三个测量队成员均由云南省农贷会所属的农田水利测量队中的主要工程师及测工调过来。
在我们参加油管工程处时的正处长姓朱,是上海交大毕业生,留美,当时也是包工商人。有一位副处长叫童大埙,也是交大毕业生,庚款留英,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后由上海交大调到同济大学土木学院道桥系任二级教授。2005年我90岁,他已是94岁高龄。当时我应母校及母系的邀请由武汉赴上海,才有机会拜访他,但询及油管工程情况时,他已经记不清,也无任何文字或图片资料可供参考。第一测量队队长姓封,该队有一个队员与我同乡,也是福州人,他们都毕业于中央大学水利系(现南京大学)。第三测量队没有印象了。
我供职于第二测量队,队长是林钟山,同济大学测量系第一届毕业生。第二把手叫郑鸿章,是同济土木系1939级毕业生。我们三个人既是同乡又是校友。工作时林队长随同美国油管工程兵负责选点,郑鸿章负责观测,我担任记录。后来又来了一位刚毕业的交大学生做助手,他叫杨锡琮,广西人。但他在油管工程处正式撤销前就走了。

油管工程处的待遇很好,当时我们领的工资比大学教授或系主任还高。我们的衣(美式军服)、食、住(帐篷)、行(吉普车)全是供给制。在野外崇山峻岭,穷乡僻壤,钱也无处可花,因此我们的高额工资和野外津贴都请驻在昆明的各队会计兼出纳员兑换成黄金储蓄。记得我离开昆明油管工程处时,除领到大笔金圆券外,还有五六两黄金储蓄,可真算是个“百万富翁”了。
测量线路,战火纷飞亦有喜乐
大约1944年秋冬,我们三支测量队,各派三四名懂得英语的测绘技术骨干,集中在昆明工程处的一间宽敞客厅内,由美军油管工程队的一位上尉军官率领两位士兵携带仪器向我们讲演如何用美制的K&E;经纬仪测绘油管路线,如何进行手簿记录(当然要用英文记录的)。这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在我记忆中,他特别强调导线经过的两旁若是稻田,应注明Rice Paddy,则将来铺管时,油管应尽量避开。以免一旦管子漏油,会损坏稻田(可见他们很重视保护农田)。所以Rice Paddy这两个英文字至今犹铭刻在我脑海中。我最初很轻视美制的K&E;经纬仪,因为它的底座是四个螺丝的,不如德、瑞的三螺丝底座方便平整,但实践结果证明,在山区测量时K&E;的经纬仪更加坚固安全。
受训三四天后便向保山出发,三支测量队分三段施测。各队的分工是由美军总部事先根据他们已有的航测照片选线、分段,每队由一美军工程兵带领。我队林队长和美军领队进行选点、打桩、施测。测完这段后,跳跃前进。每段导线的方位角最初是按磁针走向的。由于山区地质多变,磁针指北方向有偏差。如果每段十公里,每队搬三次家,测100公里后,方向偏差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后来我发现美军中带有天文年历,就建议采用北极星定向法确定方向。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改用观测北极星定向法,于是消除了油管路线的方向误差。
我们第二测量队到达保山以西的怒江某地时,松山尚未光复,惠通桥已为援缅远征军所毁,我队只能在怒江东岸铁索桥附近安营扎寨。当时日本飞机还经常轰炸保山及铁索桥。由于两岸高地都有美军高射炮阵地,敌机不敢低飞,所以没有伤亡。但我们每天都要逃警报,躲进防空洞,既不能过江,又不能工作,于是向上级请示后,暂撤离保山,向东后撤到大理待命,于是才有喜洲之游。
1944年冬我们第二测量队从保山怒江东岸某地东撤到大理,住了一个晚上。那个时代的大理都是平房,而且屋顶盖的都是平石板,因为风大,普通的瓦屋顶是挡不住风的。第二天清晨我们便出发到喜洲。我踏上田埂路,耳边听着下关吹来的萧萧风声,举头望见点苍山上的皑皑白雪,眼前呈现一望无际的蔚蓝的洱海。据说夜晚洱海映射出的月亮堪称天下一绝。两边湖泊稻田,碧波荡漾。我禁不住脱下鞋子坐下,在水沟里洗足,心中平静,连日来耳中的炮火轰炸声悄然消失。此情此景让我不禁想起幼时读过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此时忽然听到从远方传来的琴声和歌声,一问之后才知道有一个中学就在附近,不禁引起我久久的遐思,梦想抗战胜利之后,但求在此地求得一席中学教师之职,享受大自然与音乐之美。
1944年11月前盟军相继光复龙陵、腾冲、松山等地后,滇缅路全线通车,我们开始从大理掉头向西,经怒江、松山到腾冲附近,从K800里程碑向东施测。
三支测量队自从1944年秋冬由昆明出发后,少有相聚和联系的机会。油管线路测量工作在美军士兵与我方队长商定下进行。有时沿着公路,更多的时候要翻山越岭,跨谷涉溪。每天清晨在坡下驻地帐篷里用过早餐后便开始爬山。所用的经纬仪及视距标尺当然由熟练的测工扛上山,其他木桩、午餐等杂物则由当地雇来的临时工背着上山。背经纬仪的测工最重要,他是班长,要会在山坡上安置并置平经纬仪。好的班长将给观测的工程人员以安全和高效之感。我们的线路过两江(怒江及澜沧江)时是用橡皮艇运载人员及仪器冒险强渡过去的。中午我们都由美军提供军用午餐(Ration)。这是一个密封的纸盒,内装多种饼干、奶酪、巧克力等等营养丰富而又美味的压缩食品。我们整天都在山坡上或丛林中工作,傍晚收工时下山,回到驻地帐篷里用晚餐及整理手簿,资料当晚就得交给美军,由他们的施工队计划安排这段铺管工作。铺管和测量之后紧跟着一系列有序的军事计划行动。
这种单调而冒险、有苦也有乐的油管线路测绘工作好像只进行到1945年春季,嗣后我们便
在楚雄转为施工队,工程的任务转为铺设油管。
铺设油管,维护我方劳工的权利
铺管工程对我方来说,是没有任何技术性的重苦力劳动,因为扛管和铺管的都是中国劳工,接管的则是美国工兵。我的主要任务是在穷乡僻壤的山沟荒村中招收农民工。当时的云南,尤其滇西,地形上高山峻岭,跋涉困难;气候上瘴气四伏,疾病常生,居民体弱多病(多为疟疾及炎症),所以招工非常困难。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招工有如下规定:每乡或每村强派若干名额的民工,工作若干日。工人应自背行李及口粮,完工后工程队应立即支付工资,但有的工程队(如公路、电讯等)会贪污工资,更谈不到对他们健康、疾病的照顾。美军了解到当地流行的疾病,规定施工队向民工赠发一定的消炎和治疟的药品,如消炎片和金鸡纳片。每日开工时,由美军士兵和我共同按人点名,美军签了名后由我们上交给工程处,最后汇总,由美方结算支付工资。
我当时是身背布袋,内装消炎片及奎宁片,下乡后以爱护体弱劳工的精神向贫困的农民慰问疾苦,先给他们看病施药(这些药品在抗战时期即使在城市也难买到,何况乡下农村),真可说药到病除,我因此取得了他们的好感。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口碑”,我利用药品招工的好事,不胫而走,民工竞相应征,所以招工毫无困难。
施工初期有时也碰到困难。记得在楚雄施工时,曾有几天和美军大兵发生过口角争执。有一次油管工段远离楚雄公路,我和工人们每晨在楚雄城门口集合,美军司机开大卡车到城门口接我们上车,由小径开到施工段附近后下车,再由劳工扛着油管步行一二百米到该段埋设或架设。美军的行动比较准时,而我们的劳工却是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难免迟到误时,这就潜伏下中美双方的矛盾,我却无力解决。某晨几位劳工晚到了,上车后还没坐稳或站稳,司机便开车了。当时有一位站在最后一排的劳工草帽被风吹掉,他倾身去抓帽子,不幸掉下车摔死,因此引起纠纷。我批评美军司机,声称要向美军上司报告,司机威胁我说,若我向上报告,他将要打断我的牙齿(Iwill knock down your teeth)。但我还是向美军上司报告,后由中美双方通过楚雄县政府进行调解、赔偿处理。
礼尚往来,与美国大兵的交往
当时我们称美国大兵为GI(GovemmentIssue的缩写),无论测绘线路或油管施工,我们中方和美方都各住各的帐篷,除工作外很少来往交谈。我们每完成一段任务后,就收拾行装、帐篷、行军床等。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我们同他们一样,把营地四周收拾干净,不留任何垃圾,这是美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在修建抽油站、加压及减压站(Pumpstations)时,停留时间短则一两周,长则一两旬,两边的交往才渐渐多起来。此时,我们向他们学习电焊、接管及开车技术,也同他们闲聊,交换礼品,例如我以中国手工业品赠送他们,他们赠送我以克林姆奶粉、奶酪、巧克力糖或骆驼牌香烟。
在野外工作全是男性,没有女性,这对于美国大兵当然难以忍受。他们经常把性感少女封面的画报剪下来贴在帐篷上,以便望梅止渴,称之为Pin-up gil。我的帐篷上不免俗也有此美景。有一次,油管处某一副处长到我们工程队视察时,一睹此性感美女,心旌驰摇,竟未征得我的同意,将其取走。我收工回来后发现,大发脾气,要兴师问罪,索回图片,但被林队长劝止,当时曾传为趣闻。
老兵常在,油泵照亮我的人生
1944~1945年在油管工程处工作将近一年的时间,是我从事测绘事业,特别是野外作业最艰苦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抗战末期,有不少青年学生和教职工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或远征军,我当时没有报名参加,深感惭愧,幸而能在抗战胜利前夕有此良机,参加中印油管在中国境内由昆明到腾冲附近长约800公里的一段测量及施工工作,我由衷地感到荣幸与自豪。
中印油管全长1850英里(约3000公里),是当时世界最长的油管。当年我国参加中印油管全程测设工程的技术人员,至今还活着的估计只有我一个人了。我深感历史使命与责任的重大,因此必须尽我所能,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我对油管工程在抗战中的贡献及作用认识不够,测量及施工时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记下日记,也没有照相机,如今只能凭记忆捕捉历史的点滴。
回顾当年参加油管测量及施工的经历,虽隔65年,但情景犹历历在目,不能忘怀,在我一生中不断地给我生活与工作的动力。这段中印油管号称世界最长的油管,使用的时间却最短。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在印度和缅甸这两段的油管都变成电线杆了。在中国境内长达800多公里的滇缅路上的油管也逐渐被遗忘了。
最近从戈叔亚先生的博客上,看到了一篇叫作《自由之油——中缅印输油管的故事》的译文,文中写道:“用油泵去照亮苦难中的中国,他们就这样开始了用油管联结被封锁的中国的工作。”其中有一位名为“红飞蛾”网友评论道:“感动,这才是真正无私的国际主义的援助(指美国援助)”,并且他留言,称自己是昆明知青,于1969年在下乡途中,在滇缅公路的下关、祥云、永平段上看到了裸露铺设的锈迹斑斑的输油管。
我多么希望还能够回到当年我参加测设油管的地方,凭吊那“古战场”。
中印油管
中印油管,也被称为ABC油管。A代表印度的阿萨姆邦(Assam),8是缅甸(Burma),C是中国。中印油管西起印度加尔各答,经阿萨姆邦,沿史迪威公路过缅甸,一直到云南昆明。1943年前后,中缅印战区的盟军突破山河之阻和日军的轰炸占领。修建了这条全长约30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美军官方统计,在铺设输油管的施工中,美国工兵、印度军队、中缅印当地劳工的出工量达到300万个工作日。输油管海拔最低在阿萨姆邦,91米,最高在缅甸,海拔2800米,中国境内的油管海拔大部分都超过了2100米。
比起史迪威公路和驼峰航线,中印油管的存在和其战时贡献鲜为人知。根据资料,从联结完成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输油管系统一直在使用,提供了一线战区超过48.8万吨的油料。60多年后,昔日埋于地下或平行于公路的油管早被用作他途,印度人和缅甸人拆毁了油管作电线杆、旗杆甚至栅栏,而云南境内的油管据说在20世纪60年代克拉玛侬油田大会战时运到了新疆。2008年,国内调查和研究滇缅抗战史的知名学者戈叔亚先生重走中印油管线。沿途拍下了不少油管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