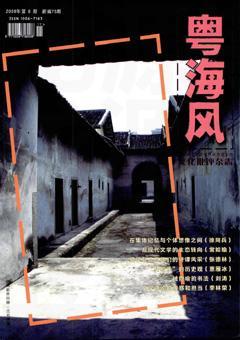追忆复旦恩师们的讲课风采
张德林
一、先从“十大教授”说起
我每次回母校复旦大学中文系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会,在文科大楼中文系办公室的走廊上,看见高高挂着以陈望道、郭绍虞、刘大杰等为代表的“十大教授”的大幅照片,内心总是感慨万千,难以平静。时间是人类的第一杀手,太无情了,这“十大教授”均已作古多年,然而他们的丰功伟绩,对学术、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和巨大的社会影响,是永无止境的,不可磨灭的。
回忆建国初期我在复旦中文系求学的情景,那时,这“十大教授”都还健在,我聆听过他们的教诲,接受过他们的熏陶,他们当年在课堂上及课外的神情姿态,音容笑貌,至今还历历在目。此外,我还听过其他许多名教授的课,同样获益匪浅。
今天的年轻学子,听我说起曾经接受过那么多全国第一流名教授的言传身教,感到惊讶,并深深地为我庆幸。其实,生活和学习在那个时代,倒觉得是非常自然的事。
二、复旦——“民主堡垒”
复旦向来有“民主堡垒”的称谓。在学术上,发扬“五四”精神,民主办学,利用上海这一大都市学者云集的有利形势,把许许多多德高望重的学者“请进来”任教。我想,这与当年陈望道校长和郭绍虞系主任的威望、广阔学术视野、兼容并包的治学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自己是公认的第一流大学者,因而容纳得下各路英雄好汉来共同参与教育事业。北方有“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提倡科学、民主、自由的学术传统一直得到继承和张扬;南方则有复旦大学,可与之媲美,形成两座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南北对峙的格局。
三、教授们的教学剪影
我是1950年秋考入复旦中文系的。1953年秋,因国家贯彻“总路线”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到成立才一年光景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迄今。那时,复旦中文系招生人数不多,每个年级不超过四十名。经历1950年秋冬的一次抗美援朝大学生“参干运动”,走掉一批优秀学生,剩下来每个年级只有二十来名,四个年级总计学生人数只有七八十名。那时在校的名教授和校外的兼职教授总数加起来也有好几十名。学生之间,年级与年级之间活动频繁,相互串门,唱歌唱戏、听音乐、看电影、跳苏联式集体舞,彼此都很熟悉。师生之间,关系密切,课堂授课只是方式之一,学生经常去老师家求教,老师欢迎学生登门,聊天、谈心,亲如一家人。我常去的有方令孺、鲍正鹄、蒋孔阳、贾植芳诸位先生的家。这种优良风气到了1957年便荡然无存了。
当时的复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教授都得上教学第一线,讲师和助教倒很少上课。助教在升讲师之前,非得“试讲”一定数量的课不可,教授亲自来听,并且还要征求学生的意见,要求相当严格。现在著名的古典文论专家王运熙教授、博士导师,汉语语法专家胡裕树教授,在1952年初都还只是助教,他们的“试讲”就在我们班上进行,系主任郭绍虞先生坐在下面听课。蒋孔阳先生原系海光图书馆馆长,1951年调入复旦新闻系,次年转入中文系,任讲师。“文学概论”分三个单元讲授。我是当时该课程学生课代表,负责师生之间的联系工作。第一单元“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由校外的刘雪苇先生(大胡子,绰号老马克思,当时的文艺处处长)讲授,在登辉堂以作大报告的方式上课,文科各系(中文、新闻、教育)学生都得来听。第二单元,文学批评,由校外王元化先生(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讲授,他当时很年轻,只有三十一岁。他讲课广征博引,说理精辟,擅长从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分析中发表自己的独立观点。讲到激动处,每每用手指节敲讲台桌子。第三个单元,文学的潮流,则由青年讲师蒋孔阳主讲。他四川万县口音较浓,普通话说得不错,略带口吃。他准备非常充分,说理重实证,逻辑层次清晰,口语化,深入浅出,少用名词术语,同学们对他的讲授是满意的。
写作和现代文选是中文系的基础课,教师的实力特别强。教我们年级写作的,先后有三位教授,都是二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许杰先生20年代乡土文学杰出代表,备受鲁迅、茅盾赞扬)、方令孺先生(方苞的后裔,舒芜的姑妈,新月派抒情散文家,巴金尊称她“大姐”、“九姑”,她比巴金大八岁,巴金说她是一个善良的人,除了“善良”外,还加上一个“坦白”)、汪静之先生(新文学史上著名的湖畔诗人),他们的讲课各有特色。尤其是许杰先生,浙江天台人,乡土口音浓。讲课从来不带讲稿,潇洒飘逸,和蔼可亲。他重视“评卷报告”,批改作业认真。一般人觉得已很顺畅的文稿,经他三言两语一指点,毛病立刻被挖掘出来了。五十岁前后的许杰先生,对文字、语言、技巧有职业性的“敏感”,到了晚年,这种“敏感”性逐渐衰退,撰文和说话便噜嗦起来了。当年经他批改过的作业,还留着眉批、夹批及各种符号批改的痕迹。如║,表示前后文气不连贯,═表示段与段之间文气不连贯;××,表示错别字或文理欠通、逻辑紊乱;△△,表示佳句,或说理透彻。虽然漫长的四十七年过去了,有个典型例子,今天仍然记忆犹新。我有一篇习作,写公共汽车上的见闻。文章是第一人称,其中出现这样的句子:“有位解放军在背后拍了我一下……”这句子看来没有什么语病,然而许先生在评卷报告中却指出,应该作这样的修改:“我觉得有人在我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回头一看,喔,原来是位解放军!”第一人称的小说或散文,都得从“我”的视角和感受出发,上面的修改,文气就顺了。他很重视写作的角度和文气的关系,文以气为主,文气不连贯,文章是无法流畅的。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却具有写作方法论上的普遍意义,我感到一辈子受用不尽。他非常强调结构方法和艺术技巧,鼓励学生多写多练,打好扎实的写作基础,争取发表。他认为即使一二十篇中能发表三四篇,也是个不小的成绩。当时有种普遍观点,作家只能从生活中来,也即是从工农兵中来,大学是不可能培养作家的。对此类说法,许杰先生是颇不以为然的。在他的鼓励下,我们班上写小说、散文、剧本、儿童文学、杂文、通讯报导、文学评论的兴趣日益增涨,蔚然成风,尽管那时可发表作品的报纸副刊、刊物和其他文学园地数量甚少,同学们投稿的发表率还是有所提高的。
给高年级学生上写作课的还有位唐弢先生。我去听过他多次的课。他是著名的杂文家、散文家,当时是复旦的兼职教授,风度翩翩,谈笑风生,出口成章,讲的是略带宁波口音的上海普通话。他非常爱才。三年级杨锡联同学,写了篇抒情散文《窗》,唐弢先生读了赞不绝口,他在课堂上说,此文在艺术上是无可挑剔的,可打满分,能与何其芳的《画梦录》媲美,可是感情太纤细柔弱了,估计现在没有一个刊物敢发表这样的散文,实在可惜。
靳以先生教我们“文艺学”,他当时四十一岁。他是巴金最亲密的战友,一起编过杂志,后来他又是《收获》的执行主编之一。他是名教授、名作家、名编辑,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精力极其充沛。抗美援朝期间,他是赴朝慰问团的作家代表,在朝鲜战场上呆过一段时间。高高的个子,头发浓密,身材魁梧,戴一副墨边眼镜,剑眉,隆準、明眸,略胖,称得上是位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的美男子。他是天津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声音清脆、宏亮,性格坦诚、爽朗。他满脸红光,讲课时有个习惯动作,经常拿出毛巾手绢揩脸上和颈上的汗水,即使已在深秋天气凉爽的日子,也是如此。他给我们的印象,身体似乎很“棒”,其实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或许,他自己并不重视。靳以1959年去世,是复旦名教授中最早逝世的一位),因为实在太忙了,估计他很少有时间备课。他几乎完全抛开课文,讲的全是他自己的阅历、见识、创作心得,以及在朝鲜战场上与许多战斗英雄交往的场景,其中最精采的是讲杨根思的战斗业绩(当时杨根思尚未牺性),这种率性而谈的讲课方式,富有激情和悟性,更能体现这位作家兼教授的个性风格。同学们很爱听靳以先生在课堂上讲的天南地北、各种各样的“故事”和社会新闻,它们大大地拓展了年轻人的生活视野。50年代初期,是靳以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他被视为“进步教授”中的一个典型。他的心与年轻人的心连在一起,他是点燃年轻人心灵的一团火,也是指引年轻人以坚定的革命态度投向生活浪潮的一盏明灯。他在参干运动中以教授的身份向大学生所作的一番即兴发言,简直就是诗篇,其鼓动和煽情作用是无可比拟的。靳以有自己的业余爱好,他堪称是一位真正的京剧行家,这点却鲜为人知。他不轻易公开演唱。有一次开师生联欢会,在学生们一再点名要求和热烈掌声中,他唱了两句《文昭关》中的散板:“伍员马上怒气冲,逃出龙潭虎渊中!”宏亮、苍劲、奔放,韵味浓郁,全场为之震惊。一听便知,他学唱须生,“幼功”厚实,底子深沉。赵景深先生是戏曲专家,又是戏迷,每逢师生联欢会,总喜欢主动“露一手”。恕我直言,赵先生昆曲唱得确实好,可是京剧唱得不怎么样。我听过赵先生唱《打渔杀家》中肖恩那几段散板和原板,圆滑而粗糙,缺少风骨和品位,远远达不到靳以的水平。
复旦的古典文学教授阵容之强,可谓全国之冠。郭绍虞的文学批评史、刘大杰的文学发展史、陈子展和朱东润的古代文学史、蒋天枢的“古典诗词论”,都是很有名望的。以上五位教授,除了朱东润先生(我未听他讲课,但听过他在系内所作的精神抖擞的学术报告),其他四位教授我都连续听过他们一学期以上的课。郭绍虞先生当时并没有讲文学批评史,却讲语法修辞学。他的语法修辞学与吕叔湘等诸家完全不同,打破主、谓、动、宾、补等常用范畴,建立自己的独特范畴和体系。他一口苏州话,说话节奏缓慢,表达时常有“这个”、“那个”的口头禅。兴致浓时,一个人在讲台周围踏方步,自言自语,伴之以会心的微笑。他的口头表达虽然有缺点,可是板书极快极佳,一堂课下来,讲的不多,板书则很详细,只要用心笔记,主要内容和精神都可以掌握的。他是位书法家,文字的俊秀挺拔,在复旦教授中堪当首位。他与书法名家沈严默是知交,在书法界的名望仅次于沈严默。
古典文学讲得最吸引人的是刘大杰先生。我们听他授课,足足有三个学期之多。他湖南口音浓,普通话说得很好。口齿特别清楚,擅长情景描绘,能把每个学生引入作品的境界中去,共受欢乐与痛苦,喜悦与哀伤。讲到屈原的《离骚》与《天问》时,刘大杰先生真是做到了全身心投入的地步,脸上忧国忧民的表情,辅之以上天、入地的手势,把屈原的精神具象化了,艺术化了。听他的课,大家感到是一种美的享受。刘大杰先生在课堂上时而用一些无伤大雅的插科打诨来增添讲课的风趣。记得有一次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时代背景,说到战争频繁,五胡乱华,他突然借题发挥:“你们知道不知道:胡通狐,狐臭就是那时传进来的。”一句话引得哄堂大笑!刚巧有位听课的女同学,狐臭顶厉害,面孔一下子通红了。同学们都心照不宣。刘先生在讲台上似乎一点不知道。刘先生的板书也是全系闻名的。他讲得快,黑板端端正正的字迹,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原来这是授课的详细提纲。这种不露痕迹的精心配置体现了这位名教授的睿智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堪称讲课艺术的一绝。
陈子展先生也是湖南人,他讲古典文学远不如刘大杰先生讲得生动。一是他家乡口音特别重,不时发出“嗡嗡”的含混鼻声,十句话中大概有三四句听不懂。他的讲课习惯,一半念讲稿,一半作解释。念讲稿时学生似懂非懂,作解释时学生仍然似懂非懂。多余的时间,他爱作自我介绍:“我是个老批评家,嗡嗡……早在30年代,我就写过……,嗡嗡……”不高兴时,他便指责“公馆派”教授如何“不学无术”。这类话是暗指章靳以和方令孺。不过,多数同学对陈子展先生的渊博的学问,刚正不阿的品格是敬佩的,对他脾气暴躁、爱骂人的缺点,视为通常的文人相轻,一笑了之。
瘦瘦的蒋天枢先生,听口音好像也是河南、山东一带人。他是王国维的嫡传弟子。他为我们讲授“历代韵文选”。他讲古代诗词赋,从来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释,讲究通篇“感悟”。他认为古文不必作字义解释,熟读后自然会明白。他经常对学生们说:“你看:王维这几首诗写得多么好,玲珑剔透,像一颗颗水晶球!”“你看:李白这几首诗写得何等妙,水晶球一般,通体透明、发光,剔透玲珑!”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抓来抓去,好像这些诗真是水晶球那样,看得见,摸得到,抓得牢!我们这批调皮学生,课后常常模仿蒋先生的口吻和手势,嘴和手并用,一边“水晶球”、“玲珑剔透”满嘴飞,一边用手抓来抓去。考试时,此类词语多用些,往往会得高分。蒋先生讲“汉赋”时,发给我们几篇讲稿《汉赋的双轨》,全用韵文写。这是他历年来精心撰写的学术论文。《汉赋》本来就难读,他的学术论文更难读。蒋先生读汉赋和古典诗词,有一套特殊本领和方法,与其说是读,不如说是“唱”。字音拖得很长,抑扬顿挫,琅琅上口,声音宏亮甜美,有点像少数民族唱山歌,相当悦耳,距离课堂外一二十公尺的地方,也能清晰可辨。阿宝是我们中的“模仿大师”,学谁像谁,碰到如此艰深的唱诗、唱词、唱赋,只得甘拜下风,自动认输。还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同班同学章培恒,落难时,曾经得到蒋天枢先生的保护和指导。他教章培恒两耳莫闻窗外事,潜心精读《资治通鉴》。章培恒现在是全国闻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博士导师,复旦的“终生教授”,享有多种特殊荣誉,这应该归功于当年蒋天枢先生的教导。
本来跟我关系更为密切的是贾植芳先生,他是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之一,教我们“外国文学”。因为有长达二十年的坎坷经历,要说的东西实在太多,这里反而只得从略了。以后有机会写专文吧。
四、聆听时政报告和学术报告
当年的复旦,每一两周都有一次时政报告或学术报告。大型报告,登辉堂可容纳一千几百人,时常坐得满满的,大多数人带着笔记本来悉心听讲,很少有打瞌睡或窃窃私语、思想开小差的现象出现。中型报告,子彬院可容纳二三百人,每个座位的右手有块特制的长阔尺把的方板,用来作笔记。
来复旦作过时政报告的有陈毅、舒同、陈其五、周而复、王力、周原冰等。
记得那是1952年的初冬的一天,气候较冷,清晨草坪上铺着薄霜和露珠。早在前两天,便已通知好听讲的队伍,估计有大人物要来作报告了。早晨八点半以前,师生们便已排队进入登辉堂,我作为学生代表,有幸与中文系教授们坐在正中前面四、五排。登辉堂内座无虚席。上海市内其他高校的教师代表也来参加了。九点正,陈毅市长穿着一件皮茄克(当时很少见,现在已不稀奇)戴着一副墨镜出现在讲台上。他的浑厚、粗犷、低沉、极有风趣的讲话开始了。开场白第一句就出人意料:“兄弟我今天来复旦,与诸位教授和同学见见面,感到非常荣幸!”他不用发言稿,随心所欲,与大家“谈家常”。总的意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前段时间的三反、五反,这段时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都出于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片苦心。”“思想改造是一辈子的事,要慢慢来,性急不得。”缺点错误人人都有,包括我在内,我也在写检讨,写交待,如果党纪允许的话,我愿意向诸位坦白。”“好些将军、高级干部,过去战功赫赫,现在也犯了错误,群众有气,不让他们下楼哩!”“一切都要向前看,不要怕嘛!”“不要给知识分子简单地分类,什么白色、红色,这不利于团结。”“又红又专的口号不要随便提。”他的讲话简明、扼要、干脆,不拖泥带水,显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严峻放达的气派和风范。陈毅市长的讲话仅一个小时。他讲话的意思,当年我就觉得与报上宣传的思想似乎有些不同,要宽容、坦诚得多。听起来十分亲切。有些话,仔细体会,带有纠偏的意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时正在复旦进行,确实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因为前几周,由于上面抛材料,刘大杰先生一时想不通,在轮船码头上跳黄浦,被当地救起来。此事引起各系教授们纷纷议论,人人感到自危。当时的高教局长陈其五,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清晨便赶到复旦,召开了各级干部会议,一再重申对教授们的思想改造要强调自觉性,千万不能搞“相互揭发”,特别是要重视社会影响。外语系教授孙大雨,根据这些观察到的事实,早有“李政文文戏武唱,陈其五武戏文唱”之说。陈毅市长的讲话更是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陈毅市长讲话结束后,还有舒同(当时的华东局宣传部长)的长篇报告。直至下午一点多钟整个大会才宣告结束。其时登辉堂下面的草坪上仍然聚着数以百计的学生(登辉堂容纳不下的学生,只能靠拉线广播坐在草地上听),肚子尽管在唱空城计,却一再高呼要与陈毅市长见见面。陈毅市长答应他们的要求,随即又在登辉堂的阳台上向同学们作了十多分钟的即兴发言。可见建国初期陈毅市长在大学生中的威望是多么崇高!
复旦的学术报告,可谓涉及的学科广,质量高,丰富多采。我听过马寅初的经济学报告,华罗庚的数理哲学报告,金仲华、王芸生的新闻学报告,朱光潜的美学报告。郭化若的军事辩证法报告,聂绀弩的《水浒》文本艺术演变报告。每个报告都是主题鲜明,观点独特,杂沓纷呈,新意迭出。限于篇幅,只能点到为止,不作阐发了。每次报告,都由陈望道校长以主人的身份亲自把主讲的客人引入会场,他先作简要的介绍,一口义乌话,不超过五分钟。他始终坐在讲台一旁,仔细听讲,从不中途退席。中文系邀请的中型报告,大都在子彬院内,全部由郭绍虞先生主持会议。
复旦建国初期学风如此严谨、丰富、活跃,我相信与两位一级教授的治学精神得到认真贯彻分不开的。陈郭两教授对复旦大学和复旦中文系的贡献是巨大的,至今人们还在缅怀他俩,还在追忆那个辉煌的年代(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建国以来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这点邓小平同志多次下了明确的结论。极“左”思潮的干扰,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早已出现,但那时还不是主流。如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批判两胡(胡适、胡风),乃至发展到反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但那时“左”的错误毕竟还限制在局部范围之内,知识分子挨批挨整的现象尚属少数。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情况就全面恶化了。复旦的学风和政治氛围与全国的高校一样,出现全面逆转的态势。这是大势所趋,谁也无法挽救的。中国人民还要经受将近二十年的巨大精神灾难,正像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噩梦,吃尽了相互摧残、自我折磨的苦头,到了1976年秋冬之际,才算醒悟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