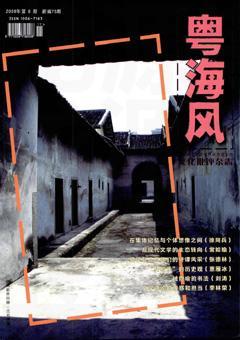后现代文学的生态转向
常如瑜
所谓后现代文学,它实质上是一个基于现代性文学之上的笼统的概念。之所以说它笼统,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的概念来明确地定义它。后现代文学最初产生于后现代诗歌当中,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很多与现代性及后现代批评的相关资料中找到证据,例如,马泰·卡林内斯库就列举了众多相关的诗人:兰德尔·贾雷尔、约翰·贝里曼、查尔斯·奥尔森[1]等等,这些诗人的作品都反映了一个模糊的、复杂的主题,即后现代主题。
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后现代文学样式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后现代文学的精神之一。对于后现代来说,现代性是其重要的精神来源。包括尼采、海德格尔等在内,他们同时既是现代性思想的源头,同时也被后现代视作精神之源。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性的结果是失败的。在文学方面,现代性终究难以掩盖悲观和厌世的心态,以及集体潜意识深处无法排解的人类的恐惧与焦虑。恐惧和焦虑的情绪既来自同类之间的竞争,也来源于自然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短期威胁和长期隐患。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映了现代性带来的人类的精神危机,另一方面则表现物质欲望无限膨胀的人类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并且预言人类将毁灭于对自然的破坏之下。
一
在这个基础上,精神生态这一概念,或者说这一新型的人类精神存在方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推崇,它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解决由现代性带来的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正如列奥塔所说的知识的合法化过程那样,现代性所代表的知识系统是精神生态所代表的人类认知体系,也是一个着眼于未来的知识系统。建设性后现代视域下文学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它着眼于对未来人类的精神建构,旨在建立一种新型的人类与自然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关系。
所以,生态文学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生态批评兴起,可以说是建设性后现代生态主义的重要体现。同现代性以及解构性后现代文本相比,生态文学更具建设性意义。现代性以及激进的后现代文学注重对传统的颠覆,例如,一些现代派文学家喜欢采用复杂、回环的解构,超越传统语法的修辞方式等,来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精神状况。卡林内斯库在他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2]中使用当代著名小说家埃科的先锋派作品为例,阐述现代小说是如何“反传统”的。因此,与传统的文学叙述方式相比,在内容的阐释方面,现代以及后现代文学都具有革新式的特征。
但是,先锋派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学对传统主题的后现代式阐述,并不能够改变人类内心深处的焦虑。埃科的中世纪式神秘小说虽然能够满足现代人寻求刺激的心理,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集体无意识的焦虑。在某些时候,后现代文学批评在形式上甚至会走向极端,走向过度阐释。因而,激进的后现代文学并不能够真正为人类精神指引方向,他们的作品也仅限于个人式的宣泄。与传统作品相比而言,结构的复杂性虽然说是一种突破,但是在精神实质上却并没有很大的进展。尤其是从潜在的心理层面上看,具有解构精神的后现代文学只是现代性的一种延续,甚至可以说是现代性反叛和破坏性精神的延续。“从两种观点来看[3],后现代主义都显得是一种‘放松,或是艺术标准的放松,或是审美批评的内在政治标准的放松。”[4]卡林内斯库的论点切中要害,他对后现代的批评也代表了众多质疑的声音。在他看来,后现代文学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不确定性”风格,这种不确定性正是解构性后现代文学在人们的头脑里构筑的“幻影”,然而这种虚无性也正是它遭到批评的原因之一。
其实,无论叙述手段,还是结构组织方式等文学式样的变化,都不能从根本上阐释后现代文学的真正价值。尤其是具有生态意义的文本,这些作品所表达的与那些以人为唯一主角的作品有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更多的是体现在精神层面。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在生态层面上的意义似乎更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相比起文学的技术手段而言,后现代所主张的生态主义及由此而萌发的生态运动更能够充实人类的心灵和精神。例如,受到现代性以及后现代精神影响的南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它们对于人类精神的意义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这些作品当中看到一种新的知识体系(精神体系)——精神生态。
二
对新的知识体系的向往,并非存在于少数人中间。例如,在一些现代批评家或是哲学家看来,现代艺术是一种逃避——“艺术家是在逃避内在心灵的混沌状态,逃避神经病患者被折磨受抑制的精神,逃避混乱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精神病,逃避自我变态心理以及社会的无政府状态”。[5]正像埃德曼一样,更多的人依然希望能够有一种秩序,一种让人类心灵能够把握的精神性的秩序,而非完全是破坏性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内心深处有一种对秩序的渴望,这种渴望或者可以认为是人类集体潜意识深处潜藏着的融于自然生态体系之中的希望。尤其对于20世纪初期的学者而言,人类精神的种种病症以及思想体系的混乱,已经造成了诸如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现实悲剧。此外,现代性对自然界的破坏和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也让更多的人试图寻找人类精神的出路。因此,人类集体心理当中存在的对良性秩序的渴望,也是基于种种现实问题而产生的。
文学艺术作品的生态转向,精神生态在文学艺术中地位的确立,还带来了另一种转变,这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
在论及这种变化之前,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人类与自然之间“旧”的关系。别尔嘉耶夫在他的《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中将这种关系归结为一种人类精神对自然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则是人类精神的解放和对自然的胜利。显然,他的见解也代表了一些现代主义者的基本观点。甚至在文学艺术方面,他也认为人类艺术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的一种超越:“改变了的世界就是美。美是对世界的重负和丑陋的克服。通过美发生的是向改变了的世界的突破,向与我们的世界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的突破。这个突破发生在一切艺术创造行为里,发生在对这个行为的一切艺术理解之中。”[6]在这里,他强调人类对世界的改变,这种改变正是人类对自身的解放,从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内)的奴役中逃逸出来,而人类所创造的艺术作品以及这些艺术品所体现的美正是导致这种改变的动力。
在这种观念当中,艺术演变成武器,象征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它是高于自然而存在的。艺术所创造的美,是纯粹的自然界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客体化的自然界和人之间的是人的创造行为”[7]。人的力量被认为是高于自然和世界的,这种力量也包括在积极进取精神指引下的艺术创造能力。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现代性,它也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一个典型特征。看看韦伯的著作,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类似的例证。
总体而言,现代性在精神上强调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虽然这种精神带来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的负作用正是将人类推向自然的对立面。在心理层面上,所谓“人类精神的解放”实质上仍然象征了人类对自然的恐惧,自然被当作奴役、压迫人类的客体而存在。于是,克服对自然的恐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之后人类一直寻觅的道理。“精神对奴役的胜利首先是克服恐惧,克服生的恐惧和死的恐惧。”[8]因此,人类精神对自然的胜利,也是从克服对自然的恐惧开始。
恐惧心理并非是一个新颖的概念,早在《圣经》当中,人们就已经意识到恐惧的强大作用。从恐惧到敬畏这个过程已经是被公认的人类学定论,因而,消除恐惧的愿望,也就伴随着敬畏的祛除,现代性所强调的祛魅,同样也类似于人类对自然的敬畏的祛除,希望将人类的精神从自然精神中解放出来的人相信“人受自然界的奴役是存在的……战胜自然界的奴役和战胜自然界自发力量的奴役,是文明的基本主题”。[9]现代文明正是沿着这条希图“战胜”自然之路前进的,受此影响,现代性在对文学艺术的认识方面,也更注重它对人类精神解放的功用。
事实上,无论人类采用何种方式对抗自然,都是人类心理失衡的一种表现。而且,每一种对抗方式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人类总是会陷入另一种新的奴役当中。即使别尔嘉耶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人,集体的人在同奴役他和威胁他的自发的自然界斗争,使其周围的自然环境人化,制造斗争的武器,这些武器位于我们和自然界之间,于是,人就进入到技术、文明和理性的劫运的现实,并让自己的命运依赖于它们。然而,人永远也达不到对自然界统治的彻底摆脱,他还周期性地要求返回自然界,以摆脱令他窒息的技术文明”。[10]不止现代文明,在现代文明之前,人类就已经在面对同样的精神问题,只是古典时期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敌对的程度并没有今天这么深入,人类对自然的作用没有今天这么广泛、深刻而已。但是实际上,人类在自然面前所感受到的精神压抑、恐惧以及紧张情绪是伴随人类发展的整个过程的。
三
在现代文明影响之下,人们只相信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拒绝自然是其最终的归宿和精神家园。自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只在少数浪漫主义者的精神世界里得到承认。“浪漫主义者总是要求返回自然界,摆脱理性的统治,摆脱文明的奴役人的规范。浪漫主义者的‘自然界从来不是自然科学认识和技术作用的自然界,不是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自然界。自然界在卢梭那里有完全另一种意义,列夫·托尔斯泰的自然界也有另外的意义。在这里,自然界是神圣的,令人愉快的,它给病态的和分裂的文明人带来医治。这个激情具有永恒的意义,人将周期性地被它所感染。”[11]
所以,在多数文学和艺术家眼里,自然并非是理性所拒斥的统治者,相反,它是人类精神的归宿。理性本身才是让人类陷入被奴役状态的根由。表面来看,文学艺术当中似乎并不存在所谓“转向”的问题。但是,这些文学作品并不代表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转向。所谓完全意义是指,浪漫主义趋向的文学艺术,并非是出于对自然的根深蒂固的喜好,它最初的动机只是出于对现代理性给人类精神带来的种种危机的质疑。这种质疑使它走向理性的方面,即走向自然、荒野,去寻求精神的解脱。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内心深处对自然的恐惧。对自然的审美也只是出于人类自身的“利益”,为了让现代文明压抑下的人类精神得以舒解,它还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态。
可以说,直到生态文学的出现,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从心理层面上来看,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是人类集体无意识深处对自然敬畏的一种表现,但是它同理性精神所宣扬的人类从奴役中解脱出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浪漫主义精神发现理性所宣扬的人类精神的解救只是一种虚妄的幻想的时候,他们开始重新找寻人类所遗失的精神,自然成为疗救精神疾病的“特效药”,但是,他们内心深处依然保有理性主义所宣扬的人类精神在万物中是至高无上的思想。自然存在的价值并没有成为人类生存需要的一部分,自然只是成为他们对抗现代文明和现代理性的武器。浪漫主义精神与现代文明的对立,只是现代文明对自然抗争的另一个版本,就像在现代理性看来,自然是人类精神的奴役者一样,对于浪漫主义来说,现代理性成为人类精神的新的奴役者。他们最终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实现人类精神的真正自由,无论从自然中解脱或是从理性中逃逸,因而,在这个层面上,自然也被“工具化”了,自然的权利和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当然,相对于现代文明和现代理性而言,他们的确拓展了人类精神的内涵。
人类向精神生态的真正转向,的确应当开始于生态文学的出现。自然真正成为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主角,在这些生态作品当中,人第一次成为配角。即使在华兹华斯的诗歌里,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人类站在自然风景之中,将自然精神融化到人类自我的精神和意志当中。然而,在生态主义的作品中,人的精神不再是一种独立的精神气质,相反,它从属于整个生态系统当中,自然真正拥有了自身的精神和意志。人们第一次意识到,自然对于人类来说不再是敌对的实体,人类也不再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相反,自然与人类是一体的,自然精神存在于人类的精神当中。在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深处,实质上就蕴涵了自然的精神,它们是一个整体,一个生态的、统一的整体。它们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相互敌对、“奴役-反抗”的关系。
[1][2][4]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周宪、许钧主编,《现代性研究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6、296—297、317页。
[3]“两种观点”分别指拒斥后现代主义的“保守”(格林伯格式)观点,和把后现代主义等同于文化消费主义的“激进”(新马克思主义)观点。参见,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周宪、许钧主编,《现代性研究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17页。
[5]欧文·埃德曼:《艺术与人》,任和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6][7][8][9][10][11]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体验》,张百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286、296、108、108、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