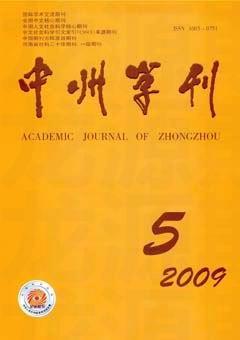论具象诗诗性的缺失
刘德岗
具象诗(concrete poetry)又称图像诗(visual poetry),它是“利用文字的排列来创造图案(如几何形状)或模拟实物(如苹果或汽车)”①的一种诗歌。这种诗歌形式在20世纪的欧美、拉美和亚洲等地区曾盛行一时。在20世纪末的台湾和香港也涌现出了一批颇有建树的具象诗诗人,如詹冰、洛夫、陈黎等。近年来,具象诗在内地也颇受一些诗作者的青睐。关于具象诗写作,诗学界时有赞誉之声。犁青认为:“写图像诗的目的之一是借图像、视觉美的优势,把语言的意旨表达得清晰和强烈,使诗语言张力达到极限。”②汉诗学者奚密说:“相对于拼音文字,中文作为一种象形文字为具象诗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象形文字的视觉效果远比拼音文字突出,而且本身已隐含音、形、义三者之间的联系。”③进入新世纪后,又有一些学者在积极倡导具象诗创作,王珂曾撰文呼吁:“大陆诗人和诗论家要改变新诗没有诗形和诗体的流行观念,要积极倡导图像诗创作及诗形实验。”④
以上诸家所言不无道理。具象诗提行技法的运用以及空白的创设,在纸质或其他平面上制造出了一种视觉美,使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美术性;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性,使诗在表达思想感情上更显自由与灵便。笔者认为,具象诗人通过文字的排列组合,创造一种视觉美的效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片面追求形式的新异,刻意制造诗歌形式的图案化效果,过分寻求视觉感官的刺激而忽略了意境的创造,这又完全背离了诗歌主要依靠词语内涵创造意象的性征,大有本末倒置之嫌。因此,笔者认为具象诗写作只能一新耳目,它不能体现诗歌创作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
(一)诗是一种想象性的语言艺术,而非观赏性的视觉艺术
我们知道,诗是一种以文字为媒介创造艺术形象的语言艺术,诗人运用语言文字把他的情思物态化,用语言文字把他感觉到的世界反映到诗的世界中。诗歌的审美特性就是运用语言文字描摹意象,表现感觉情绪,挖掘深层潜意识,为读者展示一个蕴含丰富而又玲珑剔透的诗性世界。人们鉴赏诗歌,就是为了在品味了语言的意义内涵后获得审美愉悦。许多人都读过北岛的《十年之间》,这首诗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畸形社会的种种恶德败行。这一诗意的获得正是读者在掌握了语言的意义后,通过想象和联想,体味到了诗篇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体会到了诗人抒写的特定情感。诗歌虽然只是一行行生硬的语言文字,但它所营构的诗意世界却是鲜活的,它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想象力,同时也满足了读者情感体验的需要。
然而,具象诗似乎并不具备这些美感特征。它的鉴赏主要是通过对视觉形象的观赏而跃进到它所反映的生活情景中的,读者的注意力往往是专注于“图案”而不是深入到语词内核。台湾诗人管管曾创作过一首具象诗《车站》,这首诗的前半部分运用“一张”这一语词,通过错落有致的语词排列,制造一种图案化的艺术效果,让受众者通过“图案”这一视觉形象进入到它所表现的“车站”纷扰的情景之中。读者在鉴赏这首诗时,关注点不是在诗歌语言的语义方面,而在于图画的新奇与诱人。这和梵萨特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文字的意义,但它并不存在于文字里。……它存在于文字以外”⑤的诗美规律南辕北辙。这“文字以外”的东西对具象诗作者来说确实是无足轻重。具象诗作者创作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引起受众者的视觉美感,而不是引导读者潜入到语词的意义层面。这实在是诗的悲哀,因为诗是一种想象性的语言艺术,而绝非观赏性的视觉艺术。
(二)具象诗写作易导致诗人重图案构形而轻意境创造
既然具象诗要描摹实物或创造图像,那么具象诗作者势必把创作的重心放在构形上而不会放在诗歌的意境创造上。具象诗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为创构新异的诗形而不遗余力,那么用于创造诗歌意境的精力就自然有限。诗是一种语言艺术,它是供读者阅读品味的想象性艺术,而绝不是拿给读者进行观赏的视觉艺术。无论如何诗不能追求绘画的具体或描写物体的逼真,因为这不是诗的职责。
我们还是通过具象诗的具体事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台湾诗人陈黎于1995创作的具象诗《战争交响曲》被奚密盛赞为“现代国殇”。这首诗由三个诗节组成,第一诗节是用384个“兵”字组成了一个16×24的长方形,以显示阵容的威武与庞大。第二诗节是用“兵”、“乒”和“乓”三个汉字组成,行数仍然是16行,但“兵”字逐行减少,而“乒”“乓”二字愈来愈多,此创意意在表明士兵渐渐成了伤兵。第三诗节是用一个“丘”字组成了一个仍然是16×24的长方形,表示士兵全部阵亡,每个士兵都毫无例外地变成了一个荒丘。笔者认为,这首《战争交响曲》用了1057个字的巨大篇幅,构思了如此既整齐又凌乱的画面,确实有一种“视觉震撼”效果,但它显然没有杜甫《兵车行》中“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短短14个字的内涵丰富,较之屈原的《国殇》所创造的诗意内涵也不知要逊色多少!。英国诗学家布尔顿对此类具象诗的评价是:“这用字词玩的小把戏是有意义的,也可能很有意思;但是,我怀疑其中显示的任何一点技巧是否真正跨入了诗歌,或者甚至韵文的领域。”⑥更有一些具象诗除了稍有创意和探索价值外,作为诗歌的意义则寥寥无几。这类具象诗大有脱离诗歌内容、故弄玄虚和哗众取宠之嫌。因此,有人认为,“这些令人赏心悦目的文字游戏到底算不算是诗,确是大可质疑的”⑦,这些“具体诗是可看而不可读的”⑧。
(三)具象诗给受众者提供想象和联想的东西有限
具象诗是用文字作材料构图或模拟实物,它让受众者鉴赏的主要是“形”的毕肖和酷似,它诉诸的是人的视觉想象。然而,文字毕竟不同于线条和色彩,它难以创造出丰厚的画意和画境,因此读者者在具象诗里获取的诗意信息十分有限。罗青、余光中等人对具象诗的写作甚为不屑。“罗青认为图像诗无法处理叙事题材及抽象思维过多或过于繁复的神思……余光中批评图像诗人‘不追求灵视的意境,却太追求目视的物象,甚至纸上的字形,舍本逐末,可说已到了绝境。”⑨用文字构图或模拟实物,尽管它竭力追求“形”的逼真,但它很难达到形似和神似的境地。无论管管的《车站》运用语词巧妙地创造车站里人群杂乱的场景,但它远没有庞德的《地铁车站》中“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这两句诗给读者的东西多。“语言的艺术在内容上和在表现形式上比其他艺术都远为广阔,每一种内容、一切精确事物和自然事物、事件、行动、情节,内在和外在的情况都可以纳入诗,由诗加以形象化。”⑩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在内容上具有广阔性,它具有鲜明的情感性,能为读者创造出一个丰富的情感世界。顾城那首感动了无数人的《一代人》仅有两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短短两句诗让我们感悟到“一代人”在那“黑夜”里坚强不屈的情感态度和努力“寻找光明”的人生追求,向读者传递了极大的情感力量,而具象诗的“图案”符号却不能向读者传达出如此丰厚的内涵。
诗歌语言的音、义能够产生出巨大的张力和丰富的“所指”内涵,它通过多意与含混的审美特性,在为读者创造一个丰富的“情感世界”的同时,更能为读者创造一个广阔的“意义世界”,读者的心灵可以在那个精神领域里自由驰骋。诗歌语言意义的多重与含混是诗歌的重要审美特征之一。如果诗歌语言没有这一点,它的审美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例如大家熟知的北岛的那首《恶梦》,可以说此诗的语言具有多义和含混的双重特点,诗中两个“没有人醒来”的意义决不单一,它决不仅仅指人生理上的长睡不醒;“恶梦依旧在阳光下泛滥/漫过河床,在鹅卵石上爬行/催动着新的摩擦和角逐”,此句内涵更是十分丰富,读者可以从许多层面去理解和确认。有人说多义性和含混性就是诗歌的命运,诗歌语言就是这样在多义和含混状态下建构了一个具有“增值性”的新的意义空间。
然而具象诗却用生硬的文字去构图,虽然它也能让读者通过直观形象的诱导进入那个生活经验中,但它失去了诗歌语言内蕴的多重性、含混性和情感性,因此,诗的力量就会大为减弱。莱辛说:“诗的范围较宽广,我们的想象所能驰骋的领域是无限的,诗的意象是精神性的,这些意象可以最大量地,丰富多彩地并存在一起而不至互相碰撞,互相损害,而实物本身或实物的符号却因为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局限而不能做到这一点。”(11)正因为普通诗是意象性的、精神性的,因而能给读者的心灵带来许多感悟。也正因为具象诗是“实物符号”,所以较之普通诗歌,它传达的诗意信息寥寥无几。
我国古代的回文诗和宝塔诗也具有具象诗的一些性质和特点,然而几千年来却不能像律诗或词赋那样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就很能说明问题。笔者之所以认为具象诗不是诗歌发展的正途,原因就在于具象诗背离了诗歌创作的本质特征,走进了用形式反形式的误区。
注释
①③奚密:《诗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0、71页。
②犁青:《犁青论犁青的立体诗》,香港汇信出版社,2002年,第14—15页。
④王珂:《论大陆和台港新诗的诗形建设》,《文艺研究》2007年第10期。
⑤转引自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298页。
⑥⑦⑧布尔顿:《诗歌解剖》,傅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244、241、244页。
⑨曾宗琇:《戏耍与颠覆——论80年代以降台湾现代诗的形式游戏》,郑慧如主编《台湾诗学学刊》(9),唐山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⑩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11页。
(11)莱辛:《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1页。
责任编辑:绿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