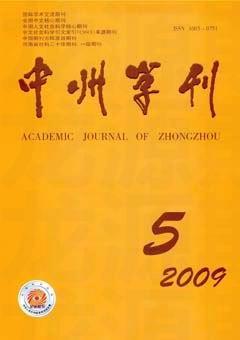风险社会中公害犯罪之刑法规制
张红艳
摘 要:自人类进入风险社会以后,防控以公害犯罪为主要表现的社会风险就成为各国刑法学者和刑事立法者所关注的焦点。欧陆刑法中设置的抽象危险犯大大降低了公害犯罪的成立标准,放松了其追诉条件,能够有效防范公害犯罪的发生。我国刑事立法也应当与时俱进,结合实际国情,在刑法典中设置某些抽象危险犯如酒后驾车罪、生产、销售假药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出售、提供个人信息罪等。
关键词:风险社会;公害犯罪;抽象危险犯
中图分类号:D924.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5—0103—03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首次系统地提出来的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概念,指20世纪中期以后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社会。在风险社会中,高科技和工业化创造了大量的财富,风险也随之大量产生。公害犯罪是风险社会的重要表现,其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刑法当中。二战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公害案件如新泻水俣病事件、富山骨痛病事件、米糠油症事件及森永奶品中毒事件等也陡然猛增,这些事件并不是天灾,而是人为造成的,是同杀人和伤害一样的重大犯罪行为。森永奶品事件中的“受害儿童现在已经步入成年,但不得不依然忍受着童年时代遭受的砷中毒后遗症的痛苦”①。与传统犯罪相比,公害犯罪具有正当行为与危害行为的交叉性、危害行为的有组织性与系统性(即常常是在一个行业领域中,由众多从业人员共同参与)、实际损害程度的难以预测性、危害行为及其所造成后果的潜伏期较长等特点。欧陆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理论在应对公害犯罪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②,我国应合理引进之,以期对风险性犯罪予以有效防控。
一、抽象危险犯及其对公害犯罪的防控功能
危险犯从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是指已经导致了该当法益侵害的可能,具体地达到了现实化程度的行为;抽象危险犯则是指由于其本身所包含的对该当法益的严重侵害可能性而被具体构成要件禁止的行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虽然同属于危险犯的范畴,但无论在特征上,还是对“危险”含义的界定及其存在形态的描述上均有所不同,两者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对“危险真实性”的认识各异。在具体危险犯中,“危险”必须是现实存在且即将发生的真正危险;在抽象危险犯的场合,“危险”更多的是一种法律拟制,而法律拟制的特点是将原本不同的行为按照相同的行为处理(包括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按照该规定处理)。因此,抽象危险犯是立法者根据其生活经验,将某种惯常发生的不法行为直接拟制为一种危险状态,该行为一旦发生,立法者就认为其具有某种典型之危险性并可因此直接定罪处罚,即立法者并不以该行为侵害结果之出现作为对其的归责要素。
抽象危险犯对公害犯罪具有独特的防控功能。第一,抽象危险犯能够降低公害犯罪的成立标准。具体危险犯的成立要求法益侵害危险实际发生,因而有明显的外在表现如将导致公共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但抽象危险犯的成立无此要求和表现。若行为人实施了某一危险行为,此行为依据客观、科学之实证结果,通常具有造成法益侵害之高度危险性,而这种危险性是立法者预先拟制之结果,即对实际有无危险不需依具体事实而为个案判断,行为人亦不需认识此抽象危险,则此行为已构成抽象危险犯。因此,在抽象危险犯的场合,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立法者所认为的“法律所不容许的高风险性行为”,则法律拟制的“危险状态”已经出现,刑法便可对该行为定罪量刑。可见,较之实害犯和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的成立门槛明显较低。第二,抽象危险犯能够减轻控方的追诉负担。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都是处罚早期化思想的体现,但就改进实害犯的缺点而言,前者比后者更具明显成效。尽管具体危险犯也是在实际损害发生前对犯罪行为加以处罚,但由于司法部门对“在什么时候某个危险才是足够具体的”常有争议,实践中经常将具体危险的确定归结于侵害是否已经发生,而除非损害确已实际发生,很难证明具体危险已出现过,所以在判断“危险状态”时常会遇到一些困扰。③抽象危险犯的成立只要求证实立法者事先预定的高风险行为的发生即可,至于行为人是否具有危险故意,其行为是否完全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人有无实害之故意及其行为与危险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都在所不问。可见,抽象危险犯的设置使得追诉机关的举证责任大为减小。
二、我国刑事立法应引进抽象危险犯理论
随着社会上各种具有严重危险性的违法行为的不断发生,加上处罚早期化思想的影响,抽象危险犯理论逐渐在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中得到体现,相关研究亦得到强化。台湾学者张丽卿就指出:“刑法危险犯的立法理由不在于那些外在世界中严重的、可以确定的结果,而应是包括对造成他人法益侵害性风险升高的行为方式的禁止。故以法不允许的特定行为方式为处罚对象的抽象危险犯构成要件有存在的价值。”④综观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事立法,抽象危险犯的大量设置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如德国刑法典中的经济辅助欺诈罪(第264条)、信用欺诈罪(第265条)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罪(第315条),日本刑法典中的单纯放火罪(第108条)等均是抽象危险犯的典型立法例。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中,抽象危险犯的设置更为普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台湾地区刑法典第185条所规定的酒后驾驶罪,在其附属刑法及单行刑法中涉及食品卫生、金融、药物、交通等领域的抽象危险犯的设置更多。
抽象危险犯对我国刑事立法而言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国内刑法学者和刑事立法者对抽象危险犯似乎都持一种敌视的态度。许多刑法学者认为,一方面,抽象危险犯理论与责任主义原则相违背,因为抽象危险犯以“拟制的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可罚性依据,似乎未造成法益侵害与法益危险,而传统刑法责任主义原则认为,刑罚适用的前提是一个行为对特定的法益有危险或造成侵害;另一方面,一旦设置抽象危险犯,则在《刑法》中必然会出现对付传统犯罪的责任主义原则和对付公害犯罪的抽象危险犯,两个相互抵牾的犯罪成立标准同时存在于《刑法》之中,显然与逻辑严谨规整、体系协调一致的完美主义刑事立法模式大相径庭。另有学者认为抽象危险犯的“抽象危险”缺乏明文规定,只能推定存在,这与危险犯概念及犯罪构成理论不符。⑤现实中一些国家的刑法普遍认为的抽象危险犯,在我国《刑法》中却以具体危险犯甚至实害犯的形式出现。如我国《刑法》第141条对生产、销售假药罪采取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具体危险犯立法模式;第142条对生产、销售劣药罪采取了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实害犯立法模式;第143条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采取了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具体危险犯立法模式;第145条对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采取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具体危险犯立法模式等。
笔者认为,刑法自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始终处于一种发展变动的状态,刑事立法也从来不是一个理论自洽、逻辑严密的规范体系。抽象危险犯理论的出现及其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刑法中的广泛应用便是刑法秉承与时俱进思想的典型体现。当传统刑法责任主义原则已经不能应对风险社会中的公害犯罪、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时,立法者就应当迅速对该原则进行修正,及时对现行立法予以相应之调整。我国近些年来环境犯罪、食品犯罪、医疗事故犯罪、交通犯罪等公害犯罪频繁发生,我国刑事立法应当积极借鉴国外抽象危险犯理论的合理内核,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在《刑法》中有针对性地设置抽象危险犯,以对公害犯罪予以有效防控。
三、在我国《刑法》中设置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建议
1.设置酒后驾车罪
在我国,每年约有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以北京为例,当今北京民众中每1000人就拥有约300辆汽车,交通事故已成为北京地区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主要肇因之一即酒后驾车。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事故处曾对媒体公布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2006年1月至12月10日,北京市共发生涉及酒后驾车的交通事故513起,死亡203人,其中酒后驾车司机自身伤亡数字为:死亡95人,重伤48人。⑥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刑法针对酒后驾车专门设置了酒后驾车罪,该罪是一种标准的抽象危险犯。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第185条规定:“服用毒品、麻醉药品、酒类或其他相类之物,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驾驶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万元以下罚金。”对于饮酒至何种程度始符合本罪所规定之不能安全驾驶,台湾地区法务部于1999年5月10日规定呼气酒精浓度达每公升0.55毫升即符合本要件,因此,检方在起诉时,只要证实驾驶人员在酒精检测时达到上述标准即可断定其酒后驾车罪成立。我国《刑法》也应当设置酒后驾车罪作为抽象危险犯,以将交通事故防患于未然。
2.修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罪状,将该罪作为抽象危险犯予以处罚
从我国《刑法》第141条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罪状表述来看,该罪以“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为要件,属于具体危险犯。对于该罪中具体危险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有如下解释:“经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鉴定,生产、销售的假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141条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1)含有超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2)不含所标明的有效成份,可能贻误诊治的;(3)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可能造成贻误诊治的;(4)缺乏所标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份的。”但众所周知,生产、销售假药是一种典型的公害犯罪行为,假药对人体危害极大,生产或者销售假药的行为一旦实施,就会对公众的健康乃至生命造成实质性威胁。因此,我国《刑法》应当修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罪状,删除“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构成要件,将该罪作为抽象危险犯予以处罚,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3.修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状,将该罪作为抽象危险犯予以处罚
由于污染环境的行为与其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模糊,而且危害后果的出现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传统刑法理论对如何规制这一行为常常束手无策。国外刑法往往将污染环境的行为作为抽象危险犯来处置,如德国刑法典第326条规定:“未经许可在规划范围以外或背离规定的或许可的程序,存放、储存、排放或去除下列垃圾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1)可能含有或产生对人或动物具有公共危险且能传播毒剂或病原体的;(2)具有致癌的严重危害或具有爆炸危险性、自燃或者非少量放射性的;(3)根据其种类、性质或者数量,足以持久地对水、空气或者土地造成不利的污染或者其他不利的变化的。在许可的设施之外,或者在严重偏离规定的或者许可的程序中,处理、存放、储存、排放或者作其他清除的,处3年以下监禁或者罚金。”⑦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却是过失犯罪,只把造成财产、人身损害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显然忽视了犯罪行为对生态环境本身的破坏。事实上,有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虽然没有造成明显的财产、人身损害,但其对环境要素本身及生态系统已造成了极大损害或构成了极大威胁,而这些危害或风险很难去除甚至经过几代人都难以根除。为了生态系统自身的良性循环,为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我国应当借鉴德国刑法典,将《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状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的”,从而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设置为抽象危险犯。
4.修改非法出售、提供个人信息罪的罪状,将该罪作为抽象危险犯予以处罚
个人信息隐私一旦被披露,其损害基本上无法挽回。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被泄露的隐私会在瞬间传遍世界。因此,对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不能仅限于亡羊补牢式的事后惩罚,而应当着眼于未雨绸缪式的风险控制。在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典中,对泄漏个人信息的行为都采用了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触角大大向前延伸。但在我国《刑法》中,非法出售、提供个人信息罪还是典型的情节犯。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删除《刑法》第253条中“情节严重”的表述,将非法出售、提供个人信息罪的罪状修改为:“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从而将该罪设置为抽象危险犯。
注释
①陈航:《日本公害犯罪理论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兰州商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②本文在此没有将抽象危险犯和实害犯对公害犯罪的防范效果作对比,因为相对于实害犯而言,具体危险犯对公害犯罪的预防效果更为明显,而若能证明抽象危险犯比具体危险犯更能有效防范公害犯罪,则已无须再将抽象危险犯与实害犯进行对比。
③正因为此,很多欧陆刑法学者都将具体危险犯视为结果犯的一种特殊形态。
④张丽卿:《交通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以德国刑法第三百十六条为例》,《罪与刑——林山田教授六十岁生日祝贺论文集》,五南图书公司,1998年,第231页。
⑤熊选国:《论危险犯》,《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⑥张婧:《酒后驾车出事故 司机死亡几率50%》,《北京日报》2006年12月16日。
⑦《德国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220页。
责任编辑:林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