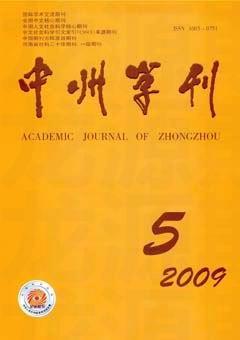循环经济法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董溯战
摘 要:自然资本安全是循环经济法的基本目标。私法理念下的循环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自主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循环经济行为常常无助于维护自然资本安全。依托作为公法的循环经济规范,政府可以弥补私法中循环经济主体的行为缺陷。欲有效实现自然资本安全目标,中国必须完善循环经济法中的政府责任制度。
关键词:循环经济法;政府责任;自然资本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5—0093—04
一、自然资本安全是循环经济法的基本目标
自然资本①安全的实质在于保障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利用。19世纪中期后自然资源法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法的形成分别是资源与环境稀缺性在法律上的系统反映。之前,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只是部分地被纳入法律的考量范围,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则很少被法律所顾及。20世纪末兴起的循环经济法以“循环”路径深化和拓展了资源与环境法平衡资源与环境供需关系的制度理性。从直接目标看,循环经济法旨在规范循环经济促进行为,保护循环经济关系主体的正当权益。从间接目标看,循环经济法旨在保障自然资本安全,即通过合理利用资源与环境,实现自然资本的可持续利用。无论是广义循环经济法所倡导的减量化、无害化理念,还是狭义循环经济法所推进的再利用、资源化制度,都力图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以使自然资本的服务能力能够持久不衰。
循环经济法主要通过废物利用制度保障自然资本安全。人类现行的经济主要是体现“资源—产品—废物”特征的线性经济,在此模式下,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必然愈来愈少,生物资源的消耗也会超过其更新速度。也就是说,这种线性经济模式忽略了不断增长的愿望、改善人的生活质量的需求与地球的有限性之间的相容问题。②为此,增长应当停止,但发展可以持续,因为增长意味着从环境进入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源流量和从经济系统反馈给环境的废弃物流量在增加,而发展则是指在吞吐量增加不超过环境承载力的情况下,环境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得到质的改进。③从增长转向发展,有诸多路径可供选择。如果说自然资本投资法律制度可以扩展自然资本的容量,即从源头培植自然资本的生命“呵护”功能,那么,经济过程中废弃物的再利用、资源化法律制度则可通过控制自然资本的耗用量、延长等量自然资本的使用时间,从中端和末端维护自然资本的功能。也就是说,循环利用资源(即把废物重新变为资源)尽管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却是推进“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德国、日本、欧盟、美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循环经济法就是依托再利用和资源化制度来推动废物循环利用的。废物的减少意味着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本依赖性的降低,进而,不可再生自然资本的服务年限得以延长,可再生自然资本的增长速度会快于消耗速度,自然资本的服务能力也可维持在稳定的水平。
二、私法理念下的循环经济与自然资本安全
循环经济因其资源节约效用而为经营者和消费者所重视。不过,私法理念下的循环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自主性,政府无法通过限制性或鼓励性制度干预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循环经济活动。因此,私法理念下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循环经济决策常常无助于维护自然资本安全。
(一)私法规则主要引导循环经济决策者关注自然资本的市场价值
在与市场相关的活动中,经营者和消费者尽管不总是、但主要以“经济人”思维作出各种决策,两者主要通过比较投入与产出来决定是否实施循环经济行为以及如何实施。当资源价格上升时,循环经济行为的相对市场收益就会提高,循环利用资源甚至优于购买新原料和新产品,一些理性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就会循环利用资源;当资源价格降低时,资源循环利用行为的相对市场收益就会降低,甚至完全丧失比较经济优势,以至于很多理性的经营者和消费者都不再进行资源循环利用。然而,上述循环经济决策常常与自然资本安全目标相悖。其一,不少循环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资源投入量多于因资源循环利用而节约的资源量,因此,当自然资本的市场供给小于需求时,虽然依照市场价格衡量,资源循环利用更合算,但资源循环利用行为所造成的有形资源和环境损耗未必就小于因此而节约的资源数量和环境容量。其二,当自然资本的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时,依照市场价格衡量,资源循环利用不合算,经济人思维指引下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不会实施此类循环经济活动,但此时的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可能更有利于自然资本的存量增加和功能增强。
(二)私法规则无法把自然资本的公共物品功能纳入循环经济决策
自然资本显著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其提供的部分物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大气、水、森林、草原、土地等自然资本既为人类提供各类私人物品(木材、饮用和经营用水、经营用土地、矿产资源等),也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氧气的生产、水与空气的净化、有机废物的分解、废弃物的隔离和无毒化、虫害和疾病的自然控制、有害宇宙辐射的防护、草地和粮食的生产、气候的调节等)④。尽管其中的私人物品可通过市场进行配置,但各类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却因具有强烈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或者排他性和竞争性很弱而无法或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配置机制。即使存在完善的私法制度,作为经济人的经营者和消费者也只能把自然资本中的私人物品的部分成本和收益纳入自己的循环经济决策,而无法把公共物品的全部成本和收益置于其循环经济决策之中。也就是说,即使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循环经济决策对自然资本的公共物品提供能力造成了损害,也难以使其承担私法上的责任。
(三)私法规则无法把自然资本的伦理功能纳入循环经济决策
自然资本既提供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必要的饮用水、食物、衣服、住房、大气、植被等),也供给非必需品(汽车、豪宅、高档饮食、高尔夫球场、高等级公路等)。自然资本中的所有可再生资源几乎都是人类生活必需品的源泉,因此,对任何可再生资源的耗竭性使用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私法理念下的经营者和消费者无法把自然资本的伦理价值纳入其循环经济决策中,而不能反映自然资本伦理价值的循环经济决策极易纵容那些符合市场规则却有害于人类生存的循环经济行为。
三、公法理念下的循环经济与自然资本安全
与私法理念下政府的消极性不同,作为公法的循环经济规范赋予政府较多的积极职责,政府可以在法律框架内推进循环经济。依托公法,政府不仅能够促使经营者和消费者把自然资本的有形价值而不是市场价值作为循环经济决策的主要考量因素,而且可以引导或强制经营者和消费者把自然资本的公共物品功能和伦理功能都纳入其循环经济决策,以实现循环经济法的自然资本安全目标。
首先,公法中的政府介入循环经济可最小化自然资本安全目标的实现成本。借助法律,政府不仅可以约束社会公众与组织,也易于把握自己的行为界限。尽管可以借助各类非政府组织推进自然资本安全目标的实现,但政府介入循环经济更能节约目标实现成本。非政府组织推进循环经济的方式有三种:其一,大型单层组织方式。依此方式,在强制力缺乏的情形下避免大范围人群的“搭便车”行为极为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其二,大型多层组织方式。依此方式,要实施协调一致的资源循环利用行动,就必须先对各个小生存权集体进行协调,然后集中各生存权集体的意见。由于涉及众多小生存权集体和多层决策,这样做的成本并不会太小。其三,小型多层组织方式。这种方式容易实施,但作用有限。对于小范围的循环经济活动,政府参与的效果可能不如小型组织的自主行动,但对于大范围的循环经济活动,政府参与就具有明显优势。由于政府只需依照法律授权对某些私人主体采取限制或激励措施,且政府不仅拥有法律授权的强力资源,还享有行政优益权,所以,无论是协商费用,还是时间投入,政府参与循环经济以实现自然资本安全目标的成本都可少于非政府组织。
其次,公法中的政府参与循环经济可最优化自然资本安全目标的实现效果。由于“搭便车”的普遍性,集体行动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推进循环经济。政府参与则可较好地克服其不足。其一,法律可授权政府制定循环经济规划并分级实施,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可依法采取相应措施督促下级政府推进循环经济。其二,当实施循环经济行为能够使相关主体的自然资本损害后果合理内化而相关主体不愿为之时,法律可授权政府强制其实施;或者,某些循环经济行为虽可为实施者带来收益却有害于公众的自然资本安全时,法律可授权政府予以禁止。这里,无论是强制实施还是禁止,都体现出作为公权力代表的政府对循环经济行为的直接干预能力。其三,循环经济行为虽有助于自然资本安全却难以给实施者带来经济或其他收益时,法律可授权政府给予实施者财政、金融方面的优惠或社会荣誉等,以鼓励其实施循环经济行为;如果某些循环经济行为不利于自然资本安全,政府也可提升相关主体的行为成本,以遏制不当循环经济行为的实施。上述法律制度安排有助于最优化自然资本安全目标的实现效果。
最后,公法中的政府可部分地克服非政府组织集体理性的局限性。集体成员的“理性”行为是通过集体行动推进自然资本安全目标的障碍之一。在小型非政府组织和大型多层非政府组织中,理性的利己会导致集体的循环经济行动无法发动或无法取得良好效果。在大型单层非政府组织中,循环经济产生的收益因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而可同时惠及不特定多数主体,且任一个人的努力都微不足道。因此,无论是理性的利己还是理性的利他,都无法使集体性的循环经济行动取得良好效果。⑤集体行动的困境使得循环经济行为的有效实施无法完全依靠非政府组织的自发行动,受立法权委托的政府则可部分地克服非政府组织自发行动的不足。依托法律获得推进循环经济的职责后,政府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适时选择行动方式。尽管进行循环经济决策的政府机构是由一定的人员组成的,因而政府也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但政府集体的规模较小,在法律的明确授权与约束下,其达成统一意志的难度不仅比大型非政府组织容易,而且易于大型多层非政府组织和小型非政府组织。
四、中国循环经济法中的政府责任制度构建
尽管公法中的政府比私法中的组织和个人更能使循环经济达至自然资本安全目标,但政府责任的合理安排是自然资本安全目标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必然选择。中国虽已初步形成了包括基本法在内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但要实现循环经济法的自然资本安全目标,还应进一步完善政府责任制度。
首先,完善政府循环经济抽象责任。其一,改进政府循环经济抽象责任授权规范的结构。日本、德国、美国和欧盟的政府循环经济抽象责任的授权规范具体而严密,中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对政府循环经济抽象责任的授权则极为简陋,这制约了中国政府循环经济抽象责任的具体落实。中国应借鉴循环经济发展成熟国家的经验,在相关授权规范中明确授权目的、授权重点、实施程序和实施期限。其二,强化循环经济行政立法的可实施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循环经济行政立法不但条款少,而且内容粗泛。中国循环经济行政立法应抛弃“能简则简”的传统做法,坚持“详至可用”的原则,对立法目的、词语解释、立法原则、权利义务等进行详细规范。其三,建立对非法源性循环经济行政规范的司法审查制度。在中国建立对非法源性循环经济行政规范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有助于改进循环经济行政规范的质量、节约司法资源、助推依法行政,而且具有可行性。其四,优化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循环经济立法权配置。政府循环经济立法权的获得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具体体现。循环经济行政立法权的强与弱应根据立法机关对循环经济事务的关注程度而定,因为这种关注影响着政府循环经济立法条件和立法积极性。
其次,完善政府循环经济宏观管理责任。在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中,政府的宏观职能主要是通过诱致性措施鼓励各类社会主体主动开展资源循环利用活动。诱致性制度包括规划制度、财税制度、专项基金制度、信贷制度、价格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产品的示范和推广制度等。这些制度使废物循环的正外部性损失得到补偿,并把资源循环利用变为有利可图的活动。正外部性使私人成本小于私人收益,而诱致性制度的实质是利用公共资源协助私人主体实现投资与收益的平衡。没有政府的这种公共援助,很多废物循环项目就会因缺乏合理的经济效益而无法启动,无形自然资本服务能力受损害、有形自然资本供给能力遭削弱的势头将无法得到有效遏制。“一个功效显著的市场经济乃是以国家采取某些行动为前提的;有些政府行动对于增进市场经济的作用而言极有助益;市场经济还能容受更多的政府行动,只要它们是那类符合有效市场的行动。”⑥中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虽然规定了许多诱致性制度,但这些制度都比较抽象,其有效实施还有赖于更多可操作性法规、规章的出台,否则,被束之高阁是必然的。中国需要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及时颁布循环经济单项法,以使各类诱致性制度得以具体化。
再次,完善政府循环经济监管责任。政府对循环经济领域的市场监管制度和宏观管理制度都是为了纠正“社会净边际产品”价值与“私人净边际产品”价值的背离⑦,其中市场监管制度主要借助强制性规则迫使各类社会主体实施资源循环利用活动,通过肯定或否定的方式约束法定的资源循环利用义务主体,使其行为依据各种法定标准如废物的分类、运输、储存、处理准则及废物回收程序、废物再商品化义务量等。强制性制度不是建立于利益诱惑基础之上,而是依托于政府的强制力。该制度形成的前提应当是,强制性义务是义务主体享有某种权益的合理结果,或者说,义务主体在遵循规则时也有合理的收益。中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虽然规定经营者和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对各种副产品、废弃产品予以循环利用,并要求建立垃圾分类制度、回收制度、市场交易制度,但由于缺乏详细的可实施性规则,相应的市场监管难以展开,这无疑降低了法律的实施效果。中国政府应当依托《循环经济促进法》这一循环经济基本法和相关单项法完善循环经济监管规则,使资源循环利用形成一个有序可循的市场。
最后,完善政府循环经济行政指导责任。中国没有行政指导基本法,现有的循环经济基本法也没有明确、系统地对循环经济行政指导行为进行规范,现有零乱的循环经济行政指导责任法律制度也十分简陋,可实施性较差。鉴于此,应当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以对循环经济行政指导形成激励和制约。其一,完善循环经济行政指导的实体制度,包括主体制度、行政指导范围、行政指导方法等。其二,完善循环经济行政指导的程序制度。循环经济行政指导程序法律制度是循环经济行政指导实体法律制度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循环经济行政指导程序可分为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其三,完善循环经济行政指导的救济制度。虽然行政指导不强迫对方接受,但是,接受行政指导的行政相对人毕竟也受指导主体影响,相对人严格依照行政指导实施循环经济事项而遭受的损失也必然与指导行为存在关联。因此,即使指导主体没有明显过错,受指导者一旦因指导而产生损失,指导者也应合理承担部分责任。
注释
①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本是指自然服务流量和有形自然资源的存量,包括太阳能、土地、矿石和化石燃料、水、活的生物体以及生态系统各部分相互作用提供的服务。也有学者认为:自然资本由资源、生命系统、生态系统构成。(参见[美]Herman E.Daly等:《生态经济学》,徐中民等译,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年,第18页;[美]保罗•霍肯等:《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王乃粒等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②[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③[美]Herman E.Daly等:《生态经济学》,徐中民等译,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④[美]保罗•霍肯等:《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王乃粒等译,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年,第182—183页。
⑤[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1995年,第70—74页。
⑥[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281页。
⑦[英]A.C.庇古:《福利经济学》,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5—187页。
责任编辑:邓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