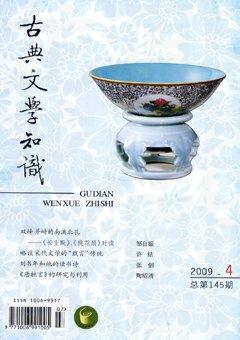《红楼梦》秦可卿死因描写新探
沈新林
《红楼梦》是一部最伟大而又最复杂的小说。小说通过贵族大家的日常生活和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描写,表现了封建贵族家庭必然衰败的主题。小说采用点面结合的手法,集中笔墨写了几件大事。第十三回写到的秦可卿之死,是小说开卷以来浓墨重彩描写的第一件大事,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备受关注。秦可卿的死因到底是“淫丧”还是“病”死,又为何要将“淫丧”改为“病”死,等等论题,历来论者颇多,但至今尚有争议。脂砚斋等《甲戌本》第十三回回末的批语云: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固有魂托凤姐及贾家后事二件,的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由此可知,小说原稿写的是“淫丧”,后来是因为秦可卿曾托梦给王熙凤,考虑到贾府后事。她弥留之际,仍然对贾府忠心耿耿,又富有远见卓识,令人感佩,于是,曹雪芹根据“老朽”的建议,大笔一挥,改死因“淫丧”为“病”死。根据该批语的口气和措词,“老朽”很可能是畸笏叟。据“老朽”的说法,小说十三回的回目似由“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改为“秦可卿死封龙禁尉”。此外,靖应鲲藏本还有“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的批语。甲戌本在正文“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上有“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的眉批,又有称正文“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是未删之笔”的侧批,还有“补天香楼未删之文”的侧批;庚辰本也有“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叹叹。壬午春”的回后批。如此看来,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批语言之凿凿,似乎可信。因为毕竟不止一个人看到过“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原作手稿。
其实,对于“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本事,在脂砚斋、畸笏叟等人以后,至今谁也没有亲眼目验过原稿,统统只是耳食而已。世界上到底是否曾经有过“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原稿呢?至今仍然还是个未解之谜。不过,我经过若干年的认真思考,坚定不移地认为,从小说创作学的角度观照,从秦可卿之死的描写在小说中的意义和价值看,她的死亡绝对不可能是“淫丧”,只能是“病死”。
秦可卿之死在小说中的意义和价值有好多条,归纳起来,大致主要有三方面:
一、在经济上,是为了表现贾府在回光返照、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仍然一如既往,讲排场,求风光,小事大办,肆意奢华,外面架子未倒,其实内囊已尽。贾府统治者利令智昏,并没有看到眼前的经济危机,为可卿操办丧事大手大脚,浪费巨资,经济方面大丧元气,渐次寅吃卯粮,坐吃山空,从而加速了衰败,以至于灭亡,有力地表现了小说的衰败主题。
二、在政治上,是借秦可卿丧葬展示贾府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极力表现其政治上炙手可热的优越地位。贾府最晚一辈的媳妇病逝,京城八公中除了贾府本身的荣宁二公之外的六公、皇室的东平、西宁、南安、北静四王等朝廷高级官员,均亲临或派子女吊丧,说明贾府当时政治地位显赫,如日中天,与京城六公、皇室四王等势要在政治上休戚与共,互有往来,关系十分密切。
三、在艺术上,秦可卿的丧事与后来贾敬、贾母的丧葬进行前后对比、对照,前面的小事大办与后来的大事小办,前面的挥霍浪费、过度奢华与后面的捉襟见肘、无奈俭省,前面的热闹风光与后面的冷落萧条,等等,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印证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一时彼一时”,“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等古训格言,侧面烘托了小说描写的封建贵族大家庭必然衰败的主题。可以说,小说原作者主要是从这三方面考虑,进行作品构思和情节安排的。
下面具体评说这三点与秦可卿之死因描写的关系。
第一点,经济意义,对于现实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最现实最直接的社会意义。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经济生活描写最能直接表现小说的政治主题。严格说来,一部优秀的作品,小说中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无条件服从主题需要,绝不能游离于主题之外。虽然《红楼梦》小说主题复杂,颇多争议,但小说在客观上写到贾府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由盛到衰,这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但这一点与秦可卿的死因关系不算太大。因为“淫丧”也好,病故也罢,总是死人。死人就要办丧事,挥霍就有了借口,小事大办,铺张浪费还是一样的。但仔细考虑,似乎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淫丧”,毕竟名声不好,对于素来号称诗礼之家的贾府,既难以启齿,不便于对外发出讣告;就是自家关上大门,秘密地大操大办,毕竟也有点底气不足。即便别人不知道底细,自己多少也总有点心虚吧。再说古人特别讲究名分,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是一般人行事的基本规则,市井细民尚且讲求名正言顺,又遑论贾府这样的贵族大家?一般说来,作者不会如此构思,也不会用几回的篇幅铺张扬厉,大张旗鼓地写一个淫妇的丧事;尤其是像《红楼梦》这样的优秀小说,作者大匠运斤,文心雕龙,构思缜密细致,绝不会出此下策,更不会有此败笔。
第二点,政治意义,与秦氏的死因就有点关系了。京城六公、皇室四王等高级官僚,作为贾府重要的社会关系,对于贾府的重孙媳妇不幸久病,不治而身亡,表示礼节性的关切。因为过去双方多有红白喜事,贺吊迎送的往来,于是纷纷前来吊丧、路祭、送葬;但如果秦可卿是淫丧,属非正常死亡,名声不好,那就很难说了。外人过多的关注反而会使贾府难堪。亲王公侯们通过不同途径登上高位,各人素质也良莠不齐,尽管他们并非个个是正人君子,但表面上肯定人人道貌岸然,对不光彩的人或事,必然避之犹恐不及,以自己的尊贵身份,谁愿意去参加一个名誉不好的乱伦淫丧者的葬礼呢?再说京城六公、皇室四王,直接代表了国家机器,意味着神圣庄严,不可侵犯,怎么可以与一个万人不齿的淫妇沾边呢?那是有损皇室尊严的。那样的文字既是对皇室的亵渎,也是对皇上的大不敬。这样构思的作品弄不好会引来文字祸端。清初的文字狱多如牛毛,让人谈虎色变,虽说小说《红楼梦》创作的乾隆初叶,情况有所好转,但文字狱并未废弛,而小说作者聪明过人,对政治问题特别敏感,决不会去以身试法。
第三点,艺术价值,与秦氏的死因关系更大。小说中的秦可卿与贾母,正好形成两个极端,对比最为鲜明。一个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宝塔尖上的人物,一个是贾府最小辈的第五代的媳妇;一个是一品夫人,一个是无名之辈;一个是公侯家庭出身,一个是养生堂的弃婴;一个四世同堂,儿孙满眼,一个婚后不育,尚无子息;一个是德高望重的耄耋老人,一个是二十岁不到的薄命女子。然而,贾府在行将衰败的回光返照时期,族长贾珍一时心血来潮,欣然决定“尽我所有”为秦可卿办丧事,她享用的是原系坏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一千两银子也没处买的,长在潢海铁网山上,“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叮当如金玉”,万年不坏的樯木棺材;为了葬礼风光,花一千二百两银子向吊丧的老内相戴权买了一个有名无实的五品龙禁尉的官衔;请了149个道士和158个和尚做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好事,至少花费一万多银子。“这四十九日,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来官去。”办丧事投入的人力甚多:二十个人单管倒茶,二十个人单管茶饭,四十个人单管灵前上香,守灵举哀,供茶供饭,四个人单管酒饭器皿,四个人单管杯碟茶器,八个人单管收祭礼,三十个人轮流上夜,照管门户。多么气派,多么风光,其规格仿佛要与皇家的国丧一比高下。秦氏的葬礼可谓挥金如土,人山人海,轰轰烈烈。然而,几年之后,贾母的葬礼就捉襟见肘,门可罗雀,冷冷清清。请看,史太君与秦可卿,一上一下,一高一低,一大一小,一尊一卑,一长一少,这一对比的审美效果是无与伦比的,非常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贾府的衰败,小说的主题十分鲜明。当然,秦氏与贾敬的对比不如与贾母对比的那么强烈鲜明,但仍然是作者创作计划中对比构思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同样是作为贾府衰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作者用心深细,用心良苦。试想,作者总不至于让荣国公遗孀老祖宗贾母与宁国府一个淫丧的重孙媳妇去进行对比吧。让贾府宗法偶像、一品夫人与一个淫妇作为艺术构思中的两个平等元素,无疑是佛头着粪的滑稽之举,显得不伦不类,必然是倒人胃口令人喷饭的败笔。
还有论者提出,秦可卿之死标志着“兼美”审美理想的失败(严安政《“兼美”审美理想的失败——论曹雪芹对秦可卿的塑造及其他》,《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4期);秦可卿是作为一个补天人物出现在小说中的(胡文彬《论秦可卿之死及其在红楼梦中的典型意义》,《江淮论坛》1980年6月),是二说不为无据,但与本论题关系不大,姑不论。
试想:如果《红楼梦》第十三回写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那么,下面的情节将如何展开呢?看来,贾府的主子们只能秘而不宣,或者诡称“病死”。然而,纸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偌大的贾府人多嘴杂,“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要不了几天,肯定流言蜚语传遍京城。那么,宁国府七七四十九天的好事如何进行到底呢?京城六公、皇室四王以及其他官员还能如期而至吗?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还会出现吗?显然,写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后面的情节就无法安排下去了,那么,读者也就看不到现在的最伟大、最复杂的《红楼梦》了。一个稍微懂得创作规律的小说家绝不会写出“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具体情节和文字,更何况还有其他政治风险呢?
脂批提到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段文字见于何种版本的《石头记》?似无记载。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俞平伯先生在《论秦可卿之死》一文中引用顾颉刚于民国十年(1921)6月24日的来信,该信中提到《晶报》上的《红楼佚话》有一段文字:“说有人见到书中的培茗,据他说,秦可卿是与贾珍私通,被婢撞见,羞愤自缢死的。”俞平伯先生认为“此话甚确”。并不惮烦劳,引用小说中现存的内证加以证明。(《红楼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其实,早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味青斋刊印的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就提出:
秦可卿本死于缢,而书中则言其病,必当时深讳其事,而以疾告于人者。观其经理丧殡,贾珍如此哀痛,如此慎重,而贾蓉反漠不相关,父子之间,嫌隙久生。(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
这或许就是《红楼佚话》的依据所在。嗣后,又有一位署名朱衣的人在重庆《新民晚报》1946年11月24日第三版发表文章《秦可卿淫上(丧)天香楼》(周汝昌《羿本纪闻》,《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二期),声称他家有“祖遗的八十回抄本《红楼梦》”,第十三回的题目就是《秦可卿淫上(丧)天香楼》,其内容与《红楼佚话》大同小异。这样,的确有所谓《秦可卿淫上(丧)天香楼》的稿本一事,似乎成了铁案。但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十多个《石头记》早期抄本和《红楼梦》刻本,在有关死因的描写中,秦可卿一律都是病死的,与朱衣“祖遗的八十回抄本《红楼梦》”并不相同。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朱衣“祖遗的八十回抄本《红楼梦》”存在的可能性。《秦可卿淫上(丧)天香楼》的稿本真的存在过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从小说创作学角度看,小说原作者不可能作出如此不明智,很可能有政治风险甚至可能掉脑袋的构思。尽管写秦可卿“淫丧”也有其不可替代的揭露批判意义。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脂砚斋、畸笏叟的批语以及各种民间传说呢?可以肯定,《秦可卿淫上(丧)天香楼》决不会是空穴来风,这只可能是作者最初曾有过的构思,也可能曾经形诸文字,形成初稿,并曾出示于脂砚斋、畸笏叟等圈内评点者。众所周知,《红楼梦》与其他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一边创作,一边评点的;或者说一边评点,一边创作的。说穿了,就是脂砚斋等人分别不同程度地直接参与了小说的创作构思。而并不是一部小说创作成功后再交由他人评点。原作者本来的构思确实想写“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这可以由第五回的人物判词以及其他未删尽的文字加以证明。
总之,从创作学角度看,《秦可卿淫上(丧)天香楼》只能是小说创作之初的原稿,或者是作者曾有过的构思和腹稿,存在时间肯定不长,只有脂砚斋、畸笏叟等少数圈内人看到过,或听说过。其时,后面的情节尚未完全展开。经畸笏叟指出以后,曹雪芹就改为“秦可卿死封龙禁尉”。可以肯定的是,畸笏叟加批语是在曹雪芹修改稿完成之后。修改的表面原因是秦可卿托梦有功,其真实原因是为小说创作顺利展开后面的情节着想,而其关键原因恐怕还是规避文字祸端。总而言之,朱衣所谓的“祖遗的八十回抄本《红楼梦》”其实并不存在,因为作者是思想卓然独立、才情超群绝伦的作家,不会写出那样拙劣的作品;同时,他也是一个头脑十分清醒的作家,是不会,也不敢去以身试法的。
既然曹雪芹根据畸笏叟的指令,对秦可卿的死因做了修改,那么,第五回关于秦可卿的人物判词以及其他未删尽的关于“淫丧”的文字又当作如何解释呢?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曹雪芹在畸笏叟的授意下匆忙做了修改,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改为“秦可卿死封龙禁尉”。但由于时间紧迫或其他原因,未及细校全部书稿,以致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如果仔细考虑,其实还应该有另一解释,那就是作者是有意为之,故意这样做的,特意留下一些或明或暗、或显或隐的信息,让读者由“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联想到“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样可以一箭双雕,既可以不授人以柄,有效地规避文字狱,又能够达到原先通过“淫丧”描写,揭露封建贵族家庭道德沦丧,生活腐败,“一代不如一代”的目的。众所周知,《红楼梦》宣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小说中许多文字可以说明,这是作者惯用的重要艺术手法之一。具体说来,就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秦可卿死封龙禁尉”不就是绝妙的注脚吗?“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是“真事”,“秦可卿死封龙禁尉”是“假语”。曹雪芹所做的修改,就是“将真事隐去”,将“真事”改成了“假语”。而作意留下这些蛛丝马迹,巧妙地给读者以暗示和启迪,这正是作者精妙的艺术技巧,也是作品的神来之笔,高明之处,即评点家所津津乐道的“一声两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性。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