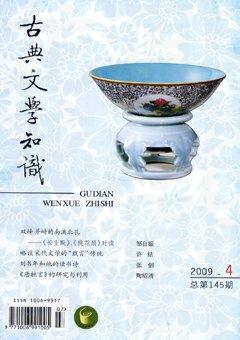《唐摭言》的研究与利用
陶绍清
二十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作为显学的唐诗研究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成果也最为丰厚。唐五代笔记的出版因承清季大型丛书的印行而屡刊不辍,但针对笔记的专门研究却寂寥冷淡,这是不太正常的现象。归其原因,正如陶敏先生所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的观念,即对笔记的性质、特点缺乏明确的认识。”(《唐人笔记研究整理工作的一点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2年)往往是搭唐五代传奇小说研究的便车,以致两者常常混为一谈。文体特征的不清晰认识、界定和区分,给笔记研究造成种种不便,也给传奇小说研究造成诸多困难。同时,历代笔记作者,虽然写作态度是严谨的,但大多标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作,远未引起学界的注意,更未作为史学考证、文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予以重视。除了《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已开始有意识地引用一些笔记史料,历代对笔记的态度也多处在闲书位置,这在前面列举的历代正史《艺文》、《经籍》志及历代书目的混乱分类上就明显看出。当然,这其中与笔记写作及内容本身的随意性有关,学者在对笔记材料的利用抱着可以理解的怀疑态度。
《唐摭言》是唐五代重要的笔记作品之一,“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是书是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最重要的两部专门文献(另一部是《登科记考》)之一,不仅大量记载了有唐一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形态、变迁等史实和保存了当代大量与科举相关的诗文作品,尤其重要的是,是书还记录了许多唐五代文人围绕科举的栩栩如生的文学活动,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对当代文人生活、思想、交往以及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但历代对《唐摭言》的研究却非常薄弱,自宋迄清,仅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文献中著录,或于历代钞本刊本首尾作简要跋语。清末民国始,才有刘毓崧《〈唐摭言〉跋》、岑仲勉《跋〈唐摭言〉》、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唐摭言》、黄永年《跋康熙时舒木鲁明〈唐摭言〉》及王素、李方《〈唐摭言〉作者王定保事迹辨正》等寥寥可数的专论和散见于一些论著中的零星述论。专论又基本局限于《唐摭言》的作者王定保的家世行迹考订及个别版本的考论,对《唐摭言》所涉及的史学、文学文献价值以及与唐五代科举制度关系的开掘和研究几乎是空白。总体上说,作为对研究唐五代科举制度有着重要文献价值的《唐摭言》的研究,是很不充分的。
最早开始关注《唐摭言》的是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卷一二“王定保”条,对王定保家世提出两点质疑:其一,钱氏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为据,认为《唐摭言》作者瑯琊王定保并非太原字翊圣之王定保;其二,王溥当为王摶之讹,但依《世系表》又不当为定保之从翁,是以存疑。钱氏提出的两个问题,也是王定保家世最重大的疑点,为后来王定保世系研究建立了最基本的支点,具有首创之功。后来的刘毓崧和岑仲勉以此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考辨。
刘毓崧《〈唐摭言〉跋》是最早对《唐摭言》作者王定保进行综合考辨研究的专文。全文洋洋万余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专考定保郡望家世;中篇考订定保行迹交游以及《唐摭言》的取材、成书时间;下篇论述定保的学识思想和道德人品,并为宋以后文献对定保的偏见进行辩诬。刘毓崧是清代学者刘文淇之子,尽读其父藏书,博通经史,曾入曾国藩两江幕,曾以殊礼异之。此跋考论结合,文献征引广泛,试图竭泽而渔,颇见功力。上篇以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所提的两点质疑为始,通过对唐代瑯琊、太原两房王氏家族成员王荛、王溥、王凝、王摶、王方庆、王方操、王璵、王倜、王损、王涣、王汶、王迈、王澄、王擢等人年辈事迹逐一考订,再结合《唐摭言》中定保有关家族成员避讳及居地的叙述,考订定保之父和郡望。中篇以《唐摭言》所载为主要依据,考证定保的游历、登进士第时间以及《唐摭言》的材料来源、成书时间。并论及王定保愤恨宦官和义不附梁,为定保思想定下基调。卷下结合晚唐浮薄学风,以《唐摭言》中多载唐代典章为据,论述定保的学识精深和性情宽厚的道德人品、撰写《唐摭言》的微言大义,有资法戒,与四库馆臣在《提要》中的评价相契。《直斋书录解题》等批评王定保弃妻入湘,“士论不齿”。刘跋也引诸家史料为证,为定保辩诬,并称他“气概之峻”、“识力之高”、“学术之邃”和“性情之厚”。与钱大昕类似札记性的杂考相较,刘跋对王定保生平进行了首次全面深入的梳理考论,也对《唐摭言》作了初步的研读。今天看来,刘跋考证不乏严密细致,但也有诸多凭主观推测的痕迹,这里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王定保本人无诗文集流传,与他交结的文人也少有提及,除了部分书目题跋等简单涉及外,史料阙如,只能从《唐摭言》文本中尽量按图索骥、顺藤摸瓜;其二,新材料缺乏,刘氏主要生活在十九世纪中期,国力萎顿,交通讯息不便,其所据材料仍以《通鉴》、两《唐书》等普通典籍为主。前人治学,穷经皓首,能如此贯通已实属不易,何况是首次拓荒。应该说,刘氏的首开之功是卓著的,其考证方法上的推测和假设也是合理和可以理解的。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唐摭言》是余先生对《四库提要》进行全面考辨的其中一篇,《四库提要辨证》是先生倾注心力的一部传世之作,尤其是“他关注的重点,是在子、史二部”(陈尚君《四库提要辨证重刊弁言》,《四库提要辨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将史、子两部二百多篇首次付印。《唐摭言辨证》是继刘毓崧《跋》之后,又一篇王定保研究的力作。此文以《四库提要》中的《唐摭言》提要为考辨对象,结合钱文和刘跋的研究成果再予以逐条逐句地详加辨证。《四库提要》对王定保及《唐摭言》的考述错讹甚多,驳之本不为难事,余先生同时将相关内容再与钱、刘二人比勘,其误处一一驳正,其正处也尊重前人已得成果,破而有立,推详既深,而正误亦明。如定保南游湖湘至入广州依刘隐行迹,《辨证》引《诗话总龟》卷二六所引《郡阁雅谈》和沈彬赠王定保诗(即《全唐诗》卷七四三《赠王定保》),驳刘氏“罢容管巡官,即游广州,而湖南特其往来之途”之误,认为“定保先至湖南依马殷,后始入广州事刘隐”(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钱文过于简略,刘跋过于繁富,《辨证》有的放矢,条理分明。稍感不足的是,《辨证》对钱刘二文原文及自注大段摘引,亦微伤主旨的突出。
在王定保事迹考辨上,岑仲勉作于1938年,发表于194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跋〈唐摭言〉》(学津本),又对上述诸人的成果做了一次清理式的论证和再考辨。文章分“事实疑误”和“家世辨论”两大部分,从唐史学的角度,对《唐摭言》中的历史故实讹误和王定保家世的存疑处精加推阐。“事实疑误”选取《唐摭言》条文中“压倒元白之半虚”、“李肇著《国史补》之朝代”等有历史错误和不确的事实,分为十节,一一考实。前九节为单件史事,第十节为多条结合。如第三节“裴度守洛与元白联句”,岑考裴度两命东都,长庆二年的首次并未到洛下任所,第二次的大和八年,元稹已于此前的五年卒世,而杨汝士则或居官京城或远守同州,四人不可能同在洛下联句,从而得出“此段故事,可为纯出臆造”(岑仲勉《跋〈唐摭言〉》,《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的结论,这些成果为我们今天整理和研究《唐摭言》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家世辨论”又分为“定保为方操后欤”、“从翁丞相溥”等五节,以刘毓崧跋所得结论为考察对象,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通常史籍,再广泛撷取地方志、地下石刻文献、《登科记考》等新出材料以及结合当时礼俗文化等加以辅证。尤其是唐人墓志的利用,对王定保家世行辈和历史年代等的推定,起了重大作用。如“从翁丞相溥”节中,以王颜《晋太原王公碑》所云“桑泉房隋奉朝请善翁,善之子聃子翁”,说明贞元时人王颜仍称隋人为翁,且两世均可称翁,认为“翁之意,常得为老成显达者之称,不专用于‘祖辈”,以驳正刘跋因定保称王摶为从翁,即断定王方庆至王摶止六世说法的可疑。不独如此,岑仲勉在完成此跋后,仍加意不断搜集和更新新发现材料,使原来文章处于一种动态当中,从而更加密实确凿。如此跋撰成十六年后的1954年,广州出土唐卢光济撰《王涣墓志铭》,岑先生又撰《从王涣墓志解决了晚唐史一两个问题》文考证,以确定1937年作的跋中所云王涣为太原二房之字文吉之王涣的正确性,地上史料与地下文献得到很好的映证。(岑仲勉《从王涣墓志解决了晚唐史一两个问题》,《金石论丛》)同样的例子还有岑先生以《故忠王府文学王固己志》所证的《王方庆六世孙璵》一文。(岑仲勉《贞石证史》,《金石论丛》)广泛使用尤其石刻文献在内的新材料,是岑跋优于前人的突出特点。稍有遗憾的是,此跋所用为学津本,未能寓目包括较常见的雅雨堂本在内的其他钞刻本,以致出现雅雨堂本已有的小注而误为张海鹏注的情况。
对《唐摭言》全文作初步校证的,首出于清人管庭芬的集钞本中,此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清道光元年至十四年,吴昂驹对《唐摭言》全文作了第一次校注和部分考证,道光十四年,方成珪在吴校基础上再校,并对吴注进行了部分考辨。道光二十三年(1843),管庭芬集吴、方两家之说,再校再注,并保留吴、方两人校语,另誊清本,是为今天所见之本。是本集三人之力,以诸家所藏钞刻本互校,并以《太平广记》、《唐文粹》、《唐诗纪事》等辅校汇证,功程甚巨,对《唐摭言》的系统整理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古典文学出版社所出版包括《唐摭言》在内的“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六十年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七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九十年代至今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书,对唐五代笔记的结集保存和整理工作均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尤其是“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不间断出版经过初步整理的笔记著作,其中就包括周勋初先生《唐语林校证》这样的精赅之作。但从总体上看,其数量和质量还显然不够。例如“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的《唐摭言》,其点读就有颇多不当,更没有进行必要的史料考证。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3年版姜汉椿先生《〈唐摭言〉校注》是目前最新的校注本,但是书所择底本、内容校注等仍有待进一步商榷之处。
《唐摭言》是研究唐代科举制度和唐人社会文学风习的一本极重要的唐人笔记作品,而对《唐摭言》的整理和研究,却与它的价值远远不相适应。这一方面与它长期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它的整理存在一定难度不无联系。在今天信息交流相当发达和文献整理有了一定的基础情况下,对《唐摭言》进行综合整理和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也是迫在眉睫的。
(作者单位:浙江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