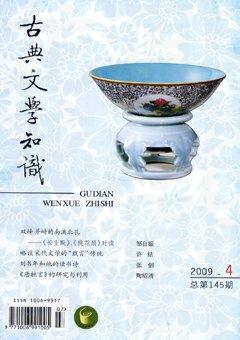周弼《唐诗三体家法序》辑考
查屏球
现存最早的《三体唐诗》是元刊的圆至注本与裴庾增注本,这两种注本前有方回序与裴庾序,依常理可以推想在元刊本之前,此书应有一个无注本在流传,原书也似应有周弼自己的序,但今存本都未见。万幸的是,周弼序没有佚失,笔者在元人吴澄文集《吴文正集》中发现了这篇序文。
在现存的文献中,最早提及周弼此书的是范晞文《对床夜语》,其卷二引用了周弼一段话:
周伯弜弼云:言诗而本于唐,非固于唐也。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于唐而止也,谪仙号为雄拔,而法度最为森严,况余者乎?立心不专,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盖诗之极盛,其实体制自此始散,僻事险韵以为富,率意放辞以为通,皆有其渐,一变则成五代之陋矣。
范晞文引用的这段话并不见于今传各种版本的《三体唐诗》中。细验文理,范氏所引之语似出于周弼所作的序中。唯周弼著作全集久佚,难以印证。但由《对床夜语》引用《三体唐诗》其他内容看,没理由判断这是范氏错引或误引的内容。《对床夜语》中还有几处提及《三体唐诗》,其中一处有引用言:
《四虚》序云: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否则,偏于枯瘠,流于轻俗而不足采矣。姑举其所选一二云:“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又:“猿声知后夜,花发见流年。”若猿若柳若花若旦暮若风烟若夜若年,皆景物也,化而虚之者一字耳。此所以次于四实也。
我们将这段话与今传本《三体唐诗》比较,元刊本《笺注唐贤三体诗法》卷十四中有:
周弼曰谓中四句皆情思而虚也。不以虚为虚,以实为虚,自首至尾,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元和已后,用此体者,骨格中存,气象顿殊,向后则偏于枯瘠,流于轻俗,不足采矣。
两段内容基本相同,文字略有差异处。范氏所引的诗句也见于同卷选的宋之问《新年作》与刘长卿《喜鲍禅师自龙山至》中。这表明范氏所见周弼编的《三体唐诗》与今传本基本上是相同的。范氏距周弼时代不远,其引周弼之语应是可信的。它们应是周弼《三体唐诗》中的佚文。我们由以上两处异文比较中也可以推断,元时流传的《三体唐诗》与范氏在宋时所见的在文字上略有区别。元刊本既增添了“元和已后,用此体者”这种具体说明,又遗漏了“化景物为情思”这样的很关键的语言。因此,元刊本不完全是对宋本周弼《三体唐诗》的原样复制,周弼原序佚于后世传本中也是有可能的事。
吴澄(1249—1334)《吴文正集》卷十九有《唐诗三体家法序》一文,曰:
言诗本于唐,非固于唐也。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于唐而止也,于一家之中则有诗法,于一诗之中则有句法,于一句之中则有字法,谪仙号为雄拔,而法度最为森严,况余者乎?立心不专,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盖诗之极盛,其体制自此始散,僻事险韵以为富,率意放辞以为通,皆有其渐,一变则成五代之陋矣。异时厌弃纤碎,力追古制,然犹未免阴蹈元和之失,大篇长什未暇深论,而近体三诗法则先坏矣。一鸠双燕,或者方且谦逊,而落木长江得意之句,自谓于唐人活计得之,眩名失实,是时昧者之过耳。永嘉尝有意于变体姚贾以上,盖未之思故。今所编摭阅诵数百家,择取三体之精者,有诗法焉,有句法焉。有字法焉,大抵皆规矩准绳之要,言其略而不及详者,欲夫人体验自得,不以言而玩也。
这段材料前半部分与《对床夜语》所引周弼的话完全相同,据此基本可断定本序作者应是周弼。理由见下:
首先,在时间上,范氏一书比《吴文正集》早很多年。《对床夜语》前有冯去非序,曰:
景定三年(1262)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书一编,语甚绮而文甚高。时夜将半,剪烛疾读,不能去手,大类葛常之《韵语阳秋》。鸡戒晨而毕,株连节解,激发人意,作而曰:美哉此书也。杜子美诗,王介甫谈经以为优于经,其为史学者又视为史,无他,事核而理胜也。韩退之谓李长吉歌诗为骚,而进张籍诗于道,杨大年倡西昆体,一洗浮靡,而尚事实,至《送王钦若行》君命有所不受,其名节有如此者,若论诗而遗理,求工于言辞而不及气节,予窃惑之,辄序于《对床夜语》之首,以补其遗,景文然之不?深居之人冯去非可迁甫。
此序的第一句话表明《对床夜语》一书至少成于1262年,而周弼《三体唐诗》应在此之前就已完成。范氏生平虽不甚详,但据程钜夫《送范晋教授江陵序》看,范氏约卒于1300年左右,《对床夜语》应是其早年时的著作
(程钜夫《雪楼集》卷十四:至元丁亥(1287),“余以侍御史奉诏求贤,驰驿至杭,众言范君晞文之贤,余因荐于朝时……范君由是连佐宪府,自尔契阔。不四三年而闻范君没。大德壬寅(1302)孟夏之月,余方坐雨黄鹄山下,乃有二士踵门,俾僮奴问焉,曰:‘杭范也。延之而望之,长身颙昂接武以进,予惊曰:‘药庄固在乎?曰:‘其仲子也。‘年若何?‘四十一矣。‘斯为谁?‘仲子之子也,二十二矣。嘻,予至杭时,范君未老,仲子弱冠,其孙甫胜衣,别半世而未老者不复可见,可见者骎骎中岁,幼者亦挺然成人。”据此推断,1287年,程初见范,范氏未老,似不过六十,其生年似在1237年前。其作《对床夜语》应似在其三十五岁前。依吴澄生平看,1262年他才13岁,这之前似不能写出如此的序文。且在《吴文正集》末列其年谱、行状、列传、神道碑等传记资料,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他的著作,均未提及他有《唐诗三体诗家法》一书,故本文应不是出于吴澄之手。
其次,现存方回《至天隐唐贤三体诗序》中有言:“其(周弼)说以为有一诗之法,一句之法,有一字之法,止于此三法而江湖无诗人矣。”此句应与上序中“有诗法焉,有句法焉。有字法焉,大抵皆规矩准绳之要”一语相对,这说明方回也见过周弼此序,并从中提取了周弼的诗学观点。方回序作于1305年,此事可表明周弼此序仍保存在当时的刊本中。方回转述与序文的相似性,也证明了吴澄集中的这篇序的后面内容,虽然不在《对床夜语》的引文中,但也应出自周弼之手。
再次,由《唐诗三体家法序》的内容看,其言“今所编摭阅诵数百家,择取三体之精者”,应是出于本书编者自己之口吻,而非他人之序。其“犹未免阴蹈元和之失”之论,也与周弼在书中所说的“元和已后,用此体者,骨格虽存,气象顿殊”的观点是一致的。由这一段前后文关系看,《对床夜语》卷二一开始列述晚宋四家诗论,多是对当朝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的批评,其顺序为严羽(1192?—1245?)、萧德藻、刘克庄(1187—1269)、周弼(1200—1257),刘克庄在周弼之前,当因其年资与影响更大。因此,这一段引用文字,与书中内容甚合,也不应是后人添加出来的。它出于周弼之书,也应是无疑问的。
最后,再由《吴文正集》形成的方式看,本文入选文集,吴氏可能并不知。《四库全书总目•吴文正集》提要有言:
是集为其孙当所编,永乐丙戌其五世孙爟所重刊,后有爟跋,曰:《支言集》一百卷,私录二卷,皆大父县尹公手所编类,刊行于世,不幸刻板俱毁于兵火,旧本散落,虽获存者,间亦残缺,迨永乐甲申,始克取家藏旧刻本重寿诸梓,篇类卷次悉仍其旧,不敢更改,惟卷首增入年谱、神道碑、行状、国史传以冠之,但旧所缺简,遍求不得完本,今故止将残缺篇题列于各卷之末,以俟补续云云。则此本乃残缺之余,非初刻之旧矣。然检其卷尾,缺目惟十七卷《徐君顺诗序》一篇,五十四卷《题赵天放桃源》,卷后一篇五十七卷《题约说后》一篇,又三十七卷《滹南王先生祠堂记》末注:“此下有缺文”而已,所佚尚不多也。……吴当所编,过于求备,片言只字,无不收拾,有不必存而存者,未免病于稍滥。然此亦南宋以来编次遗集之通弊,亦不能独为当责矣。
《吴文正集》是由其孙吴当在明代永乐年间编纂而成的,非吴澄本人手定。吴当在搜辑中唯恐有遗,只言片纸都罗列其中,部帙庞大,四库馆臣也以为其“未免病于稍滥”。窜入其他人的作品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新文丰出版公司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中的《吴文正集》四十九卷外集三卷,是明成化二十年刊本,是取百卷本重加编次,卷十一仍留有《唐诗三体家法序》,在卷中排序与百篇本同)。这篇序文也许是吴澄抄书时留下的手稿。
另外,《吴文正集》中所存的周序,称《三体唐诗》书名为《唐诗三体家法》,与现存周弼《三体唐诗》传本书名不同。现存本或名《(笺注)唐贤三体诗法》,或曰《(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皆非其旧。吴集中的序文所称也可在《对床夜语》中得到印证。《对床夜语》卷二有评周弼此书曰:
周伯弜选唐人家法以四实为第一格,四虚次之,虚实相半又次之。其说四实,谓中四句皆景物而实也。于华丽典重之间有雍容宽厚之态,此其妙也。昧者为之,则堆积窒塞而寡于意味矣。是编一出,不为无补后学,有识高见卓不为时习熏染者,往往于此解悟;间有过于实而句未飞健者得以起,或者窒塞之讥。然刻鹄不成犹类于鹜,岂不胜于空踈轻薄之为,使稍加探讨,何患不古人之我同也。
范氏所称就是“选唐人家法”,这可能是比较符合本书原貌的。本书起初的书名应是“唐人家法选”或“唐人三体诗家法”之类。“家法”之称在先,“诗法”之名应在后。至于所谓“唐贤绝句三体诗法”,有明显的辞不达意的错误,它应是“唐贤绝句”与“三体诗法”二种书名的组合。元中期,“二泉唐贤绝句选”与“周弼三体唐诗法”,是私塾中两种最流行的蒙学教材。书贾可能将两书名合成为一书,才形成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说法。现存元刊本方回序也作《至天隐注周伯弜三体诗序》,并未写出书名的全称,其简称可能是“周弼选三体唐诗”,已失“家法”一名的原貌了。序文与范氏之称相符,也足可证明《吴文正集》中的《唐诗三体家法序》应是周弼之作。
裴氏增注本在后来的影响超过了圆至原本。陶宗仪(1329—1410)《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六还曾提到了注中的内容:“《三体唐诗》裴庾注云:《广州记》:卢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为壶橘,又曰卢橘。”今存裴注本卷一戴叔伦《湘南即事》“卢橘花开枫叶衰”一句下注曰:“《广州记》:卢橘皮厚,气色大如甘酢,夏熟,土人呼为壶橘。”
(《李太白集注》卷五《宫中行乐事八首》注:《广州记》云:“卢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结实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吴录》云:“建安有橘,冬月树上覆裹,明年夏色变青黑,其味甚甘美,卢即黑色是也。”《施注苏诗》卷三十六:《广州记》:“卢橘皮厚,味酸,大如柑,至夏熟,土人呼为卢橘。”诸家皆引《广州记》解“卢橘”,文字稍有不同,亦属常见之事,皆出于《事林广记》、《文事类聚》等类书)陶宗仪所引这则内容与此基本相符。这说明增注本在元已是众人熟知的书籍。又如明人瞿佑(1341—1427)《归田诗话》上卷“三体唐诗序”一则在抄录了方回序后言:“按此序议论甚正,识见甚广,而于周伯弼三体诗则深寓不满之意,书坊所刻皆不载,而独取裴季昌序,近见唐孟高补写三体诗二帙,书此序于卷首,故特全录于此,与笃于吟事者共详参之。”(瞿佑《归田诗话》,《续修四库全书》1694册)足见,在明初,坊间更加流行裴氏增注本,以致完全失去了有方回序的原书之貌了。在瞿佑看来,当时方回序已稀见。至于在此之前的周弼自序,他自己也不知道了。周弼《三体唐诗家法》一书,约在1250至1262年间开始流行,圆至注刊刻于1305,裴庾增注作于1305年。方回为圆至注本作序时,还提到周序的内容,显然,在最初的圆至注本中可能还有周序。圆至注是“碛砂唐诗”的祖本,原来是供僧人习诗之用的教材。周序的佚失,应是它流入坊间之后的结果。仅由此事,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元代初期,一些诗学著作在普及化的同时,又在出版商业化的作用下,多有变形走样的命运。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