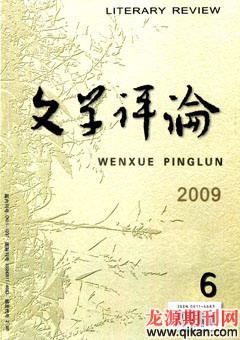评曾枣庄《宋文通论》
郑 园 陶文鹏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全宋诗》、《全宋文》等大型总集的编纂出版,宋代文学研究也渐呈兴旺之势。但与宋词、宋诗研究的春花烂熳相比,宋文研究却颇似秋叶稀疏。张海鸥先生《宋文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一文从“典籍整理”、“研究状况”、“学科建设”三个方面分析了宋文研究的冷落,指出:“如果说来词学和宋诗学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学科规模,那么,宋文研究则连个‘散文学或‘文章学的学科概念都还没有。二十世纪的词学研究可谓名家辈出,硕果累累,然而宋文研究却专家寥寥,著述不多,无论规模、层次、研究角度、方法、还是成果,都还未能成‘学。”最近,曾枣庄先生《宋文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通论》)的问世,却使这一状况大为改观。这部规模百万字的著作,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大幅度地提升了宋文研究的学术水平。
一、结构谨严内容全面
宋文研究,首先必须厘清“文”的概念。中国文学史家长期习惯使用的“散文”一词,一般指纯文学的散文,这是近代西方文论将文学作品划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种体裁中的一种。而中国传统的“文”,更多指写作学意义上的文章。曹丕《典论·论文》将“文”分为四科八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中奏、议、书、论、铭、诔、赋皆属文章。陆机《文赋》将“文”分为十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皆属文章。萧统《文选》将。文”分为三十七体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问、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除诗外皆属文章。之后宋初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姚铉编《唐文粹》、南宋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元苏天爵编《元文类》皆仿此,至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将“文”分为一百二十七体,其中百体属文。文章分类至此极矣。而清人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将诗词曲以外的全部文体,包括赋、骈文皆归于文章。可知文章实乃中国传统文学之大宗,其观念也是不同于西方纯文学观念的泛文学观念。
《通论》即根据中国古代的泛文学观念及文体分类意见,共分六编三十一章一百一十五节。第一编为宋文总论(第一至三章),分别论述宋文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宋文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宋人论文及其纷争。第二编为宋代辞赋通论(第四至八章),分别论述宋代的骚体辞、骚体赋、仿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第三编为宋代四六文通论(第九至十四章),分别论述宋代诏令、公牍、表、启以及其他各体四六文。第四编为宋代韵文通论(第十五至十九章),分别论述箴、铭、颂(含偈)、赞及哀祭文。第五编为宋代散文通论(第二十至二十七章),这是全书的主体,约占全书近半的篇幅,分别论述宋代的论说文、杂记文、书信、赠序文、书序和篇序、题跋、传、状、碑、志以及宋代的诗话、词话、文话、笔记、小说、戏剧、语体文。第六编为宋文的总体特征及其影响,实际是对全书的总结,论宋人理想同现实的矛盾,宋人的忧患感、悲凉感、旷达感与宋文的艺术特征。宋文对宋诗、宋词等其他文体的影响,宋文对元、明、清各代的影响以及宋文的对外传播。全书格局宏大,结构谨严,层次清晰,丝丝人扣。其内容之博赡,论题之丰富,几乎涉及中国文章学的全部范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论》对一些从前没有或少有人关注过的宋文体裁,都做了系统研究如宋赋、四六文、韵文,该书皆作专编研究,宋赋中的骚体辞、仿汉大赋、骈赋,律赋,该书也分别作专章研究。再如宋四六文的诏令(诏、诰、制、命令、戒敕、喻告)、公牍(国书,羽檄、露布、移、判)、表及其各种变体(笏记、右语、致辞、笺)、启以及其他各体四六文如乐语、上梁文、祈文、祝文、连珠、楹联,宋代韵文的箴、铭、颂、赞、哀祭文,皆很少有人研究,该书亦做了专编、专章或专节的阐述。即使是前人研究较多的宋代散文,该书也开拓出新的领域,如第五编第二十章“宋代的论说文”,作者指出论与说为论说文的大宗外,又用专节揭示了论说文“传、议、辩(辨)、解、原、问对、喻、应等不同称谓”(第644页)。这些详略不同的论述,填补了宋文研究的不少空白。
二、立论坚牢新见迭出
评判一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仅要看其选题是否新颖,内容是否丰富,结构是否谨严,更重要的是看它提出多少切合实际令人信服的新观点。《通论》具有创辟性的见解可谓俯拾皆是,如对北宋末南宋初文学创作水平的评价即是一例。以往论者多认为:士风的萎靡、党争的白热化以及奸臣擅权等因素,致使北宋末南宋初的数十年间,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或消极颓唐的诗文辞赋泛滥成灾,其作者也几乎覆盖了当时整个文士群。在高压政治下,失去“名节”的士大夫文人们炮制出的谄谀之作,可谓汗牛充栋,整体文学创作水平呈下滑态势,成为宋代文学史的一个转折点。但《通论》却旁征博引,对这种说法做了驳正:陆游《吕居仁集序》云:“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迨建炎、绍兴问,承丧乱之余,学术文辞,犹不愧前辈。故紫微舍人东莱吕公者,又其杰出者也。”又《傅给事外制集序》云:“国家自崇宁来,大臣专权,政事号令,不合天下心,卒以致乱。然积治已久,文风不衰,故人材彬彬,进士高第及以文辞进于朝者,亦多称得人,祖宗之泽犹在。党籍诸家为时论所贬者,其文又自为一体,精深雅健,追还唐元和之盛。及高皇帝中兴,虽披荆棘,立朝廷,中朝人物,悉会于行在。虽中原未平,而诏令有承平风,识者知社稷方永、太平未艾也。”又《江湖长翁(陈造)集叙》云:“我宋更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帝受命中兴,虽艰难颠沛,文章独不少衰,得志者司诏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娱忧纾愤,发为诗骚,视中原盛时皆略可无愧,可谓盛矣!”又《尤延之(袤)尚书哀辞》云:“虽宣和之蛊弊与建炎之军戎,文不少衰兮殷殷窿窿。太平之象兮与六龙而俱东。”周必大《跋韩子苍(驹)与曾公衮(纡),钱逊叔(伯言)诸人唱和诗》云:“崇宁、大观而后,有司取士专用王氏学,甚至欲禁读史作诗,然执牛耳者未尝无人。凡绍兴初以诗名家,皆当日人才也。今读韩子苍与钱逊叔、曾公衮等临川唱酬,略可睹矣。或疑所以然,予日:举子在场屋为学不专,为文不力,既仕则弃其旧习,难乎新功。彼有志之士,其操心也专,其学古也力,譬之追风箭云之骥,要非绳墨所能驭。故子苍诸贤往往不由科举而进,一时如程致道(俱)、吕居仁(本中)、曾吉甫(几)、朱希真(敦儒)皆是也,其又奚疑?”又《跋曾公衮、钱逊叔、韩子苍诸公唱和诗》:“国家数路取入,科举之外多英才。自徽庙迄于中兴,如程致道、吕居仁、
曾吉甫、朱希真诗名藉藉,朝廷赐第显用之。今观曾公衮、钱逊叔、韩子苍诸贤又皆翰墨雄师,非有司尺度所能得也。绍兴初星聚临川,唱酬妍丽,一时倾慕,郡之名胜。”吕午《竹洲集(吴儆撰)序》云:“建、绍、乾、淳间,人才项背相望,于斯为盛。”吴潜《魏鹤山文集后序》历述南宋文化之盛云:“渡江以来,文脉与国脉同其寿。盖高宗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谓有益治道,可为谏书。自孝宗为《苏文忠公文集》御制一赞。谓忠言谠论,不顾一身利害。洋洋圣谟,风动四方,于是人文大兴,上足以接庆历、元祐之盛。至乾、淳间,大儒辈出,朱文公(熹)倡于建,张宣公(拭)倡于潭,吕成公(祖谦)倡于婺,皆著书立言,自为一家。”国家不幸文人幸,当时的歌功颂德、谄诗谀文固然不少,但在整个绍兴议和过程中反对和议,在议和达成后仍力主抗金、防金以及反对秦桧专权的诗文也很多,出现了大量爱国文学名家,如赵鼎、李光、胡铨、岳飞、李清照、辛弃疾等等。……总之,宋代文学并未因北宋灭亡而中断,这才是绍兴文学的主流。(第79-81页)上面这段论述颇能代表《通论》的行文风格,即作者阐述论点时,往往先详细胪列古籍中有关记述,然后案论之,让材料说话,论从史出,结论自然可靠。这种述论方式,颇类于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先生以为刘氏之著有“辑录这时代的文学评论”的贡献(《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通论》无疑也附带了这种功能。文献资料的翔实丰赡,既使其立论坚牢,又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对宋赋和宋四六地位的充分肯定,是《通论》又一重要观点。自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云:“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一些赋体专著根本不论宋及宋以后之赋。但《通论》根据大量的事实证明:“宋赋可谓诸体皆备,骚体赋、骈赋、律赋、文赋都有不少名篇。”(第252页)对种种认为宋四六成就不高的观点,《通论》逐一驳斥,认为宋人例能四六,故宋人别集几乎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四六文,有些别集甚至全为四六文,并以四六名集。宋人总集亦如此,吕祖谦所编《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各种四六文约占文的三分之一,宋魏齐贤、叶棻合编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跋》一百一十卷,四六文占到三分之二。宋代出现了不少四六话,正是宋代四六文发达的产物。《通论》总结说:“中国文学史上有所谓骈散之争。在不同的时期,其势力互有消长,但谁也未能取代谁。经过唐宋两次古文革新,散文取得了优势,但骈体四六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在北宋古文革新之后的南北宋之际,骈体四六还曾风行一时,出现了不少四六名家、四六专书。”(第366页)这是切实通达的创新之论。
《通论》还发人所未发,具体论述各种分类更细的文体,慧心独具,新见迭出。如宋赋分为骈赋、律赋和文赋,《通论》对这几类赋体都有不少新的看法认为“一讲宋赋,人们往往就想到文赋。其实文赋数量很小,骈赋仍为宋赋大宗”(第295页),又认为“律赋不可一概否定”(第322页),并举徐夷《铸鼎象物赋》,蔡齐《置器赋》,吕臻《富民之要在于节俭赋》,王曾《有物混成赋》,范仲淹《金在铬赋》,范镇《长啸却胡骑赋》,秦观《郭子仪单骑见虏赋》为例,指出“宋代律赋不仅数量大,而且佳作也不少……宋人为人仕计,不得不从小练习诗赋,因此名篇佳作,代不乏人。否定律赋者往往说律赋限制太严,其实文学如戴着枷锁跳舞,越是限制严而又能自由驰骋,就越能表现作者的才华。正如律诗限制很严,但仍出现了大量名家名作一样,律赋限制虽严,也不乏名家名作。(第323页)对今人特别推崇的文赋,《通论》也有不同意见:“文赋是兴起于唐,而成熟于宋的新兴赋体,它是对徘赋、律赋的反动,是对秦汉古赋的复归,而又不同于秦汉古赋。”(第340页)“杜牧、欧阳修、苏轼创作新兴文赋后,这种赋体并末成为宋及宋以后赋的主体。《全宋文》所收宋赋约1400篇,堪称文赋者不足100篇。就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看,北宋初年很少有人作文赋。宋初的辞赋大家,如王禹傅存赋二十七篇,吴淑存赋一百篇,夏竦存赋十四篇,宋祁存赋四十五篇,范仲淹存赋三十八篇,文彦博存赋二十篇,刘敞存赋三十篇,但几乎都是骈赋、律赋或仿汉古赋,都没有文赋存世……。文赋之所以兴起,主要是因为北宋古文革新运动对宋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各种文体无不打上散文化的烙印,以文为赋同以文为诗,以文为词皆是文学散文化的表现而已。宋入并不是有意作文赋,而是受古文运动影响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文赋这种体裁……因此,宋代古文革新的部分作家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文赋的代表作家。但他们的存世文赋也远较其他赋体为少。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宋六家中,苏洵与曾巩无赋存世。欧阳修现存赋十九篇,真正可算是文赋的只有《秋声赋》一篇。”(第346页)“在苏轼现存赋二十五篇中,文赋只有前后《赤壁赋》、《黠鼠赋》、《天庆观乳泉赋》四篇。”(第348页)“苏辙现存赋九篇,比苏轼少,可算文赋者有三篇,这就是《缸砚赋》、《墨竹赋》、《黄楼赋》。”(第351页)建国以来出版的多部影响巨大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在论及宋赋时,只论欧、苏这几篇堪称经典的文赋作品,乃至使人们误以为文赋是宋赋的主流。《通论》以作品数量的精确统计和简明通达的论述,揭示事实的真相,使人们获得正确的认识。其他如对散文中“序”的看法,对四六文中“乐语”的探讨,对韵文中“铭”的研究,也都立论新颖,给予读者崭新的知识,并深受启发。
三、选文精新拓宽视野
《通论》的另一大贡献是提供了诸多富于文学性却为人们忽略的各种类型的宋代范文,并简洁灵活地赏析评价,相当于一部新型的宋文选或宋文鉴。
《通论》不是靠各种宋文选本撰写的,而是作者在校点和审订《全宋文》的过程中,读到自已有兴趣的宋文时,摘录要点并附上一些读后心得,逐渐积累的,因此《通论》所举宋文,多有前人很少论及或从未提到的。如杨亿的《殇子述》(第654页),以骈文作记叙,为其子云堂生“六百六十七日”夭折而作,抒情深挚,但从未被各种文选选录。《通论》举其末段:“因念尝读金仙子书,了知大雄氏之旨。识六尘之妄相,见诸行之无常。聚沫非可撮摩,浮云倏然变灭。轮回起于爱,必断必除;烦恼归于空,何执何著?一切虚幻,万化纷纶。又安能触类增悲,缅怀舐犊之爱;积毁成疾,自贻丧明之戚哉!予出于儒门,沉迷俗谛,犹或慕圣人之达节,希上士之忘情。诚知其无可奈何,聊以自遣耳。服名教者,得无罪我乎!”然后简析:“金仙子之书指佛书。圣人达节指子夏丧子而有失明之戚,曾子罪之(《礼记·檀弓》上)。上士忘情,指佛家万物皆幻,何必增悲之说。但作者越是告诫自己不要太执著而要‘必断必除其父子之爱,就越见其不能断除。”欧阳修的《哭女师辞》(第264页)论者亦鲜,全文仅一百一十六字,哀伤之情发自作者肺腑,漫溢字句之间:“暮入门兮迎我笑,朝出门兮牵我衣。戏我怀兮走而驰,旦不觉夜兮不知四时。
忽然不见兮一日千思,日难度兮何长,夜不寐兮何迟。暮入门兮何望,朝出门兮何之?恍疑在兮杳难追,髡两毛兮秀双眉,不可见兮如酒醒睡觉,追惟梦醉之时。八年几日兮百岁难期,于汝有顷刻之爱兮,使我有终身之悲。”《通论》评日:“全词以生前的朝挽暮迎与死后的朝出何之、暮入何望作对比,以生前的日嬉于怀和死后的一日千思作对比,特别是以倾刻之爱换得的是终生之悲作对比,充分抒发了失去爱女的悲伤之情:‘遗哀遣卷,殆骨肉之情不能忘。(刘埔《隐居通议》卷五评)”作者独具只眼,深会文心,选录书中,评鉴也切中肯綮,要言不烦。
再如《通论》第二十六章中的“砖铭、阡表、墓表与墓碣”,既举有欧阳修《泷冈阡表》、《石曼卿墓表》,王安石《宝文阁待制墓表》等传世名文,同时又举出梅尧臣《小女称称砖铭》、陆游《何君墓表》、吕大中《宋诗人刘君墓碑》等罕有人关注的佳作。其中对梅尧臣《小女称称砖铭》的评鉴亦颇简赅:梅尧臣有《小女称称砖铭》。首记其生卒时间“吾小女称称,庆历七年十月七日生,至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死。”仅活了半岁,无事可记,故主要是抒发自己的悲哀。首悲其不满一岁而夭:“呜呼,鸟兽蝼蚁犹有岁时之命,汝不然也!”次极写其无忧无虑,猝然而夭;“汝禀气血为人,丰然哲然,其目了然,耳鼻眉口手足备好。其喜也笑不知其乐,其怒也啼不知其悲。动舌而未能言,无口过,动股而未能行,无蹈危。饮乳无犯食之禁,爱恶无有情之系。若是,则得天真与保和,何病夭之乎!”末叹人生不可料,可料者是人人都要“朽而为土”:“得不推之于偶然而生,偶然而化,偶然而寿,偶然而夭。何可必也!吾将衣汝衣。敛汝棺,葬汝于野,亦人道之常分。汝之魂其散而为大空,其复托为人,不可知也。其质朽而为土,不疑矣。富贵百年者尚不免此,汝又何冤!瘗之日,父母之情未能忘,故书之砖,非欲传之久,且以志其悲云。”羡慕小女的“动舌而未能言,无口过,动股而未能行。无蹈危”,寄托了自己无限的人生感慨。(第1015页-1016页)。这类作品,不胜枚举。仿佛遗落于深海的珍珠,被作者不辞艰苦,潜游海底,一一检出,使《通论》闪耀出瑰丽光彩,也引发读者的审美趣味。可见,作者虽以泛文学或日大文学观为导向研究宋文,从而写成了这部涵括了宋代全部文章之体的大著,但对于文学的形象性、抒情性和语言艺术,仍然是高度重视的。
《通论》的作者曾枣庄先生长期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主编了大型总集《全宋文》,大型类书<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大型丛书《三苏全书》、《宋文纪事》等,对宋文及其背景资料、评论资料非常熟稔。曾先生二十馀年磨一剑,而今剑吐奇光,辉耀学林。《通论》体制宏博又抉微探幽,气脉贯通更血肉丰满。这是作者奉献给宋代文学学界的一份厚重大礼,是宋文研究的最新硕果。当然,世上无足赤之金、完美之玉。日后重版修订,我们希望作者对文献资料更细心地梳理剪裁,加强理论阐释,行文更加考究,使《通论》成为传世久远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