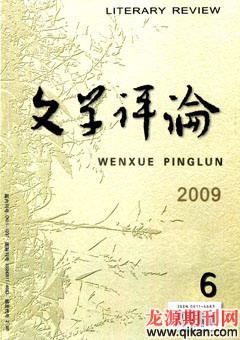后现代的香港空间叙事
凌 逾
内容提要:小说空间叙事研究在学界日益受到重视,开拓型作家在空间叙事实验上花样翻新,香港作家对此早有尝试,具有前卫性。与传统叙述方式相比,香港作品空间叙述的突破可概括为四方面:后现代地理志的空间意象、后现代建筑空间的拓扑结构、空间考古学的时间零叙述与历史故事、空间权力学的第三空间与异托邦空间,体现出后现代性。
人们习惯了从头到尾讲故事,即便故事从中间起笔,也要追溯缘由,说清结果。热奈特也从时序、时长和频率这三个层次,构筑了时间叙事学大厦。已有的香港城市史书写,同样多以线性时间叙事面目呈现,或聚焦于人物历史,或刻意讲故事,以曲折的情节吸引读者。如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叙述妓女发家史,以妓女与中外男客的情爱纠葛,隐喻香港与殖民统治者的关系转化,寄寓性与政治的此消彼长;李碧华的《胭脂扣》对香港历史的想像寄托在个人情爱命运之上。有别于上述香港书写,西西的《我城》、《浮城志异》、《飞毡》开始有意识地尝试空间叙述,创造了蒙太奇文体和蝉联想象曲式等反线性的叙述手法。本文重点论述新生代香港作家中的佼佼者董启章,他更进一步创作了空间叙述佳作:《地图集——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1997)和《V城繁胜录》(1998)。
视角产生创意。显然,空间视角是通向新发现之旅的驿站,小说家权且熄灭时间的键钮,刷进空间视野,把故事重讲一遍,叙事方式焕发出新的颜面。文本意义也产生出新解读可能,学者借此可以重新经营前人理论。例如,香港这座国际都市的发展,具有传奇性,当代作家竞相为香港城市空间绘像。本文要探究的问题是,以空间为主的小说如何书写?与传统叙述方式相比,香港作家的空间叙述有哪些突破,如何体现出后现代性?
一、后现代地理志的空间聚焦
进入21世纪,小说地理、空间叙事研究日益成为显学,这是不争的事实。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于提出了小说空间形式(spatial form)理论,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此后五十多年来,各家言论迭出。早期研究注重分析物理实体空间叙述,如查特曼认为文学空间(Iiterary space)指人物活动或居住其间的环境,运用具体术语environment、move or live in、place、setting、landscapes、climaticconditions,cities.gardens,rooms,located objects,existents即位置、场景、方位、背景、区域等表述空间存在。在空间分类方面,罗侬分出框架和架构空间,查特曼认为有故事与话语空间。
1974年,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分析出物理、心理和社会空间,自此,空间叙述研究跃升了一个台阶。凯斯特纳因此区分出另三种空间形式:图像式空间,指对故事背景和环境的描写;雕塑空间,即小说人物与视角形成的立体空间幻觉,有心理、知觉和虚幻空间-建筑空间,即小说叙事和结构上的节奏、顺序、比例和篇幅大小等。
最近,米切尔又将文学空间拓展为四个类型:字面层、描述层、文本表现的序列原则、故事背后的形而上空间。劳尔·瑞安也透析出四种空间类型:物理空间,文本自身的建构或设计,构成文本的符号占据的物理空间.作为文本语境和容器的空间。在哲学和地理学界,从福柯到伯杰,从列斐伏尔、哈维,再到克郎的《文化地理学》,都有精彩的空间论述。其中最痴迷者,当属爱德华·苏贾,三十多年来出版了《肯尼亚的现代化地理学》(1968)、《后现代地理学》(1989)、《第三空间》(1996),《后大都市》(2000),从现代到后现代研究,创立了第三空间关键词,有别于传统,形成了一套语境分析和跨学科的理论话语。
新生代香港作家不仅在空间叙述层面谋求突破,而且在空间意象营造上也有开创性。巴赫金总结过传统空间意象的四大类型——象征邂逅的道路、象征回忆的城堡、象征阴谋的沙龙、象征危机进行时的门槛。但董启章以地图作为聚焦对象,开创了新的空间意象。《地图集》以地图空间为叙述聚焦点,从地图这一物理空间载体切人,透析各种版本的香港地图。叙述者凌空,俯瞰香港这描绘在地图上的城市,抓取地图上的某一问题加以点染阐发,并置铺陈地理理论、城市空间和地图符号。运用先进科学的的地理术语,增添精确性;运用话语批评分析,渗透出深厚的反思性,勾画出既真实又虚幻的香港空间。
新的空间意象叙述不仅研究地图疆域,而且分析地图语言,即由各种符号、色彩与文字构成的表示空间信息的一种图形视觉语言。如《换喻之系谱》一节,叙述者由地图的颜色图示划分工、商、住区,联想到颜色也可标识声音、气味分区图,比如红色对应商业区、爱的宣言和中央冷气系统的细菌,赭色对应公共屋村、被强暴者的尖叫和雪柜里的断肢等。因此,从用途、听觉以及嗅觉,由物质到感官到精神状态,空间三者交叠,组合成系谱化的城市,为多面的、冲突的城市心貌图。
新的空间意象叙述不仅研究常规的地形地貌,而且涵盖文化生态。如《地质种类分歧》分析香港的地质构成,分为火成岩、火山岩、沉积以及填泥、废物,隐喻香港本不过是个由废料填海而建的岛,但又是个成份复杂的混杂性社会,讲地理本质意在深挖香港本土文化底蕴。对于1987年《香港向外地购货图》,叙述者发现,不同学派解读出迥异的语义经济学家认为这呈现出香港以“进口货品”为指标的经济存在形态;而气候学家则认为这刻画出1985年全球气候异常大变动,以及因此导致的巨型台风。董启章的笔记式风物志《V城繁胜录》,叙述者分别化身为维多利亚、维朗尼加、维奥娜、维慧安、维纳斯、维真尼亚和维安娜等,逐一讲述V城的民风物貌,如城市外相如通道、桥、街、政府及督府,城市内相如酒楼、小食、傀儡、娼妓、店铺、时装及伎艺,城市节景如正月、清明、复活、端午、七夕、盂兰、中秋等。董启章读遍了香港的每一寸肌肤,让后人难以找到下笔重述的地方。
新的空间意象叙述不仅研究地图本身,而且透视地图背后的权力话语。《地图集》的叙述者琢磨在所谓史料客观的表相之下,香港的空间形态如何在古今中外的地图绘制者手中被拿捏和重塑,进行空间版图的建构,形成空间错觉,掌控虚构权力空间。叙述者在研究香港二维、三维地图基础上,也掌控建构空间的话语权力,以解构地图和空间的形式,化生出立体多元的香港空间,成为既是建构学也是解构学的作品。
以城市空间为聚焦对象,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1972)是早期的成功范本。他想象虚构城市,叙述了五十五个可能的城市:如被垃圾包围的扩展之城;由绳索和铁链组成的蛛网城市,有座水城,没有墙、天花板、地板,只有水管的森林,年轻妇女躺在奢华的浴缸,小仙子们习惯于在水管和水道中旅行。累建在湖边的湖上城和倒转城,两城居民眼睛相连,为彼此而活,但彼此之间没有爱。忽必烈描述的梦中城市更有意思,人们只可以出发,无法回航。但《看不见的城市》关注城市的形态、内相和本质,穷尽
各色城市的可能面目,纯粹书写想象性空间,为雕塑空间。而董启章在此基础上,将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空间。
新生代作家笔下的香港,就像苏贾的洛杉矶,也像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叙事始终向侧面空间延伸,而不是依据时间序列展开,这种空间性分析和阐释,包容了物理的、抽象的、心理的、地理的、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存在的、认知的、静态的与动态的、开放以及封闭等形形色色的空间,生成了互相冲突的丰富形象,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学,成为一种后现代地理学。
二、后现代建筑空间的拓扑结构
后现代小说着力于文本序列的建筑空间设计,强调同存性(simultaneity),即打破线性文本的正常流动序列,描述诸种同时发生的事件或侧面图绘,通过空间逻辑扭结在一起,成为观察时间与空间、历史与地理、时段与区域、序列与同存性等的结合体。博尔赫斯先知先觉,在小说《阿莱夫》中表达了难以用线性方式书写空间同时态的绝望。在后现代社会,作家们的这种焦虑更为突出。随着现代影视和网络传媒的高速发展,全球事件零距离呈现,世界困境与个人难题即时而至,这种大众化、互动性的后现代处境,让人应接不暇。为此,后现代作家采取了拼贴、并置的新颖手法,文本的建构序列原则具有拓扑学(topologie)特点。
香港后现代小说叙述的同存性建筑空间,表现为拓扑学框架。如《地图集》,大框架铺排为理论篇、城市篇、街道篇、符号篇。它们本是同时存在的地理空间整体,叙述者将之切割为四个板块,便于研究它们的位置关系、本质特性。理论篇借用十五个地图学理论,如对应地、共同地、错置地、取替地、非地方、独立地/统一地等,考察香港地理理论和实地建构史。城市篇分十四节叙述香港的区域规划史,如监狱、总督府、驻军、四环九约总貌等等。街道篇细化叙述十二条街道,特写市民生活空间。符号篇解读十二个地图符号示例,如电影的花絮,深化或解构已有论述。城市篇与街道篇多为图像式实体物理空间;理论篇与符号篇以抽象视角形成了雕塑空间。小说的整体建筑空间,由四大板块又分裂并置为15、14、12、12个板块,形成小框架,小板块也采取地图拼贴蒙太奇的方式,将同时或异时发生在不同处境的空间并列,文本片段位置可以自由更换。叙事者与城市的距离经历了远——近——远的循环,读者阅读也呈现为出发与回归的过程。再如《V城繁胜录》,文本序列并置为三大板块.卷一书写城市外相,为城墙之城、城中之城,卷二书写城市内相;卷三书写城市文化风物。这种并置使得地理空间取得了连续的参照与前后对照关系,成为城市中的城市,倒影中的倒影;也使小说的叙述空间建构起对照关系,能研究空间在拓扑变换下的不变性质和不变量。
表面看来,《看不见的城市》也采取较传统的框架式建筑结构,大框架是可汗与马可波罗的对话,小框架叙述马可波罗描绘的各种城市。但《地图集》的空间结构更为复杂,正如《多元地/复地》所述:“一、地域与地域间并排而不衔接:常常会发生一个空间突然跨进另一个空间的情况……二、地域与地域互相重叠……三、‘相同的地域以不同的比例同时并存……(第52页)。重叠穿插,互相渗透,在复杂多元的蛛网中理出相对关系的线索,寻找本质特性,这正是后现代小说的同存性建筑结构的拓扑学方法。三空间考古学:时间零叙述与历史故事
后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如何既切断叙事时间的进程,又反映出故事的历史脉络?
传统小说叙述空间状态,多为场景叙述,即热奈特所说的“TR叙述时间=TH故事时间”。但《地图集》对各种时间的操控更精细微妙。在叙述时间上,为时间零叙述,这既不是热奈特所说的停顿——TR=n,TH=O,也不是省——TR=O,TH=n,而是叙述时间趋零,它不省略故事,而膨胀转化为空间叙述。首先,这跟地图空间的排斥时间特点吻合,“在一切地图制作的背后,假设了一个凝定的时间,在这‘永恒现在式的假设上,描画出地表‘在某一时刻下的状况和面貌。”(第179页)。其次,叙述者拼贴板块式结构空间,不以时间为序,而且将过去与现在并置叙述,起作用的瞬间是现在,而不是接着;还在一个同时性并置中又穿插另一个,叙述时间流仿佛被截断了,减少了向前的推动力,读者忽略了对时间的感知,因而能集中于认知空间,正如弗兰克所说,空间形式要求读者能把内部参照的整个样式作为一个统一体理解之前,在时间上需暂时停止个别参照的过程。因此,后现代小说的时间零叙述需要暗含读者的感悟,正如隐含作者术语需要读者揣摩一样。虽然作品隐含有线性的时间框架,但它基本上摆脱了前因后果的负担,将之转嫁给读者。
在故事时间方面,《地图集》以考古学家的意识,梳爬潜藏的城市史。第一,在写作时间方面,作者有意选取香港时空即将产生大变异的敏感时刻。第二,作者有意搜罗一八四一年至一九九七年间的各种版本地图。香港的地理实体空间发生过巨变。作者借由残存的地图,通过想象,解读积淀其中的历史文化,重构湮没的城市历史本面。第三,叙述者有意探索地图背后的故事时间。他并不选取来自科学化绘图时代的当代地理理论,而是来自古老而濒于失传的说法,或传教士论述。显然,这些理论更具有故事性和历史性。而且,叙述者比较前后版地图,反思香港在不同历史时空中多重身份的认同。如比较早期地图与数码地图中的总督府,发现其从早期的统摄全城,因时过境迁,堕落到1990年的被各大银行包围。这个空间小事件隐射出时代大变迁,世界的格局不再是政府势力驾驭全局,而是金融势力掌控全球。第四,在句段中有意运用错时叙述。如“据后人考证,一七八六年达尔林普尔的《中国沿岸草图》中的非地方,实为后来的香港岛”(第27页)。“传说中的维多利亚城,就像维纳斯一样,诞生于碧海波涛之中。至于它最终如何淹没,则无从稽考。而今天读图者在地图的浩瀚大海中意图寻找维多利亚城的遗迹,为的其实可能是在延续那个在想象中诞生的爱情故事”(第64页)。叙述者讲述相对于写作时间的过去,为故人故事,但其预设的隐含读者则指向未来。叙述语句将过去、未来和现在的时间并置,有意让大多数读者模糊时间概念,而让有考据癖的读者对时间更敏感。这形成了具有后现代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时间叙述形式。
四、空间权力学:第三空间与异托邦
爱德华·苏贾创立了第三空间术语,指既真实又想象、既结构主义又人文主义、既马克思主义又反马克思主义的、既唯心又唯物、既受学科约束又跨越学科的空间。其理论的基点是博尔赫斯创造的阿莱夫,即充满同存性和悖论的无限空间,福柯的异托邦(Heterotopias)理论,即指反映--社会又对抗社会的真实空间,而乌托邦则是虚构的、非真实的。异托邦偏离正常的场所,同时又穿行于其中,它向四方渗透,又使自己保持孤立。西西的《飞毡》正是再现了这种异托邦空间,进而抵抗以时间为线条、以一元论精神为线索的哲学史。
新生代香港作家叙述的形而上学空间也与第三空间意念不谋而合。董启章在实体物理空间基础之上,同时再现想象空间。他搜集实存之地理论英文为place后缀。想象之地为topia后缀。如“完全地”意念,呈现全世界每一个既有的和可能的面貌的完全地图,包含一切的地理事实的地图/地图集的终极梦幻。这种宗教地理学即是天堂的地理学,折射出人类追求与神同一的大愿。叙述者搜罗地图、解读地图,最后却发现地图学有局限:“我们的是一个给各种认识挤迫得再没有可能存在想象空间的世代。在可预见的不久将来,世界上所有以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的总合,将会让你认识到一切可能被认识的地理环境。但你将永远也认识不到的,是桃花源的入口”(第36页)。地图不可叙述之处,或逻辑不能裁判的事物,文学将之收罗,成为文学意义之所在。
乍看《地图集》,感觉作者有抢地理学家饭碗的嫌疑。叙述者研究地理文献记载,初看俨然是客观的科学语调,但《地图集》根本不准备成为地理学专著。细品起来,作品其实采用的是皮里阳秋的春秋笔法,其空间叙事具有隐喻性,具有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如作者譬喻香港为“东方半人马”社会:“人马是一种不可能的生物,因为马的成长速度比人快,在三岁时马已经完全成长,而人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孩,而且马将比人早五十年死亡”(第86页),这意在指出,泾渭分明的中西文化人马拼合不可能长久,只有中西合璧的混合体才能永存,寓意分明。《碎甸乍的颠倒》叙述第一任总督碎甸乍绘图,以南方定向,形成了陆上海下的格局,而这种视觉上下颠倒的症状,导致其在入侵阿富汗中,把敌方军队当作水中幻影,惨败告终。笔调反讽辛辣。《对反地》按地理理论,英属芒角和清属沙头角本来处于对立对反两极,但叙述者偏偏根据“阻隔一结合、分离一回归、遗忘一思念”的关系修辞原则,硬是将两者转化为以爱情为论点的关系。如《想象的高程》高程术语既指拔起于那不能容许高度的平庸,也指超出水准、想象无边。在文学家看来,高度具有暧昧诱惑性。在小说中,高程隐喻香港的积极向上攀升的欲望与历程,因此该节最后一句:“香港的实际高程也许比想象中要低一些”,话中有话,隐喻港人不要被表象迷惑,而要头脑清醒。
在苏贾的第三空间意念里,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能够同时讨论,而不扬此抑彼。反思这三种问题,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是有力的武器,能检验语言如何影响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变化。即现存的话语惯例如何成为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之结果,揭示出使这些惯例自然化的社会、历史机制,即这些机制如何让这些惯例显得自然以至于成为常识。董启章专门检视地图语言,发现人们要么以绘图方式争夺地方的领属权,成为权力实体在兴师动武之外的另一战场,地图具有外领属性。要么是透过夺取诠释权来掌控诠释对象的欲望,众多学说形成竞逐性的关系,呈现和阅读成为建构过程的一体两面。
在种族与空间层面,最适合透视种族、殖民问题的典范城市正是香港。香港在国家政权之间漂泊,港人对领地和权力深有感悟:“领地……包含着占领、隶属、管辖等富有主从关系和权力色彩的内涵。”(第28页)。不同政权绘制地图代表着主权交替,如中国人绘制而由英国人达尔林普尔印制的1786年《中国沿岸草图》,英国东印度公司辖下的海军上尉绘制的《澳门之路》,1819年版的《新安县志》,来历不详的1840年《中国海岸图》……地图本不过是一块拼图、一张薄纸而已,但出自不同权力机构的一张张地图,争夺着这座城市的领属权,地图符号甚至颜色的改变都代表着权力欲望。《戈登的监狱》殖民者企图建构理想女皇城的美好前景,想依靠监狱军队威权实现殖民统治。他们还想模仿英伦家乡气候,制造大雪纷飞的拟似经验,成就了一条“雪厂”街。据说这街名由来还有个版本,即洋人畏热,冰量消耗大,于是建立了整条街的美国天然冰仓库。他们养尊处优,错把他乡当故乡,结果到如今,群带路将重新改造,卑路乍昔日的扩张理想霸图,被现实印证为一个丑陋肮脏的“蛤蟆”。香港在权力游戏中无所依靠,无所谓归属,而城市本身一无所知,亦无从申诉。而港人在本土、大陆和外国文化等的涤荡下,经历了矛盾和融合的转变过程。
在阶级与空间层面,《街道篇》叙述了街道名字的来历和传说,最能体现港人的不同阶层、不同社会文化风情。如“通菜街与西洋菜街”街名本来源自农民夏造通菜,秋种西洋菜,但随着原居民迁出、外区人迁入以及下一代的成长,冬夏二元对立的农耕模式被消解了。农民洗脚上田,主妇们甚至混淆了通菜和西洋菜,进入了后结构主义时期。再如,随着洗衣行业的消逝,“洗衣街”原来表征为底层、草根阶层身份的符码意义不复存在。阶层与空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碰撞出相斥与相融、矛盾与困惑,流浪与追寻的多种形态。
在性别与空间层面,如叙述“七姊妹道”的命名,有“香艳、神怪”之说,反映出自梳女习俗和纯粹女儿世界的梦想。也有“当时两性社会关系沉重而充满伤痛的反映”之说,体现了当时女子对男性夫权的激烈抗争和对女性自主权利的追求。但显然,作者对性别与空间的认识,关注度不及上述两层面。
新生代香港作家创造了小说的地图空间新意象,把城市的地图解读为一部自我扩充、修改、掩饰、推翻的小说.反恩其中的历史、文化和权力。这种空间叙事颠覆了小说传统,具有多维性、非连续性、交叉性特色,作品充溢着颠覆、批判、反讽力量。在反线性叙述上为文学创作开创了新的方向。其价值正如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探究分析监狱空间,叙述仪式化的权力空间变化的谱系史,具有开拓性。旧有的文学理论已经不能评判这种新的文学现象,新的理论范式注定要诞生。小说空间叙事的理论不仅能评判新的文学样式,用于研究已有文学现象也能发掘出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