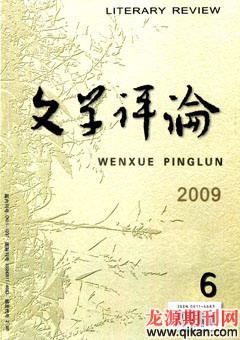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另类亲情”
王列耀
内容提要:尽管族群间的通婚也有许多成功与美满的范例,北美新移民文学似乎对其中的“另类爱情”更为关注。“另类爱情”拖曳出的是形形色色的“另类亲情”:充满疏离、惆怅甚至是暧昧,充满冷漠、敌意甚至是罪恶。作家不仅以悲凉的心态叙述华族“故事”,也以悲凉的心态叙述“异族”“故事”;不仅以悲悯的胸怀容纳“故事”中的华族人物,也以悲悯的胸怀容纳“故事”中的“异族”人物——新移民文学展现了不同于老辈华人文学、留学生文学的鲜明特色。
亲情与爱情一样,也是文学书写中的一个永恒母题。本文所关注的亲情母题,不是文学中一般意义上的父母与子女、兄弟姊妹之间的血缘之亲、骨肉之情,而是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之一翼的北美新移民文学中所特别关注,而且特别揪人心弦的“另类亲情”。“另类亲情”是指由于家庭重组,尤其是隔海重组形成的伦理意义上的亲情关系,如继父、继母,或者养父、养母与其继/养子女,及其无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牵扯与碰撞,当然,也包括着继父、继母自身在这个“另类亲情”空间中的种种牵扯与碰撞。
北美新移民文学所书写的“另类亲情”,大都建构在多族杂处、多种文化共在的特殊语境之中,因此,我们期望在解读“另类亲情”时,能够对北美新移民文学这种所谓“异族叙事”的特质加以特别的关注。
一、存在与荒诞:“生拉硬扯”的“另类爱情”
由于美国与加拿大都是移民社会,族群间的通婚已经较为寻常。尽管存在某些文化与生活习惯的差异,族群间的通婚也有许多成功与美满的范例。然而,北美新移民似乎对其中的“另类爱情”更为关注。因此,所谓“另类亲情”,大多都是起源于“生拉硬扯”的“另类爱情”——曾经有过,将来可能还有的“跨国婚姻”,一种主要不是源于爱情,而是因为某些需要或者欲望,而获得婚姻“名义”,又止于“名义”的婚姻。
在北美新移民文学中,这种“生拉硬扯”——“拉郎配”而成的婚姻,比比皆是。严歌苓《花儿与少年》、《红罗裙》、《约会》中的三位丈夫都是美籍华人,陈谦《覆水》中的丈夫老德,则是一个标准的美国白人。而且,他们都是年近古稀、富足的美国人。他们的妻子,都是隔海而来的比较贫困的年青女人。《约会》中的“丈夫”六十八岁,“开很大的房屋装修公司。人人都做这生意时他已做得上了路,人人都做失败时他就做成了‘托拉斯”。《红罗裙》中的“老东西”周先生七十二岁,妻子海云三十七岁。周先生住在一座“一五0银灰的城堡里”,“一五0是房价,不是街号。十年前它挂过一次出售牌,全街人都打电话问过它的价,回答是‘一百五十万。全街都安分了”。《花儿与少年》中的瀚夫瑞,已退休十年,曾是有名的律师,“一生恶狠狠的工作,恶狠狠的投资存钱”。他比妻子晚江大三十岁,“十年前娶她进大屋”,晚上看她的神情。如同不时点数钞票的守财奴般”。而陈谦《覆水》中的丈夫老德,则比妻子依群大三十岁,比依群的母亲树文还大三岁。
这种“生拉硬扯”到一起,且获得了“婚姻”名义的“另类爱情”。充斥着需要或者欲望,唯独没有爱情。表面上看,这些“丈夫”是新的“婚姻”、“爱情”的拥有者,“男子获得了对妇女的胜利,但是桂冠是由失败者宽容大量地给胜利者加上的。”而这里妇女的“宽容大量”实际上还是出于某种权衡利害的现实需求。
——海云经人介绍见面的“第二天他们便结了婚。”“海云不是为钱嫁的。海云多半是为儿子嫁的。”
——五娟对儿子晓峰说:“要不为了你的前途,我会牺牲我自个儿,嫁他这么个人?”晓峰不言语了,突然意识到母亲牺牲得壮烈。
——晚江“为了寻求‘幸福,一个女人离婚,再婚,来到大洋彼岸。但是她真的爱她原来的丈夫和孩子,于是,在十多年间,孩子一个一个来了,前夫也来了”。
——依群嫁给老德,一半是为到美国治病,一半是为兄妹、母亲移民美国。正像她母亲树文所说:“老德对你是有大恩的”,依群也常常提醒自己“一个最为关键的事实是老德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
我们读到在小说的叙述中,身处“另类爱情”的女人,都会不断地申言与辩白:“不是为钱嫁的”;可是,在她们心灵深处,都清楚一个事实:不论是为了儿子、家人、前夫,还是为了自己“治病”,归根结底——必须嫁个有钱,舍得为自己掏钱的丈夫。正是这根她们十分讳言的金钱绳索的“生拉硬扯”,初次谋面的老男少妇,迅速获得了“婚姻”的名义,也引发了种种荒诞与悲剧。依群不能忘记,他们的初夜,老德年迈到只能用手指去实现丈夫的权利。他“试出”依群还是“处女”,偶尔振奋,第二天,依群却发现,老德所卧之处竟有大片的遗尿。海云也不能忘记:与周先生见面的第二天,“在王府饭店开了房”,“关上灯,海云感到一个人过来了,浑身抚摸她。那手将海云上下摸了一遍,又一遍,像是验货,仔细且客气”。周先生比老德更加老迈,多年以后,直到海云“秀”着儿子健将打工买来的艳丽、性感的红罗裙,他才有了一次难得的振奋……,从描写中不难看出一方面是近乎“无能”的丈夫的“欣喜、紧张、侥幸和恐惧”;另一方面,是再婚妻子的极度无奈与。顺受”。这种“生拉硬扯”的“另类爱情”,包括其中最为敏感的“性”,说到底,还是一种21世纪北美“文明版”的金钱交易——在付出与获得中,双方都默认与维护着一种合乎“名义”、悖乎情感的交易。这种交易正是一些人的情感满足(包括性满足)乃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也依然是以女性被男性所奴役的方式而出现的。
二、冷漠、暧昧与罪恶:
“另类爱情”拖曳中的“另类亲情”
“另类爱情”拖曳出的是形形色色的“另类亲情”:充满疏离、惆怅甚至是暖昧,充满冷漠、敌意甚至是罪恶。在这里,妇女由于男子的统治和“继”的地位上的竞争,家庭形式享受不到实际的自由和相互尊重。
首先,继父与继子之间如同天敌,水火不容。
“晓峰来到这家里的第六个月,丈夫对五娟说:‘你儿子得出去。她知道这事已经过他多日的谋划,已铁定求饶耍赖都没用处”丈夫全然不顾晓峰如何“在空楼里孤零零害病”。在继父的逼迫下,在“异国的陌生,以及异族人的冷漠”中“晓峰仍是个孤儿”。——《约会》
周先生与继子健将近乎冤家对头:“凡是有健将的地方,一般是没有他的”,健将与继父的亲子偶有冲突,“周先生一拳擂在桌上:‘你嘴放干净点。不然我马上可以请你滚出去!”最终还是把健将赶到了五百里外的学校去寄宿。——《红罗裙》
《花儿与少年》中的继父子之间,走到了断指明志的绝路:九华用自己的血淋淋的断指宣告,从此离家出走、与继父恩断义绝。
其二,继父与继女之间充满危险,继父卑鄙无耻。
郁秀《美国旅店》中安妮的“美国继父”,是一个整天醉醺醺的无业游民,“对她极好,又亲又抱”。“她妈妈更好,跟了老美跑到美国,到了美国又跟别人跑了。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要,直接就丢给她的继父了。”这个“美国继父”正好乘机对小女孩安妮痛下毒手:“那衰老的身体所蕴藏着
的对青春的贪婪与仇恨,终于成了罪恶”。
张翎的《余震》中的继父王德清,公然打着“父亲”的旗号,碾过“亲情”伦理,亵渎小灯的心灵与身体:“爸,爸只是太寂寞了,你妈,很,很久,没有……”,“王德清脱光了小灯的衣服,将脸近近地贴了上去。小灯的身体鱼一样地闪着青白色的光,照见了王德清扭成了一团的五官。“那年小灯十三岁”。
其三,继母与继子之间,弥漫着暖昧气息。
北美新移民文学所书写的“另类亲情”,大都建构在多族杂处、多元文化共在的特殊的语境之中——现任丈夫多有混血的儿女。继予的年龄与继母相近,且“擅长”与继母“调情”,当年曹禺的名剧《雷雨》中“周萍与繁漪”式的危险“游戏”,便在“另类亲情”中一再上演。
晚江深爱儿子,“顺从”现在的丈夫,还与原来的丈夫保持着密切联系-却也不妨碍与继子路易保持暖昧之情:
“晚江发现路易眼睛的瞬间异样,……她感觉得到它们在瞬息间向她发射了什么,那种发射让晚江个人从内到外从心到身猛地膨胀了一下”。“无名分”不等于没事情;“无名分”之下,甜头是可以吃的,惬意是可以有的”。——《花儿与少年》
海云也深爱儿子、顺从丈夫,却与“一个粗大的金发妇人”生下的“一个这么优美的杂种”,“二十几的”“美国人”儿子卡罗暗中传情,甚至投怀送抱:
“对于她这三十七岁的继母,卡罗的存在原来是暗暗含着某种意义,“海云这三十七年没爱过男人,或者她爱的男人都不爱她。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卡罗这样往她眼里死找他。”
“I…Love…You!”他啼溜着鼻涕,口中发出喝粥般的声响。“海云一动不动,但浑身都是邀请”,“海云甚至没留意儿子的明显消瘦和病马般迟钝的眼神。”
痛苦中的儿子健将,“突然纵身,抄起地上碎作两半的瓷碗,向卡罗砍去,砍到了卡罗额上角,一个细红的月牙儿刹那间晕开,不一会,血从卡罗捂在伤处的手指缝溢出。——《红罗裙》
种种情境表明,小说中的女人或被迫或无奈或出于其他考虑,在“另类亲情”里实际上卷入一种危险而又荒诞的“爱情”游戏。新移民文学所书写的这些女人,过上的甚至是“危险的”三重“生活”,不仅陷于了“危险的天伦险境”,而且,也陷于危险的情感险境、舆论险境,甚至法律险境。这里自然就没有圣洁的道德可言,恩格斯早就说过“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姑且不论爱情、亲情的“天长地久”,仅仅以此类危险的游戏而言,不能不说作为“历史进步”的个体婚制的一个相对的退步,是文明社会细胞形态的“婚姻”中的毒瘤。
三、“险而不绝”的叙述:“郁闷”中的“诗意”
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两个家庭”、“危险的”三重情感“生活”,随时会遭遇“雷雨”。但是,在新移民文学中,多半却是一种“险而不绝”的叙述:“一切都在郁闷地腐烂”,“结局随时可能来临,读者时时屏息等待,但结局永远不会来临”。这不仅是因为北美“二十一世纪的‘雷雨”,不同于20世纪的中国《雷雨》,更因为叙事者置身于多族杂处、多元文化共在的特殊语境之中,在叙说“一种两性相隔的绝望”时,潜在着一种在“不可能中展示人性所具有的强烈张力”的艺术追求。
人们在谈论诗歌时,常会论及诗歌的意象。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优秀的小说,也会蕴含强烈的诗意,也有可能营造出令人难以忘怀的意象。
细读北美新移民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在那些“险而不绝”的叙述中,聪敏的作家有意营造了一些意蕴性与暗示性极强的“意象”——“电话”、“长跑”、“香气”。正是有了这些蕴含强烈诗意的“意象”,“郁闷”气息中总会有一线“生机”;小说中的人物,也得以不懈地穿行过重重“郁闷”与危机。
不论是“两个家庭”,还是“危险的”三重“生活”,不论是与“儿子”,还是与原来的丈夫“私通款曲”,都离不开电话。以特写方式反复出现的电话,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道具与暗示。
《花儿与少年》中的瀚夫瑞就像防盗、防火一样,防止晚江与儿子九华以及原来的丈夫洪敏见面与通话,包括旁听电话、以各种借口阻拦与跟踪。可是,晚江与九华、洪敏之间的电话从未中断,见面也从未中断。瀚夫瑞每次抢先接听,都是一些“老女人”找晚江;当着瀚夫瑞的面,晚江也会大谈黄油、白菜;瀚大瑞一转身,晚江与洪敏就像一对不曾分离的“小夫妻”,窃窃私语:她从“吃过早饭没有”中听出牵念,疼爱、宠惯,还有那种异常夫妻的温暖。那种从未离散过的寻常小两口,昨夜说了一枕头的话,一早闻到彼此呼吸的小两口。包括电话中蕴含的“两人间从未明确过的黑暗台谋:瀚夫瑞毕竟七十了,若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运气,将会等到那一天”。瀚夫瑞不懈地防范、监视,晚江、九华、洪敏却不断地变着法子在电话中“亲热”。其中的欺骗与被欺骗,欺骗与反欺骗,应合着“结局随时可能来临”,“结局永远不会来临”“主题”的反复与拉锯。
不论是“两个家庭”,还是“危险的”三重“生活”,不论是与“儿子”,还是与原来的丈夫“私通款曲”,跑步,尤其是长跑,是又一种重要的“道具”与暗示。严歌苓笔年迈的瀚夫瑞永远追不上晚江。晚江总是把瀚夫瑞甩得很远,她的儿子在前面等她,她的原任丈夫也在前面等她,晚江的生命在路上,晚江的期望也在路上。瀚夫瑞跑不过晚江,可是他拼着命追赶,实在不行,就开着车去追赶。这种跑与陪跑,监视与摆脱,跟踪与反跟踪,也正应台着“结局随时可能来临”,“结局永远不会来临”“主题”的反复与拉锯。
电话归电话,跑步归跑步,妻子对现任丈夫的“责任”总要维系。因而,在叙事中反复出现的“香气”,也具有了强烈的意蕴性与暗示性。回到起居室,九点了。瀚夫瑞从楼上下来,身上一股香气。只要他在上床前涂香水,晚江就知道下面该发生什么了。这种“发生”并不频繁,一两个月一次,因此她没有道理抗拒”。甚至到了晚江决定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的时刻——她写信向瀚夫瑞坦陈了一切;只是,“挂号信仍没有到”。“香气”依然具有强烈的意蕴性与暗示性:
九点半她又闻到瀚夫瑞身上香喷喷的。她觉得自己简直不可思议,居然开始刷牙、淋浴。她擦干身体,也轻抹一些香水。洪敏这会儿在家里了,趿着鞋,抽着烟,典型断肠人的样子。“香气”在这里被赋予了丰富的想象与寓意。弥漫在“香气”背后的是挣扎与压抑、暗示与顺从,付出与索取,这种凄惨的“诗意”,又一次地应合着“结局随时可能来临”,“结局永远不会来临”“主题”的反复与拉锯。
自然,“香气”还有另一种意蕴与暗示。在王瑞芸的《戈登医生》中,始终渲染着一种奇怪的“香气”:“我在凯西身上闻到过一种奇怪的香味,在戈登医生身上,我也闻到了同样的香味。”甚至,在戈登医生收养的中国幼女爱米的身上,也闻到了这种奇怪的“香味”。因此,“我”曾经怀疑戈登医生与仆人凯西,这个“像一头黑色的母猩猩一
样挡在门口”的“黑女人”甚至爱米,“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一个黄种人”,三者的关系是否暖昧。然而,这种令人狐疑的“香气”,在“暖昧”背后导向的是“郁闷”中的沁心,是“梅雨”中的一线“生机”。原来,这里隐藏着另外一种荒诞:戈登医生的中国太太去世了,痴心的戈登医生把她的尸体“偷”回家,用一种散发着特殊香味的药物“保全”太太的身体,并与养女爱米一起享受着团聚的甜蜜,凯西、戈登医生和爱米身上共有“香味”,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共谋”。面对着戈登对太太、养女“那股说不出的宠爱和呵护”,“我”这个被临时雇用的局外人,都不由得生出了些许的妒意,“忍不住抱起爱米,大声用中文对她说:‘爱米,你实在实在是个有福气的孩子,你是修了几世修来的?”
可见“香气”在这里也被赋予了丰富的想象与寓意。弥漫在“香气”背后的是猜疑与隐瞒、多变与痴心,这种怪异与凄惨的“香气”,冲击着扑面而来的肉欲的“香气”,从另一个角度暗示着。郁闷”中的亮色与“诗意”。
如果说,“险而不绝”的叙述具有某些“诗意性”,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些“史诗”的价值与特性的话,那么,“电话”、“长跑”、“香气”这些具有诗意性的“意象”,作为在文本中起到隐喻性和连缀性的艺术元素,值得咀嚼与留意。
四、“险而不绝”的背后:悲凉、悲愤与悲悯
“另类亲情”中的人物,都在“险而不绝”的处境中煎熬与苟活;北美新移民作家既无从改变这种仍在不断上演的悲剧,也无法将已经陷于“郁闷”中的“人物”拉出泥潭,因此,作家们只能将自己内心的同情与悲凉默默地投射在“郁闷”之中。
由于置身于中西文化交汇处,或者说置身于中西文化边缘处,作家所着力展现的是“生命”与“心灵”“移植”后的鲜明特色:既以悲凉的心态叙述“故事”,又以悲悯的胸怀容纳“故事”中的人物。
在作家笔下,“周先生”、“丈夫”、瀚夫瑞及其他小说中的许多丈夫,都是“另类亲情”中的压抑者、跟踪者。他们“实施暴力”、“压迫”妻子、拆散“亲情”,造成了“另类亲情”中新的离散,甚至是血淋淋的“断指”,导致出一幕幕悲剧。在叙述这样的“故事”时,小说渗透出无言的愤懑和难言的悲凉。但是,“周先生”、“老东西”、瀚夫瑞及其小说中的许多丈夫,也是受伤者、被压抑者。他们付出了金钱,付出了全部心血与期望;他们的心灵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而且一再被伤害。例如,陈谦《覆水》的老德曾经拯救了依萍,是依萍及家人的“恩人”。随着岁月流淌,依萍手术后身体逐渐康复,事业蒸蒸日上,老德却越来越衰弱,心灵也变得脆弱。这时的依萍,却将情感逐渐投向了另一个男人——艾伦。老德承受不了这个事实,终于抑郁而终。
可见,生活在北美21世纪“雷雨”中的丈夫们,并不都是“周朴园”。这样,作家一方面以悲凉的笔法,具体、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在“另类亲情”中的专横、霸道;另一方面,也以悲悯的胸怀对他们寄予了理解、宽容与同情。
海云、晚江、依群等及其小说中的许多继子,都是“另类亲情”中的被压抑者、被跟踪者;他们在“暴力”与“压迫”之下,忍气吞声、担惊受怕,还得柔顺迎合,“郁闷地腐烂”。在叙述这样的“故事”时,悲怆、凄切力透纸背。然而,海云、晚江、依群等及其小说中的许多继子,又是欺骗者、压抑者。妻子委身于丈夫,继子在经济上倚仗着继父;妻子却瞒骗丈夫,甚至过着“三重”的情感生活,继子视继父与“天敌”,甚至帮助亲父哄骗继父。他们也不是“繁漪”与“周萍”。这样,作家一方面以悲凉的笔法,具体、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在“另类亲情”中的委屈与无奈。另一方面,也以悲悯的胸怀对他们时有含泪的挪揄、讽刺。
如此看来,所谓“异族叙事”,是指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作家在“族群杂居”的语境中,对复杂、微妙的“杂居经验”的感受、想象与表述方式,以及他们利用文学方式,通过言说其它族群进而言说自我的一种方式与心态。不过,不同的华人作家群体,在“异族叙事”的言说方式与心态上也有所不同。
老作家黄运基在《异乡三部曲》、《旧金山激情岁月》等小说中,“异族叙事”的基调,是抗争与悲愤。余念祖与美国移民局甚至五角大楼的抗争,既悲壮又悲愤——“他的美国生活灰色而沉重:要反抗美国社会的压力,还要承受华社中不同政治壁垒的迫害,他铭记美国华人苦难的历史,极力抨击美国政府施于华人身上不公平的待遇”,“和美国女人的感情总是沉重并痛苦,他始终不能融人美国社会,”“‘他生活在美国,却更像是一个中国人。”而留学生文学“异族叙事”的基调,则是疏离与悲愤。如在白先勇《纽约客》系列的《芝加哥之死》中,吴汉魂(“吴汉魂”系“无汉魂”的谐音)的毕业之日,就是他的自尽之时。摩天大楼、芝加哥街道全是恶的梦魇与化身,白人妓女,不仅是堕落的象征,也是吴汉魂报复的对象。在《安乐乡》中,主流族群以潜在的方式饱含排斥与敌意:依萍社交失败,小女儿遭到嘲笑,安乐乡卫生室般的市容,刀削斧凿过的草地,死水一般的寂静,实验室般的厨房,处处都让人触目凉心。诚如陈瑞琳所言:“无论是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还是白先勇的《纽约客》、於梨华的《傅家的女儿们》,都是在面对陌生的新大陆的疏离隔膜,遥望故国,表达自己的那挥之不去的落寂孤独与血脉乡愁,以及对西方文明不能亲近又不能离弃的悲凉情感。”
新移民文学“异族叙事”的基调,出现了一种嬗变:由对立、疏离走向对话。“另类亲情”大都建构在多族杂处、多种文化共在的特殊语境之中,白人、黑人、黄种人、混血儿,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因此,在“异族叙事”的过程中,也显现出同样鲜明的特色:既以悲凉的心态叙述“异族”“故事”,又以悲悯的胸怀容纳。故事”中的“异族”人物。
王瑞芸的《戈登医生》与陈谦《覆水》等小说,都渗透着悲凉、充满着悲悯。戈登医生对逝去的中国妻子一往情深,痴心到社会不能容忍的程度,引发了舆论与公众的批评、围攻。小说通过“我”与舆论、公众,包括与自己丈夫的对立、冲突,显现出对世俗的不满,对有着“怪异之举”的戈登医生的包容与悲悯。
《覆水》中的老德,曾经是一个强者,是依萍及全家的“恩人”。当老德越来越衰弱,心灵受到打击,猝死在家中时,带给读者的是无限的惆怅与悲凉,是对老德的同情与悲悯。母亲树文,虽然没有回答依萍的询问:“你是不是一直爱着老德的?”而在“故事”中,依萍的姨妈曾经疯狂地与老德相爱,树文一直默默地照顾着“老德”,直到他不幸去世——因为他是一个值得爱护的男人。
在石小克的《美国公民》中,傅东民第一次被女人爱着——个美国女人伊莲娜,而且有着亲密的关系。然而,伊莲娜。伙同情报部门以及别有用心的人,出卖了傅东民——把他推上了法庭,有可能被终身监禁。但这并非是伊莲娜无耻,而是她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她要恪守她的职责——她是傅东民所在保密项目的“保安主任”。真正无耻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府官员,是与傅东民有着生死之交的朋友林山。作家以悲凉的心态叙说着这场巨大的阴谋,却以赞许的“语调”,叙述着伊莲娜的真诚——她坚持只说真话,即使有可能将恋人送进监狱;她坚决不说假话,即使面对“权贵”与金钱的利诱。
不仅以悲凉的心态叙述华族“故事”,也以悲凉的心态叙述“异族”“故事”;不仅以悲悯的胸怀容纳“故事”中的华族人物,也以悲悯的胸怀容纳“故事”中的“异族”人物——新移民文学正是这样展现了不同于老辈华人文学、留学生文学的鲜明特色。在这个意义上,严歌苓的《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多少有些寓言的味道:不同族群之间,可以由对话过渡到平等交往;互相隔膜、排斥的心灵,最终有可能在对话中互相靠拢。在小说中,作家对“名字”异乎寻常的关注,颇有意味。亚当在外表上是一个成功的美国男人,内心深处却是一个讨厌女性的同性恋者。叙述者我,是一个刚遭遗弃的华人女子,无论是文化上,经济地位上,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边缘人。亚当性取向由畸形到正常,显然受到了“我”的影响,而“我”也在亚当的影响下放下自己的种种精神重负。
从悲愤与对立、悲愤与疏离,嬗变为悲凉与悲悯,新移民文学作家在对“出生成长国与再成长国”双重的爱与痛中,呈示了自己逐渐成长的身影与心灵。这个过程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也许还很曲折、漫长,但是,新移民文学已经由此揭开了北美华文文学新的篇章,并且正在北美21世纪“雷雨”的阵痛中,锻造着自己充满诗意的生命与饱含新质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