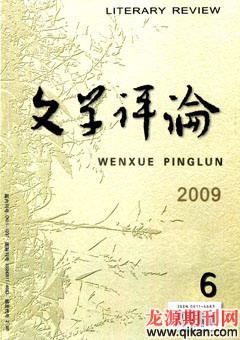中国古代诗论的美学品性及美学学理建构意义
张 晶
内容提要:中国美学学理建构是关系到美学发展的重要问题,仅凭日常生活作为美学建构的基本资源,仅凭后现代理论来说明当代审美现象,不足以解决美学学理的内部建构问题。美学的基本资源仍然是艺术,由对艺术的审美体验升华出学理命题,仍然是美学发展的主要途径。中国传统诗论具有进入当代美学格局的重要价值,其鲜明的审美体验属性和独特的审美抽象思维,都与美学有着天然的渊源。体验是审美活动最本质的状态,而中国古代诗论正是建立在丰富的品味与体验之上的理论形态。同时,其重要命题亦非仅停留在这个体验层面,而是高度审美升华而获致的理论成果,中国古代诗论的思维路径与理论形态,对于当今美学的发展会有更重要的意义。
一当代美学学理建构的资源向度
中国的美学学理应该如何建构?美学学科发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当然是不可能定于一尊的,但却是作为美学专业教师或学者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目前美学领域的情况可谓是纷然杂陈,各种理论争相登场,尤其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似乎已经成了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而其他的美学理论则隐然退后了。这就带来美学学理发展上的断裂,而使当代美学流于浮泛而缺少思辨的深度。美学是要发展的,传统美学理论确实很难阐释和解决当代的审美问题。但是要以五光十色的日常生活作为美学建构的基本资源,浮光掠影地用后现代文化和消费社会理论来说明审美现象,是不足以在内部解决美学学理的当代建设的。
我在这篇小文中将中国传统诗论作为当代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也许会引起很多同仁的晒笑,或以为这不过是“九斤老太”的心态,其实我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古代诗论本身,而是出自于对美学性质的理解。牵强之处也许难免,但却是一个特殊的视角。简而言之,美学的基本研究资源还应当是艺术,在/>天传媒艺术成为最具人气的艺术形态的时代,艺术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很多时候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也弄得漫漶不清,但由对艺术的审美经验升华出美学学理,仍然是美学发展的主要路径。从这种意义上来探寻古代诗论与当代美学的关系,就可以看到命题的真正价值所在。
致力于开发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试图激活古代文论的生命力,这是当代的古代文论或古代文学学者们多年来的突围之路,所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正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命题。我在此文中所表现出的初衷与思路,也许有意无意地与此有部分的重合。在这方面我坦诚地予以承认,因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争论,把问题提到了当代文艺学的课题之中,并使之大大向前进了一步,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创造“惊世骇俗”的理论的能力和野心,只是想在不断地趋近之中打通一些东西。这当然也是需要一点勇气和自信的。
这种企图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对文学与当代传媒的关系的研究、美学发展所亟须补足的要素等等。容当我用寥寥数语简略概括而不作展开,以便使同仁理解本文的提问意义。
我认为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虽然只是一种“家族相似”,但就其本质而言,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其根本之点在于,文学与艺术都是以形式的创造力和完整性来激发人们的审美经验的,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创作主体(诗人、作家或是画家、音乐家等等)都是以其艺术形式的独特创造为其价值依据的,再则是艺术形式的完整性,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艺术创作,必然是以其艺术形式的完整为其特征的,也就在这一点上,与日常生活相区别。再一点,从当下的文化研究学者的见解看来,似乎文学在电子传媒时代已经遭遇厄运,图像的泛溢使文学命运走向终结;而在我看来,当下的电子传媒并未使文学走向终结,文学恰恰是在与传媒艺术的姻合中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并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学样式。从美学学理的接续与发展而言,美学走到今天,在学理上产生了巨大的断裂,由社会学或文化学入主,在美学领域中大行其道的是视觉文化理论、消费文化理论、后现代文化理论等等,这些都为美学变革的社会因素做了令人信服的阐扬,但却未尝为美学学理自身提供多少有益的发展因素,或是使美学学理在新时代条件下向上提升。“日常生活审美化”之类的命题,是使美学走向泛化,但却无法使美学学理得到新的建构。那么,当代美学的学理建构究竟需要什么因素方可向上提升或开创进境?这个问题是有相当迫切的现实意义的,而非“一个针尖能站几个天使”之类的学院问题。我以为传统美学以其抽象与思辨建构起大厦,而当下的审美现实则是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视像为主要对象,审美主体很难对其进行“静观”,也就无从进行抽象与思辨的学理提炼。西方传统美学的逻辑建构,对于当下的审美现实更多的是无所措手足,而听任社会学和文化学来入主美学庭园。“日常生活审美化”之类的命题,把那些无首无尾、流沙无形的泛审美现象呈现给美学圣殿,却无法抽象为具有时代刻度的美学学理。当代美学仍然需要在学理层面进行延伸与突破,而其学术资源又将安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从古代文论研究的立场上来推进这个问题,但我以为,还可以从当代美学建设需要的立场出发来认识古代文论的价值所在。中国传统诗论,在古代文论中则是最具美学意义的,而且对于美学学理建构,可能会在思维方式等方面提供一些别开生面的建构资源。
二古代诗论的美学品性
单就中国古代诗论来说,究竟它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当代美学的资源?这个命题是否有着伪命题的危险?这里需要给出一个可以让人差强人意的答案。这就需要对中国古代诗论的美学品性加以抉发,并且指出其对于美学学理的裨补与建构价值。
应该看到,古代诗论本身并非美学理论,难以直接进入美学学理的构架之中。然而,中国古代诗论多数出自于对诗歌创作的品藻与体验之中,有着突出的审美体验性质。“体验”之于审美活动,是最为本质的状态,它是主体与客体的沟通,也是对主体与客体的超越。对于文学艺术创作与欣赏而言,体验是获得其中三昧的关键。西方思想家对于“体验”有颇为深刻的理解和阐发,从狄尔泰到伽达默尔,都系统论述过“体验”的意义。体验德文原作“Erlebenis,源于Erleben,Erleben本义为经验、经历、经受等,而狄尔泰的“Erlebenis一词却不同于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经验”,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源于人的全体生命深层的对人生事件的深切领悟。正如王一川教授所指出的:“因而对狄尔泰来说,体验特指生命体验,(英文常译作‘life---experience或‘experience of llife)相对于一般经验、认识来说,它必然是更为深刻的、热烈的、神秘的、活跃的。——因为在狄尔泰那里,‘体验首先是一种生命历程、过程、动作,其次才是内心形成物。我们试用中文词‘体验译它,可以保持其动、名词特性,也带有‘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亲身体验的含义。这样做可以同我们通常所谓‘经验概念区别开来。经验指一切心理形成物,如意识、认识、情感、感觉、印象等;‘体验则专指与艺术和审美相
关的更为深层的、更具活力的生命领悟、存在状态。”…王一川依据狄尔泰对“体验”的阐释,对体验和经验做了区别,这种区别是具有美学理论价值的,由此可以看出,体验与艺术、审美的创造历程是最为密切的。审美体验这样的概念,则进一步强化了体验在审美活动中的本质属性。我们可以认为有一般体验与审美体验的不同,但是最能体现“体验”的突出特征和本质的还应是审美体验。在这个方面,伽达默尔明确地揭示了审美体验的含义,他说:“审美体验不仅是一种与其他体验相并列的体验,而且代表了一般体验的本质类型。正如作为这种体验的艺术作品是一个自为的世界一样,作为体验的审美经历物也抛开了一切与现实的联系。艺术作品的规定性似乎就在于成为审美的体验,但这也就是说,艺术作品的力量使得体验者一下子摆脱了他的生命联系,同时使他返回到他的存在整体。在艺术的体验中存在着一种意义丰满(Bedeutungsfulle),这种意义丰满不只是属于这个特殊的内容或对象,而是更多地代表了生命的意义整体。一种审美体验总是包含着某个无限整体的经验。正是直接地表现了整体,这种体验的意义才成了一种无限的意义。一无疑地,艺术创作必须有审美体验构成其最为本质的东西,没有审美体验也就无从谈艺术创作。中国古代诗论的作者们,基本上都有创作经历,即便不以诗人闻名于世,但其实都是能诗的。譬如宋代的严羽,虽不以诗人闻达,但现存的作品也有200余首。诗论的运思方式,也多是从对具体诗作或诗句的品鉴而升华的审美判断或理论命题。审美体验的色彩是颇为鲜明的。
但是,古代诗论所凝结的一些重要命题,却并非停留在体验的层面上,而是有着高度抽象的品格。这种抽象,所体现出来的不是纯然的逻辑抽象方式,而是由审美抽象和逻辑抽象相融合的思维方式及性相。而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当今美学的发展,也许会有重要的操作意义的。如果以艺术作为美学的主要土壤,那么审美抽象就是美学学理的可能性途径。我以为审美抽象可以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蕴含,另一种则是美学理论的有关命题。中国古代诗论更多的是由审美抽象而升华的命题。
中国古代诗论,其出处颇为复杂。有的是出于思想家的经典之中,如《论语》等。有的是诗歌品鉴的专论,如:钟嵘《诗品》等;也有相当多的是诗话、词话等专门论诗的著作,如:《石林诗话》、《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也有的是诗人在作品中表达的诗歌美学价值观,如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等;还有一些以诗的形式来论诗之作,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等,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给他人写的序跋和书信中表述的对诗歌的评价。还有许多是通过对前人或他人的诗集作注的形式来抒写自己的诗歌观念的。其形式之丰富多样,是自不待言的,其理论价值当然也是大小不等的。但无论是对诗歌创作的“夫子自道”,还是对他人诗歌的品鉴评价,都是以具体的艺术创作为其生发基础的,其中的审美体验性质是其突出的特色。如专论五言诗的《诗品》,作者对诗的品鉴与评骘,都是建立在审美体验的基础之上的。如钟氏对陆机拟古之作的评价:“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对刘桢五言诗的评价:“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等等,都是从对其作品的具体感受中得到的审美体验。而如杜甫所道为诗体会:“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杨万里谈诗时所说:“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旬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望金华山》)分明是从诗人自己多年的创作实践的深刻体验中所得出来的。《诗话》中评论其他诗人之论,也大多是从对其诗作的审美体验出发,如欧阳修论及同时两位诗友梅尧臣和苏舜钦的不同风格时所云:“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对苏、梅二位诗人的精当辨析是建立在对其诗的深切体验之上的。再如清人赵翼论诗中奇警以李白为特出,其云:“诗家好作奇警语,必千锤百炼而后能成。如李长吉‘石破天惊逗秋雨,虽险而无意义,只觉无理取闹。至少陵之‘白摧朽骨龙虎死,黑人太阴雷雨垂,昌黎之‘巨刃磨天扬,乾坤摆磕破等句,实足惊心动魄,然全力搏兔之状,人皆见之。青莲则不然。如‘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如沙尘。‘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一日三风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皆奇警极矣,而以挥洒出之,全不见其锤炼之迹。”对以奇警风格著称的几位诗人进行辨析,都是由诗论家本人的审美体验为其依据的。
中国古代诗论中多有形象的、诗意化的表述,使人在审美化的感知中得到理论的启示,这种形象化、诗意化的表述,是出自于诗论家独特的审美体验,并以独特的意象表征其诗学趋向。在这个过程中,又贯穿着向美学高度的升华。《诗品中》引汤惠休评颜延之和谢灵运的风差异:“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以此诗意的描绘来形容颜谢的风貌,成为经典之论。宋人严羽评李杜诗:“李杜数公,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问耳。”这是针对具体诗人的创作所作的诗意描述。而还有很多是对于诗歌艺术规律、风格的概括,也是基于作者的审美体验的。如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有三境”说:“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王昌龄的论述在意境理论史上有其独特的意义,而其对“物境”、“情境”和“意境”的阐释,则是在本人的诗歌创作的审美体验中生发的。唐代皎然在其诗论名著《诗式》提出“取境”说:“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取境”在诗歌创作理论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皎然的“取境”之途,也是出于其对诗歌创作的审美体验的。在这方面,司空图的《诗品》可说是最为典型的,司空图将诗歌风格类型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这样二十四种,而对每种风格类型的阐述,则是用四言诗的形式来作的。如“自然”一品:“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钧。”“豪放”:“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
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这是《二十四诗品》对诗歌审美范畴的诗化描述。它们当然不是理论的诠解,而是用诗的语言,把此种风格的特征与境界写得惟妙惟肖。而作者对于诗歌风格类型的概括,是非常经典的美学范畴。
中国传统诗论还有很多是从对诗歌审美体验的诗意描述中直接升华出重要的诗歌美学命题,或者说是审美体验与命题概括的直接结合。此种例子甚多。如钟嵘《诗品》中所云:“若乃春风舂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于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戊,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远女有扬蛾人宠,再盼倾圄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诗可以群,可以怨,使贫贱易居,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这段话论述诗歌创作的抒情功能,前面关于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的种种指陈,都是作者对诗歌的审美体验,而在后面提升出诗能够“使贫贱易居,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的美学功能。宋代诗论家叶梦得则有:“诗语固忌用语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著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沧,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深深若无穿字,款款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叶梦得通过对杜甫“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等名句的细微品鉴,提出诗歌语言应“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的理论观点。
三古代诗论的审美抽象高度
在很多人的成见中,认为中国文论和美学思想,是偏于直观而缺少抽象的,长于具体感悟,弱于逻辑思辨,但从我看来,中国传统诗论在抽象思维都有着与西方文论不同的高度与特征。中国传统诗论(也包括在文学一般理论)中的抽象高度或许并不输于西方文论,而恰恰具有更为深刻的美学价值。如果说西方的文论与美学思想虽然有密切联系,但基本上又是分离的,中国传统诗论因其体验性质,而更多地将美学思想蕴含于中,在抽象思维上更显独特的概括力。陆机《文赋》论述诗文的创作思维过程:“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咙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段《文赋》之开篇,其实是概括了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过程,一方面文辞极美,体现了陆机作为一代文学巨匠的才情;另一方面,在对创作思维过程的论述上是高度概括的。刘勰论述诗人心灵与外物感兴关系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是以诗人感物,联类无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皎日彗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在深切美好的审美体验中所进行的理论概括,是抽象程度极高的。“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岁时变化带来物象特征,使诗人情感得到兴发,诗歌语言表现由此发生这样的诗歌创造感兴过程,概括得非常精要。“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则是对诗歌美学规律的高度抽象。皎然提出诗之“重意”:。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诗的“文外之旨”,即是“但见情性,不睹文字”。明代诗论家谢榛论诗歌创作云:“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北。凡登高致思,则神交古人,穷乎遐迩,系乎忧乐,此相因偶然,著形于绝迹,振响于无声也。夫情景有异同,模写有难易,诗有二要,莫切于斯者。观则同于外,感则异于内,当自用其力,使内外如一,出入此心而无间也。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这段话既有对诗歌创作的切实体验,又有关于情景关系及创作形态的理论提炼,其美学价值是相当高的。这在中国传统诗论中是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的。正因其出自于诗人或诗论家(诗论家本身大多也是诗人)对于诗艺的直接的、具体的审美体验,所以,这些论著内蕴着非常集中的美学价值;而中国传统诗论不走逻辑推论路径,是从对具体作品和创作形态的诗意描述中直接生发出诗学命题,这就使中国诗论所凝结出的命题,有着更鲜明的审美抽象的性质,同时又是与逻辑抽象相融合,它的最为突出的体现,还是以有充分的自明性和完整性的理论命题的形式产生和凸显。关于“审美抽象”。是笔者对于艺术领域的思维方式的一种概括,曾有专论加以阐述。我是将“审美抽象”作为审美领域的思维品格认识的,在《论审美抽象》一文中,我这样论及:“在我看来,审美过程中是不可能没有抽象的思维方式的,它不同于逻辑思维的抽象,而是一种有着特殊概括与提升路径、并使审美活动获得意义的基本思维方式。为了与逻辑思维的抽象相区别,我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审美抽象”。我还将审美抽象和逻辑抽象作了区别:“审美抽象指审美主体对客体进行直觉观照时所作的从个案形象到普遍价值的概括与提升。审美抽象与逻辑抽象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它们都是从具体事物上升到普遍的意义,但逻辑思维的抽象以语言概念为工具,通过舍弃对象的偶然的、感性的、枝节的因素,以概念的形式抽象出对象主要的、必然的、一般的属性和关系,审美抽象则通过知觉的途径,以感性直观的方式使对象中的普遍意义呈现出来,在艺术创作领域表现为符号的形式。”我在这里所侧重认识的还是在艺术创作的范围,而在理论的领域,我也可以认为,中国美学的范畴与命题,在相当多的场合也是由审美抽象而得来的,但其最后的产物,则是理论凝结的形态。诗论尤其是如此。易言之,由审美抽象而获理论命题,这是中国传统诗论的一个基本的致思路径。上面所引的这些例证,大都是这种情形。
由审美抽象而获致理论命题,往往有着自明性和完整性的特点。所谓自明性,指无须进一步论证、解释,就可以使人明确理解命题的含义。所谓完整性,是指在中国的诗学系统中得以凸显和经典化的命题,本身就是完整自足的,甚至在语法上都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而无须后缀、补充和演绎。自明性和完整性,只是两个角度的说明,其实在形态上是一致的。如:王弼的“得意忘言”、“立象尽意”,刘勰提出的“神与物游”、“感物吟志”、“以少总多”,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苏轼的“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绚烂至极归于平淡”,李仲蒙的“触物以起情谓之兴”,叶梦得的“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严羽提出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国维的“有境界自成高格”
等等,都有相对完整的语法结构,并在中国诗学系统中形成了经典性的命题。这其实是与中国诗论由审美抽象而获致理论命题的思维路径密切相关的。
古代诗论在中国美学的格局中。有着首当其冲的重要地位,有着非常独特的自身美感。很多诗论话语,就是用诗一般的辞采来表述作者的诗歌创作和欣赏中的美学观念,因其是来自于作者本人的深切审美体验,又加之作者的卓越才情,形成了诗论史上的一些经典篇章或自成一体的片断。这些诗论,有着与中国诗歌内在的相通性和一致性,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诗论本身就发散着精光闪烁的魅力。其中所升华出的理论命题,则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或许可以说,中国传统诗论有着鲜明浓郁的审美属性,与美学思想有着天然不可分割的渊源。与西方诗论相比,这个特征恐怕是不言而喻的。在语言形式上,很多诗论话语有着鲜明的韵律感和节奏感,其内容凝炼而思想明晰,之所以能成为传世经典,是与这种语言美感直接相关的。如《今文尚书·尧典》中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作为中国诗学发端的话,不仅有着“诗言志,歌永言”这样的经典命题,而且有着光英朗练的节奏感和诗性美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季札论“颂”:“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苏轼论诗云:“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叶燮谈诗之“胸襟”云:“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其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情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物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其有胸襟以为基。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如钻燧之火,无处不发;如肥土沃壤,时雨一过,夭矫百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无不具足。”等等。这些诗论篇章,语言、声韵和气势,都具有浓郁的美感,本身就可以说是美的文本,而同时又有颇高的诗学理论价值。它们不是纯然抽象的逻辑推理,不是凝固不变的理论教条,而是有着生香活色的美学升华。
当代美学的学理建设,不能割断与传统美学之间的联系,而应该是在以往的美学理论大厦的基座上的接续。从当代的审美经验来看,原有美学理论的很多观念或理论,都难以解释当下的审美现实,美学自身好像难乎为继,借助社会学、文化学的理论方法和现成概念,来指陈现在的审美现实,成为美学界的普遍现象。这大大拓展了美学的疆域,也从生成机制上阐释了当下的审美事实。但这并不能取代美学理论自身的生长。仅仅靠“日常生活审美化”这类的美学热点,是难以真正推进美学理论的提升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表征了古代文论研究进入当代格局的价值诉求,但还是给人以一厢情愿之嫌!美学的学理发展,换个角度来看,思维方式的创新是突破的可能性所在。如果站在中国的美学话语立场,传统诗论的思维路径和理论形态,就是很值得反思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