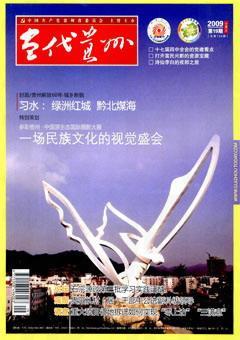三门塘小忆
潘年英
三门塘,其实就是一个上承远古,下接当代,同时广纳中西文明的一个文化的桥头堡。既是开放的、时尚的、流行的。同时也是保守的、传统的、民族的和地方的。
三门塘这个位于清水江畔,一个靠木材的航运发展起来,最后又由于陆路交通的兴起而衰落的侗族村寨,多年来我一直被其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深深震撼,但总是没有信心为它写下一些文字。
说起来,我最早见识三门塘,是在1999年的天柱县金山笔会上,而那一次笔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为着向外界推介三门塘。因为在此之前,三门塘一直默默无闻,并不为外界所知。
那一次会议省内外的作家、艺术家云集在天柱,连一向深居简出的贵州省著名作家何士光先生也出席了。
那一次,我在三门塘看到了久违的“红头绳”——天柱侗族姑娘传统的头饰。这种头饰我在小时候是经常见到的,这一文化传统大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退出舞台并逐渐销声匿迹,但在三门塘,却有着最后的保存。
不能说三门塘是偏僻而闭塞的。事实上,由于三门塘本身就是清水江上的一个重要码头,是早年北部侗族地区最著名的木材集散地之一,所以这里自古以来恰恰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荟萃各种先进文化的地方——村中保存至今的那些古老建筑和各种文化符号:不用说那造型别致的王家和刘家祠堂,也不用說那遍布村中的各种青石板,更不必说村中随处可见的突出于各栋木楼之间的封火墙……就是村中那一座卓然独异的三圣宫,也会让我们大为惊诧。这座修建于明代的古老建筑,完全结合了当地侗族传统木楼和汉族徽派建筑的特点,使我们看到了当年文化交流的历史明印。
而在三门塘的全部文化古迹中,最让人感到印象深刻的大约莫过于刘家祠堂大门上方的那由44个字母组成的一副对联了,那是一组拉丁字母,至于究竟是什么意思,至今仍无人破解。我们看到,该村的整个家祠建筑风格本身都是中西结合式的,门窗多为半圆型,有西式建筑风范,但四合的天井,以及祠堂内部的环廊,却又全然秉承汉侗传统——毫无疑问,三门塘,在当年,其实就是一个上承远古,下接当代,同时广纳中西文明的一个文化的桥头堡。既是开放的、时尚的、流行的,同时也是保守的、传统的、民族的和地方的。
每次我都在想,当年敢于在这门方上用西洋文字写对联的人究竟是怎么考虑的呢?其又当承受着族人怎样的非议和指责呢?
我们今天自然到处都在提倡保护原生态了,而且作为一种时髦的理论和观念,似乎也早已深入人心,连最基层的老百姓也懂得了传统的重要和宝贵,因此一说要搞现代化建设就会遭到许多人尤其是某些所谓专家学者们的非议和诟病。中国人凡事总喜欢一分为二,非此即彼。但其实,许多时候,事物却往往是可以一分为三的。
最近的一次去三门塘,是2007年5月,我陪同《潇湘晨报》的几位记者前往。村民热情招呼我们进村,并向我们热情介绍村中各种令他们自豪和骄傲的文物古迹和民族风情。
“为什么叫三门塘?”第一次去三门塘,我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村中最早为严、谢、王三大姓由湖南迁入,故而得名;另一说是原来村中有中、西、南三个寨门,故得此称。”当地人答复说。
“现有多少户?多少人?”我又问。
“300多户,1500余人,都是侗族。”
“都还会讲侗话不?”
“老的都会,年轻的,会的不多了。”
这样的状况,当然令人忧虑。但是,当歌声从寨中飘出来,还是几乎被遗忘了的传统侗歌,悠悠扬扬地回荡在河谷的两岸,这又使人感觉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