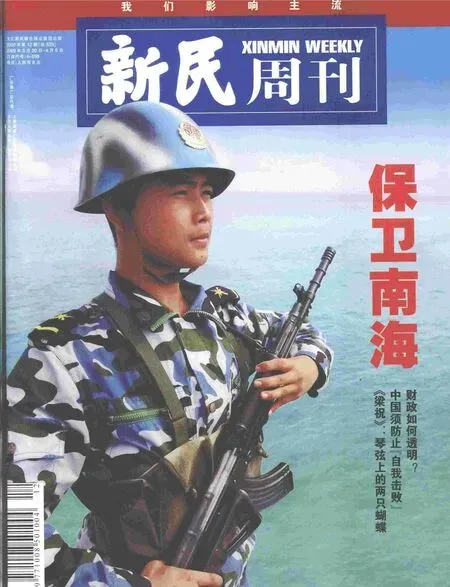相逢一笑泯恩仇
王悦阳

“前两天我还给陈钢打了电话,我说我们仍然像五十年前一样,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五十年多不简单呀……他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这样多好!”
五十年前首演的盛况仿佛近在眼前,最后一声和弦在空气中散发的回响若隐若现,“当时,台下掌声不像现在又是叫唤,又是跺脚。”何占豪回忆道,“台下的观众就是默默地鼓掌,这是我最难忘的第一次喝彩,真叫不快不慢,经久不息。”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诚心聆听音乐者都应该感悟得到,这种纯粹的理想化的宣誓才理应是《梁祝》最原始的主旨,而《梁祝》也绝非是让人为名利趋之若鹜的小道具。
如今,《梁祝》已然成为中国的一个符号。《梁祝》谱写了太多奇迹,它见证了“业余”作曲家所缔造的辉煌。可是,《梁祝》毕竟是音乐而非产品,这种符号化的放大,无形中让《梁祝》本身的音乐性渐渐弱化。一晃五十年而过,从昔日的共谱辉煌到今日的恩怨情仇、是是非非,《梁祝》这部国内被称为“民族的交响音乐”,而在国际上更是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实在承载了太多音乐之外的纷纷扰扰。让人不禁感叹:五十年后的《梁祝》太需要“非诚勿扰”了!
如今,何占豪回想起曾经走过的漫漫长路,那些世俗瓜葛形同渺茫沧海中的一抹浮云,“当年我们这一代青年,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志气——要把中国的交响乐推向世界,要将中国的民族音乐推向新的高峰。《梁祝》来得多不容易!其中所包含着不是我一个人的汗与泪,孟波院长、已故的刘品教授,还有丁芷诺、俞丽拿等这些小提琴民族化试验小组成员,包括陈钢和我的名字,都应该镌刻在《梁祝》的里程碑上。民族化并不是简单化,《梁祝》能有今天的成就已足以让我感到欣慰,想到这一点,还有什么不平衡的呢?难道我们不应该高高兴兴地庆贺《梁祝》五十年?”
让老百姓听懂小提琴
半个多世纪前,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班的一场入学考试,引得全国各地的音乐才子纷至沓来,经过几轮残酷而又激烈的竞争角逐,何占豪这个从乡下来沪,十六岁才看到小提琴,十七岁才开始学琴的“另类考生”,凭借他出众的才华脱颖而出。
出乎意料地坐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课堂,让何占豪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国外的优秀作品,可是,这些课堂上学来的优美旋律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听,下乡进行慰问演出时老乡们也不爱听,认为是西方人故作优雅的“锯木声”,这让何占豪深感困惑。
在當时的音乐学院支部书记、长笛教师刘品先生的启发与引导下,何占豪和丁芷诺、俞丽拿、张欣等六位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这群年轻人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劲头,平日里除了要完成自己的功课作业,还要花很多精力去搞业余创作,同时又得在民间音乐的学习方面花去不少时间——白天时间不够用,就在深夜“挑灯夜战”;瞌睡了,就打上一桶自来水冲一下脑袋……不久,何占豪就根据他熟悉的越剧素材创作了一首被他戏称为《小梁祝》的《梁祝四重奏》。

著名越剧琴师贺仁忠曾提出:小提琴是西洋先进乐器,戏曲中如若使用得当,可以使乐曲更有表现力。不仅如此,他还用《二泉映月》作教材教何占豪各种民族风格的演奏手法。《小梁祝》的创作源泉正是融入了这种风格性的演奏手法,在之后的下乡演出时,老百姓终于听懂了小提琴的美妙旋律。
试验小组因此在音乐学院也小有了名气,何占豪他们“振兴民族音乐,小提琴民俗化”的理想也逐渐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来“上音”视察时,对实验小组的创举大加美誉——“小提琴民族化方向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请大家再接再厉”。在大礼堂的后台,孟波马上将这席话传达给了何占豪,更使得这群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使中国的小提琴让老百姓喜欢。
适逢国庆10周年大庆,当时闻名于世的十大小提琴协奏曲中又唯独少了中国的一席之地,上级领导便对实验小组布置了更宏伟的要求:“你们这个小组不能小打小闹地搞,要勇攀国际高峰,要写出一个大的协奏曲。”大跃进的思潮让这群抱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美好理想,在还没有奠定理论基础便自诩为“小提琴民族学派”的年轻人,凭着一腔热血就豪情万丈地接下了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下乡去往温州前线采风的船上,一行人久久不能入眠,在甲板上开会商定创作题材。“娘子军”们很积极,一番热烈的讨论后,马上就有了两个方案:第一是“大炼钢铁”;第二是“女民兵”;何占豪随即又根据领导曾经的指示,补充了最后一个方案,提议用越剧风格为《小梁祝》写个大的协奏曲。
试想,如若没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超英赶美”的理想,甚至是接近“堂吉诃德”式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怎会有如今如此完美的《梁祝》呢?“毛主席提倡‘洋为中用,西为中用,说我们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政治服务,为大炼钢服务,错了吗?没错!大跃进是我们的志气,中国人赶超世界人民的一股志气,不能全部否定。我拉小提琴是洋的,但我们要为中用,《梁祝》是谁出的题材?是农民伯伯,本身就是下里巴人的。我写《梁祝》就是要响应为工农兵服务,我何占豪是无心插柳,但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五十年来阳春白雪的《梁祝》的经久不衰,是时代在有心栽花。”正如何占豪的豪情壮语一般,寄托《梁祝》那个关于“托梦蝴蝶”奇妙幻想的不正是大跃进时代年轻人骨子里泛滥的理想吗?
然而,《梁祝》的创作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之前经历了《小梁祝》、《二泉映月》的创作,肚子里东西都被搜刮尽了,真正开始创作《梁祝》的时候,何占豪却再也写不出来了,一种“我是业余的”的惶恐袭来,不禁打起了退堂鼓,不愿意接下创作的任务。这下可急坏了刘品,他把何占豪喊去谈话,而何却仍旧执拗着不肯写、不愿写、不想写。
在这些日子里,刘品为了做何占豪的思想工作,便与他朝夕相处,甚至连睡都睡在了一起,依着枕头共话音乐。一天晚上,何占豪给刘唱越剧,刘连连赞叹唱得好听,还鼓励着何占豪道,“你不是认为那个是越剧,不是小提琴协奏曲么?难道巴赫他们的音乐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脑子里生来就有的?他们也是从民间音乐中汲取来的。”就这席话顿时让何占豪打开了思路,从而坚定了民族音乐可以化为小提琴音乐的理念,思想上也完成了从“要我写”到“我要写”的转变。
那年的温州正是橘子丰收的大好年头,阵阵芳香随着婉转秋风将何占豪从美梦中催醒,奔波于上海温州两地的“钦差大臣”刘品早不知上哪儿去了。睡眼惺忪的他瞧见床头的书桌上摆放着一盘橘子和一个橙子,下面压着一张字条,上面用钢笔写着:“何占豪同学,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为小提琴的民族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组织上相信你,你一定能够为我们民族化事业做更多的贡献。”
遥想当年在温州那一幕,何占豪还是忍不住淌下了激动的泪水:“当时我只是个小小学生,但是从领导到支部到老师都这么重视,我很感动。”

《梁祝》情迷民族化
何占豪克服了心魔,《梁祝》的创作工作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创作组实行分工的方案——何占豪与丁芷诺这对曾经合作过《二泉映月》等一批优秀的小曲子的老搭档,业已磨合出了默契,因此《梁祝》最初的创作工作正是由何占豪与丁芷诺进行的。
然而,刘品还是有些心存疑虑,便向何占豪提议:这么大的曲子,以前都没人写过,单靠小提琴专业来完成恐怕有些困难,应该找个真正学作曲的。刘品想到了陈钢,当时,陈钢是丁善德院长的学生,如能约他共同参与,《梁祝》的推广不但能得到丁院长的一臂之力,而何占豪他们也可以获得去丁院长门下学习的机会,想到这个层面,何占豪也欣然同意了刘品的建议,立即代表实验小组找到了之前并不认识的陈钢,向他发出了邀请。可是,陈钢却婉拒了何的邀请,一方面陈钢那时正在忙着创作毕业作业;另一方面,相较并非“科班出生”的何占豪等人,陈钢本身骨子里的傲气也使他不愿和并“不专业”的实验小组合作。

得不到陈钢的帮助,何占豪同丁芷诺也只能“自力更生”了,温州采风的一个月里,两人对乐曲构思逐步达成共识。在创作主题之前,刘品先生曾很慎重地向他指出:《小梁祝》的爱情主题虽然有,但缺乏深度。也正是有了刘先生的提醒才促使了何占豪能够重新回到越剧中寻找深情的素材。
于是,何占豪沉浸在了属于他的音乐海洋之中,苦思冥想,连梦境都注满了抑扬顿挫的旋律,很快满卷的音符跃然纸上。根据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唱腔中《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那声甜美叫唤“妹妹啊”提炼的《梁祝》的主题也油然而生,而活泼的小快板“三载同窗”业已经初具雏形,之后,丁芷诺更对主题旋律作了初步的配器。
1959年2月寒假刚过,丁善德说服了陈钢加入《梁祝》的创作队伍,消息不胫而走,为此,顾全大局的丁芷诺悄然退出了创作队伍,想起当年丁出走的情景,何占豪禁不住黯然神伤,后悔不已,“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悔,当初我为什么不提出留住丁芷诺,如果三个一起合作,就更能体现这个作品是整个小组的集体劳动成果,或许现在也可以少了许多是是非非。可以肯定,丁芷诺身上,正有着当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及‘吃苦在前,荣誉在后的可贵品质,令我铭记终身!”
陈钢的父亲是著名作曲家陈歌辛先生,当何占豪还在浙江杭州越剧团工作时,就曾得到过陈歌辛热情的辅导,这也拉近了两个陌生年轻人间的关系,因此每次何占豪到他家去合作《梁祝》都得到了热忱的关照,两人之间的合作很快进入了“流水作业线”——以小提琴为主的段落由何占豪先写旋律,用小提琴演奏给陈钢听,两人再互相商定,当场修改,而其余部分则由陈钢用钢琴创作,弹奏给何听,经过不断修改直到两人都满意为止,再由陈钢配器,两人的智慧才情不断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取长补短、珠联璧合,无数个无休的日夜融化在《梁祝》的每一个音符中。然而,何占豪却不无谦虚地表示,“其实说得确切一些,当时我们两个还是尚未全面掌握作曲知识的青年学生,根本谈不上是作曲家。”
用乐章奏鸣曲式的结构来写《梁祝》是陈钢首先提出来的,虽然与原先情节性的构思存在矛盾,但经过两人反复思索,终于将两种思维统一在了一起:充分运用奏鸣曲式中对比、展开、再现等原则使《梁祝》符合了音乐上的逻辑,又尽可能适应老百姓的思维习惯。在《梁祝》的布局结构上也保留了“草桥结拜”、“三载同窗”等以内容命名的方式,这本身就将 《梁祝》烙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正如曲式权威钱仁康教授所言,《梁祝》的确已经“不太像”典型的西欧奏鸣曲式。
当初,孟波促成了“何陈”的联手,在《梁祝》整个创作过程中,孟更是倾注全力。听了最初再现部表现蝴蝶翩翩起舞的那段旋律后,他感觉在感情色彩上还不够鲜明,于是提出要重组这个旋律。为此,何占豪大伤脑筋。突然有一天,何占豪想起当年苏昆演出的《游园惊梦》中“万年欢”曲牌那段旋律极为优美,大可借鉴,于是跑遍了散落在上海街道各处的新华书店,终于在一本辞书中找到了那段曲子,于是立即提笔将商调式的昆曲音调和徵调式的越剧音乐“移花接木”,写成了如今那阕让人只闻其声便如临境的“蝶恋蜂飞”之章……
1959年5月27日,《梁祝》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参加上海市音乐舞蹈会演的节目,正式首演。
“我说不出自己当时是什么心情,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任务总算完成了。自从实验小组成立以来,我感到压力太大了,深怕辜负领导和同学们的期望;观众的掌声,送给我的是一身轻松……”何占豪意犹未尽地谈着首演时的感受,无限感慨发自肺腑,“回过头想想,我和陈钢只是穿着中山装的学生,真是两个学生,纯正的学生。《梁祝》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一个‘纯字,在一个‘纯的年代里,两个很‘纯的青年写了一个很‘纯的作品。”
何占豪的信箱塞满了来自教师、大学生、工人等各阶层群众写来的信,“他们信上会这样说:我是音盲,本来对音乐一窍不通,《梁祝》让我听懂了,感谢你们……有的还告诉我,听到‘楼台会时,他们忍不住边听边哭。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很高兴,因为老百姓听懂《梁祝》、喜欢音乐不正是我们实验小组最大的心愿吗?”那些信件至今仍是何占豪最宝贵的珍藏。
化蝶五十年
《梁祝》留给何占豪无数荣誉,同样带来了劫世灾难。伴随着“文革”的爆发,《梁祝》被打成了“封、资、修”的典型,文艺“大毒草”,被迫遭到了禁演,何占豪也被打成了“文艺黑线”。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何占豪与《梁祝》同甘共苦,共同沉浮,在他最困难的、最迷茫的时候,给他最大安慰的却依然是《梁祝》。
“文革”结束,《梁祝》仿佛那只舞动在电波中的斑斓蝴蝶,飘然而至。
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随之而来的是“物质”与“利益”欲求的膨胀,“名利”二字忽然变得微妙了起来。一本名为《黑色的浪漫曲》的小说,大篇幅地将《梁祝》协奏曲的创作灵感与陈钢的初恋紧密相连,而此书的作者正是陈钢本人。随后,1992年二胡改编版的协奏曲《梁祝》在美国卡内基上演,节目单上却没有出现何占豪的名字。《世界日报》的推波助澜更造成了两位作曲家首次在海外报纸上的冲突。也因此将两人之间的口诛笔伐推上了又一个高潮。
十年后,陈钢又以个人名義用《梁祝》去申报蜚声中外的美国斯卡莫大奖,这是一项个人荣誉奖,令何占豪愤慨不已,“如果陈钢在四十八年前和我合作时,对越剧一窍不通,我还能理解,时至今日,不仅不懂,还要装成内行的样子,以作者的身份,多次到中央电视台去误导听众,这就不应该了,为了个人成就而抹煞别人集体辛勤耕耘得来的成果就更不应该了。”
事态愈演愈烈。不久之后,在一场名为“上音优秀交响乐作品”的音乐会上,当主持人在介绍《梁祝》时,引用了陈钢在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中所说过的一席话,将《梁祝》的创作与他的恋爱故事相联系,顿时使何占豪感到非常不满。坐在二楼前排的他愤然地站起,在音乐会现场激动地喊道:“这是虚构的,陈钢的爱情与《梁祝》无关,……我把旋律都写好了,他才加入的……”当主持人表示,这是一个历史话题,可以展开专题研究时,何占豪继续喊道:“这根本不需要研究,当事人都还健在,我们可以当面对质。”最终,在现场观众一片“我们要看演出”的呼声中,演出终于得以继续……昔日因《梁祝》结缘的好友如今几乎成了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各奔东西,当年《梁祝》的演奏者俞丽拿情不自禁地用略带感伤的语调感慨道:“因为《梁祝》,老何和老陈是从过去吵到现在,从国内吵到国外,真不知道该怎么劝啊。”
然而,就在2007年的末尾,事情出现了转机。由于小提琴家潘寅林的从中斡旋,陈钢竟在何占豪亲自指挥乐队演奏《梁祝》完毕之后,上台祝贺,二人在台上握手示好!昔日的好友尽管并不一定就此彻底放下成见,但却为《梁祝》的五十华诞写下了最绚烂的序章。2008年春天,两人又再度相聚于“俞丽拿交响音乐会”,共同为当年的首演者献花,并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引起台下掌声不断……对于这位相交半世纪的老同学、老朋友,何占豪从不否认他为《梁祝》成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认为,陈钢在《梁祝》的构思上面确实很有作用,他把我们的民族乐段很好地同西方音乐相结合,符合旋律发展规律,因此使得整个布局有了新的突破,新的面貌。比如小提琴和大提琴对拉那一段,虽然不是他写的,但是对我的旋律发展起到了启发作用。现在想来,我和陈钢之间的‘蜜月怎么就不能长过五十年呢?前两天我还给陈钢打了电话,我说我们仍然像五十年前一样,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五十年多不简单呀……他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这样多好!”
五十年《梁祝》重的是“含情脉脉”、“一往情深”。许多人或许一辈子都说不上《梁祝》为何人所作,却能永远铭记住玲珑剔透的旋律,快乐时哼唱助兴,悲伤时凭吊情思……或许,只有一双自由的蝴蝶比翼双飞,重新谱写钱塘江畔的浪漫,才能唤起更多人心中的美妙回忆。若得如此,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