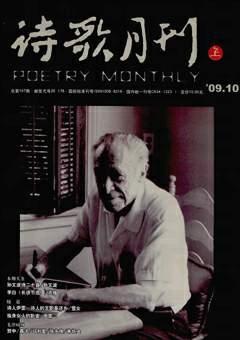章闻哲访谈:以自己的姿势崛起
阿 翔 章闻哲
阿翔:闻哲你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女诗人,我已经注意到了你,希望了解一下你写作的历程。
章闻哲:谢谢阿翔!其实,我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很多人写的诗在我之上,历史的,和当下的,这其实是每个写诗人的现实,你没有理由膨胀,只能不断学习,去获得进步。我可能只是偶然写出一首大家所认为的好诗,但是这首诗在别人眼里或许是博尔赫斯的“第三只老虎”,或者赫拉尔多·迪戈的“闪电”,对我自己来说却还远远不是,借用博尔赫斯诗中的一句话,我一直在努力寻找“那不在我诗中的,另一只老虎。”却至今未能找到。大多数时候,我都在写劣质诗。这一点很多人都表示赞同,当然,矫情地补充一句:缪斯也许并不这么认为。
我的写作历程其实很短, 2005年开始触网、写诗、写随笔,陆续有作品发表于县市级报刊杂志。该年秋末,经我在央视工作的亲友介绍,到本市(诸暨)文联旗下的一个文学杂志社当编辑,我一直处在文学的边缘,一直未真正动笔搞创作,如果说05年前的经历跟我的写作有何种关联的话,那就是我一直很自信,相信我的体内藏有一种天生的驾驭文字的力量,一旦我开始写作,我就必然能写好。在我的诗途上,我非常感谢《诗歌月刊》,在2007年民间诗刊专辑中就用了我的《绿色父亲》一诗,我想这与《九月诗刊》的力荐是分不开的,我感谢所有给我过这样提示的刊物,如《诗选刊》、《绿风诗刊》、《诗林》、《女子诗报》、《黄河诗报》、《大象诗志》、《新大陆》诗刊、《诗参考》等等。我对写作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但是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它,我会活得不太开心,但我也经常对它倦怠,或者说是创作的惰性。关于我的写作大致就是这样。
阿翔:阅读你的作品,在你的诗歌中有一种罕见的异质:开阔,自然而且敞亮。比如《绿色父亲》《你将有一只最美的耳朵》《北京之铜》等,这些作品充满个性甚至对当前的汉语写作有一种冲击力。记得傅元峰对你的《绿色父亲》评语是:“它不向情感的任何一种庸俗类型归属,自始至终用语言维护了造化的神奇。季节颂的审美革命就这样发生了,它不同于人生感受和诗歌存留中的任何季节,不同于任何自然歌吟。它不仅仅是新奇,也同时是对沦落的审美图景的果断刷新”。我觉得你对传统的突破和颠覆非常令人惊讶,有出奇制胜的效果。
章闻哲:其实这与我的阅读习惯有关,一首诗我常常只读前面几句,就认为大致能判断这是一首好诗还是坏诗,如果我感觉不好,我就停止阅读;如果感觉很好,我会飞快地扫过整首诗,而不会像很多人通常做的那样,一遍一遍或逐字逐句地去阅读,一首好诗通常会在我的“扫视”下撞击出闪电和火花,而其中的词语和意象却从来不会很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但我却已经遇见了这首诗的灵魂,这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可理解,但我就是这样,我偶尔会攫取他人诗中的灵魂移栽到我的诗中,但你不太可能在我的诗中找到与别人相同的词语组合,或相同的语境,这一点我敢肯定。我总是走自己的独木桥,但这样一来,我的诗可能不被很多人所接受,而且因为杜绝了经验,在技术上造成欠缺,导致诗歌有时显得很笨拙,这也是我诗歌中常常存在的问题。我在写的过程中并未意识到要颠覆什么,我只是在写我所认为的诗歌;傅元峰教授对《绿色父亲》授之以“刷新”之语,你又在这里再次提到“颠覆”,这既是对我诗歌形式的最大肯定,也给了我写诗的理由。但我探寻我的这种“颠覆”的根源也许只是得益于像美国诗人罗伯特?罗威尔所说的那样“我没有模仿别人的能力”。
阿翔:呵呵,你的诗歌让别人有一种无法模仿的气质。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或者说你对你的诗歌的期待是什么?能否描绘一下你理想的诗歌蓝图。
章闻哲:定位,这个其实我在上面已有所指,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大家所承认的写好诗的诗人,我会努力写出好诗,但如果命中注定终其一生只能写出两首好诗,那我照样很满足。因为大师们已经给了我榜样。
阿翔: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进行诗歌写作,或者说什么样的状况下你最具备灵感?我觉得诗歌其实更需要的是积累:包括知识,阅历和经验的积累,以及个人的智慧和气质,你平时喜欢阅读那些方面的书籍?
章闻哲:灵感?也许出现在早晨,但是这个早晨必须有一个经过一晚的好睡眠作为前提;另外,我发现我在学习完半张英语报或其它英语读物时,会比较有灵感,我听说孩子学外语可以锻炼右脑,而右脑是想象力的基地,所以有可能灵感就是这么来的。
关于诗歌是否需要积累,我觉得是需要的,灵感是在我的思考过程中出现,就一首诗的整体来说,它已多数是思考的产物,灵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因此没有积累是不行的。譬如你的人生观,你的阅历相对应的将是诗歌的境界和厚度,你的个性形成你诗歌的风格。
我平时最常读的是哲学类,诗歌偶尔读,我说过我怕受到他人诗歌的影响,因此不会经常去读诗歌。中国古典书籍我也喜欢,言史小说我也喜欢,但没时间去读;民国时期的小说也爱读,喜欢它白话与文言揉合的语言,感觉含蓄,精致;国外的最喜欢《红与黑》,其次《简爱》、《呼啸山庄》、《基度山伯爵》等等,都是书店里常见的,读它们多数是因为对名著的虚荣,就像追求名牌一样,有点什么人穿什么,什么人读什么的意思(笑)。
阿翔: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理想化非常率性的女诗人,在你的诗歌中流露出一定的敏感和对世界的触觉。能给我们谈谈现实中的你和在诗歌状态的你吗?
章闻哲:率性?其实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极端,就是对我所认为不妥的事物,我通常会直截了当指出,很少隐忍。这大概就是率性的表现,是理想化的结果,总是想让世界按照我的标准来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我都如此,这是基于我对事物的判断之上的,我对我的判断有种过度的自信,因此总是直言不讳。这种性情肯定会影响到我的诗歌,我的诗歌有时也表现出这种极端,有股子蛮劲,这在一些情况下成为诗歌中的趣味,在另一些情况下,它是诗歌的硬伤,与传统的美学相悖。你所说的“诗歌状态”的我,我觉得有点概念模糊,我且把它理解为是指诗歌中的叙述者,它与我不尽相同,它有时是睿智的,有时是神秘的,有时是怪异的,有时是偏激的,阴郁的,有时又是调皮的,欢快的,而作为写诗的我,也许也具备其中某些特质,但远不如它来得显著。若你所指的是一切与诗歌有关的空间活动(包括精神空间)状态下的我,我想这个“我”是相对孤僻的,自闭的。它不向外界敞开,只向内审视它自己;而现实中的我则保持一个正常人应有的姿态:与人交流,在人面前保持礼貌谦和。(这种状态与你所说的率性并不冲突,因为率性的表现是不可能充满每个时间的。)新闻人赵牧曾提到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的分裂,这种诗歌性格和现实性格的分裂可能也属于大多数写诗者的通病。
阿翔:你最近进行诗歌理论写作和研究。你写诗歌评论的角度非常刁钻,你的阅读面非常宽阔,见解非常独到。我想你理论研究加上诗歌创作和探索,你将会是一位了不起的女诗人。
章闻哲:理论研究谈不上,我写评论其实是源于对哲学思辨的兴趣,(当然一开始并非如此,最初我写的评只能算是一种鉴赏活动)我希望在对诗歌的解剖中表现我的思辨,这一写作模式其实是一个命题式的游戏,当然,诗歌本身及我作为一个写诗者的意愿,都不希望它被游戏,因此我说的游戏,将从它自身的规则中来体现严肃性。一个命题从假设成立到证明成立,这其中的思辩必须经过缜密的推敲才能从自已的封锁中突围,这是件很累的活,所以我虽有兴趣,却并不热衷。有人说我写的评比诗好多了,这是真的吗?我是否能在诗歌和理论上同时迈进,这是个未知,这是两种有冲突的思考方式,一种具有严谨的逻辑,一种却要求打破逻辑,我在实践中已经感知这两者的战争,虽然不是你死我活,却也是很难调和。
阿翔:身为女性诗人,你是否关注当前女性诗歌写作?你认为当前女性诗歌写作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章闻哲:说到当前女性诗歌写作,我的一位朋友曾有一个有趣的总结,他认为就当前女性诗歌创作内容而言,主要可以分为怨妇型、精灵型、叛逆型、甜蜜型等。我觉得确切地说这是以情状来分,虽然不足为凭,却也多少道出了当前女子诗歌文本的精神状态。如果逐一分析这些不同情状下的文本,你将发现,这些情状的将主要面向男性展开,不管她是十三岁还是五十岁,一旦她的诗歌模式脱离儿童诗的模式,她的诗歌心理情状就不再单一地隶属于家庭情感产物,她更多地面向社会中的异性。因此我认为当前女性诗歌写作依旧反映的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现实,而女性的本我意识仍然处在从属于男性的位置上。尽管这些年不少诗歌刊物推出 “女诗人”专号之类的,尽管网络纷纷出现一些打有“女诗人”标志的自由团体,女子诗歌写作貌似“崛起”,本质上却只是一个数量增加事件,并未产生精神上的革新意义。
阿翔:你有没有关注女性生存的现状?生存的切面会在诗歌中直接或者间接地反馈出来。比如“汶川大地震”引发的全民诗歌潮,你认为当前诗人的任务是什么?
章闻哲:我觉得生存是全人类的事,我不会特别去关注女性的生存。每个人都有生存危机,但是只要你四肢健全一日,你就应该用劳动去创造尽量美好的生活;“低生活”也好,“高生活”也好,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活不下去的人都是对自己缺乏正确的认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帮助是让弱者的能力强大起来,而不是物质。当然,物质是基础,是前提。但他人只能给你基本的物质帮助,你最终只有靠自己强大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就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唤醒和鼓励每个人成为自己的强者。生命强大后的壮美才是最好的诗意。汶川地震引发全民诗潮体现的正是一次精神上的呼唤,让幸存下来的人继续活下去,我们在诗中记录了不朽的爱情,母爱,师爱,党爱,民族情,友邦情,爱情让人看到希望,乃至让倒下的人重新站立,并强大起来。
阿翔:我知道你和你先生《黄河诗报》主编王竟成刚结婚不久,从自办刊物的经验谈谈办刊的理想和艰辛的付出,也谈谈你对当前诗坛的了解和认识。
章闻哲:既然办刊,“办好”并不是说这个刊物在国内乃至全世界有多少多少影响,也不是简单的时代和民族声音的记录,而是希望能够创导一种新的诗观,在办刊过程中探索到诗歌的真谛,建立一种新的美学。当然这说来容易,要做到却很难,目前只能搪塞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笑)
说到当前诗坛,我只有一个认识:它是个无限开放的诗坛,什么诗都能包容。审美标准之多,足以让你怀疑和否定你最先的关于美的认识。但你可以建立你自己的诗观。并努力取得大多数人的认同。不过要注意一点,每个人都继承了传统的审美基因,你必须兼顾传统,否则你很难让人信服。我们说颠覆传统或反传统时,其实我们无时不在顾念着传统。
阿翔:你们夫妻之间美满令人羡慕。同时作为诗人,能谈谈你的幸福生活吗?你先生对你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章闻哲:幸福生活就是鸡毛跟蒜皮都很幸福,没有其它解释。他不喜欢我写的诗歌,但要是我给他写一首爱情诗,不管多差,他肯定会推崇倍至。我也不喜欢他的诗歌,但我准备接受他的诗歌,并试图理出一点思路来替他鼓吹。正确地说是鼓励。(笑)他是个相当自信的人,会认为别人的鼓吹是理所当然的。他还经常把自己赞美得一塌糊涂。我在写作上不可能受他的影响,但他今后将永远是我的第一读者。
阿翔:说说诗歌之外的话题,我注意到你很喜欢旅游和拍照。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吗?我看你的照片有时候有吉普塞女郎的流浪味道哦。呵呵。生活中的你一定是很精彩的。
章闻哲:旅游我很向往,但与我的懒隋相悖,我其实很少旅游,但我爱人喜欢,今后可能会多些出游的日子。关于吉普赛女郎的形容,在你之前也有人说过,看来这是真的。(笑)说到生活中的我是否精彩,我觉得目前尚无精彩可言。每天码字,看书,偶尔出去旅游,尽力写好自己的文字。没有很多意外。我很向往“飞特族”的生活,就是工作一段时间,赚到钱然后去旅游;花光钱,再回去工作,再玩。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看各种各样的风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充满了冒险和刺激,也挖掘了你所有的生存潜能,真正的享受生命的姿态。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不枉此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如此,这需要勇气。就说这些吧。
阿翔:嗯,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也祝愿你能在诗歌上有更辉煌的成绩。
章闻哲:谢谢阿翔。也感谢《诗歌月刊》。我想说,诗途中有你们的鼓励,很美,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