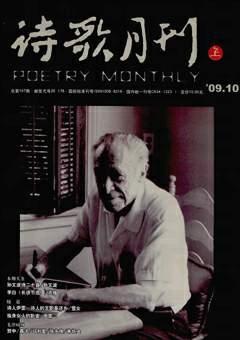读诗笔记
孙文波
1
整个清代的诗歌,除了个别诗人的作品,现在的人对之的评价,似乎不高。但如果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就技艺而言,中国古典诗歌到了清代,其实已经达到了圆熟、融通、炉火纯青的高度,很多诗人的作品让人读后不能不赞叹:写得太好了。
这不能不让人心里产生一个问题:这样好的诗歌,为什么没有获得像唐诗那样的评价呢?对这个问题我迷惑了很久,一直想不明白。
但这几年我想明白了,这是写作的有效性发生了作用。
在对中国古典诗的评价中,现在的人们大多是以唐代诗作为标准的。而唐代,由于产生了杜甫、李白等伟大诗人,更由于中国古典诗的所有范式都已在唐代得到了确立,因此,后来者的写作,如果没有在范式的意义上有所突破,自然会失去人们对之阅读时的新鲜感。
过去人们一直很忽视阅读新鲜感在阅读评价中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它总是在产生作用,也内在的成为了人们阅读时评价作品的基点。而阅读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对某一作品的孤立的阅读,而是阅读之比较。是一种由系统牵引的行为。
2
审美趣味并非一味不变,就像我国历史上曾有过以“四六骈赋”为美,推崇绮丽、浓艳文风的时期,也有把宫体诗夸到极至的时期。这些都要视那一时期的审美观为定夺。还有就是,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审美观评价那些时期,不能说萧绎、萧统,以及裴泳、韦迪之流就错了。以他们的才华和能力,对文学的认识用今天的眼光看,虽然有时代局限性,但仍然是卓越的。当然也与他们身处的社会地位有关。在我国文学史上,他们应该算真正的以贵族的身份看待文学意义的人,这一点又与今天从事文学的人很难有家学渊源不同。就算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胡适、陈独秀们,家学渊源有那么一点,但仍然很难说是到达了贵族的程度。而早期我国文学的生产者们,却几乎都是出自贵族世家,像谢灵运、谢眺、庾信等人无不是如此。而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对文学的要求自然不同。今天以大量平民身份从事写作的人,把审美要求建立在自然、朴素的观念之上,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说没有关系。
我曾在与友人谈话中分析过一点。并认为中国当代诗缺少韵致,显得不那么典雅,一方面是由于现代汉语不成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写作者的社会地位多是平民。所以,有时候我们真得不能强求一些东西,把不是属于自己社会地位的认识加到文学写作中来。为什么我总是看到一些力图把诗写得雅的人的作品,最终给人的感觉矫揉造作呢?就在于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从身份上获得一个看待事物的高点,而硬要雅起来,那种雅只能是“伪雅”。
3
在我国的诗歌史上,说到帝王诗人,曹操应该是排在前列的。这位因为一部小说《三国演义》,被民间视为枭雄的王者,却在诗歌写作上留下了不少至今被传颂的伟大名篇。就汉魏诗歌而言,如果我们能平心静气地评价,那么曹操不被排在前列是说不过去的。很多时候,当我读到这样的句子“青青子矜,悠悠我心”时,心里总是涌起感慨,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的诗人,内心是怎样的细腻啊!还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样的句子,又是体现了怎样的非凡的情愫呢?
4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杜甫其实就是一个乞丐,一生都在别人的施舍下生活。对于这篇文章在这个时候生产出来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少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已经被“经济化”了,他们看什么问题只会拿“经济”作为尺度,而从来不去认真思考隐藏在表面现象后面的,事情存在的原因,以及种种内在的理由。
杜甫的一生,活得的确困顿,很多时候也确实是在接受别人的帮助,最著名的当然是接受当时的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帮助了。但是为什么严武会支助杜甫呢?如果不是因为严武对文学的喜爱——他也写诗,不是那个时代对诗歌的推崇,严武会这样做吗?中国古代一直把文学的地位看得非常高,“诗书传家事,文章万世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杜甫之所以能够一再地获得别人的帮助,是因为人们对他作为一个诗人价值的肯定,同时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诗歌的价值的肯定。
而对文化的支助,也并不是起于唐代,在更早的时候,譬如六朝,就有不少文人是在别人的支助下生活,像梁朝的几任皇帝,在他们还没有坐在帝位上,还只是储君时,就在身边集合了不少文人,这些文人靠他们的支助生活,他们也在与这些文人的交往中,发展了自己对文学的认识。很显然,梁朝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其发展成熟的“宫体诗”,以及一整套关于文学的观念,虽然在后世被诟病得很厉害,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会看到,正是有了对“宫体诗”的再认识,才会有唐代诗歌的转换、偏移。就是今天搞诗歌研究的,如果看不到六朝诗歌与唐代诗歌的关系,恐怕也很难谈出什么有见识的话来。
因此,很多时候,文学的发展其实是有一条自己的路子的,诗人的生存方式也不完全与一般人相同,不理解这一点,自然不会懂得像杜甫这样诗人的人生生涯是怎么回事了。其实不光是中国发生着诗人在别人支助下生活的事情,就是国外这样的事情也很多,远的不说,二十世纪的西方诗人中,像庞德、里尔克都是受到支助的诗人。正是有了支助,里尔克才能镇定地住在一座城堡里,写出被称为西方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篇的《杜依诺哀歌》。如果按照那位说杜甫是乞丐的人的说法,里尔克不同样是吗?
我相信,如果不是获得了支助,杜甫不会为中国的文学留下那么多伟大的诗篇。从这个角度讲,那些支助杜甫的人,不过是代表自己的民族做了供养他的伟大圣贤的事情。而且我们还应该看到,杜甫以其留下的伟大诗篇,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给与了世界丰厚的回报。我知道仅仅一个成都的杜甫草堂,一年的门票收入就是几千万。多少人靠着杜甫以为生计。
5
中国古代文人治学问,四书五经是必须要谈论的。因此,历史上的大儒,无不是以经为源,由此出发而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但是到了今天,在文化分类越来越细的情况下,做学问的人大多是耽于自己的学科专业,我们已经看不到像古代大儒那样的通经之才。正是因为这样,季羡林先生虽然也是一代学术有成者,但其却没有面对任何领域发言的能力。
按理说,他应该清楚这一点,但最近网上引发的关于新诗的成败与否的争论,则是由于他的一句“新诗是一个失败”而来的。这句没有说明,只是结论的话,的确让人不明白季羡林先生为什么要说,他的理由何来?因为以一般性的猜测,人们都会认为,像季羡林先生这样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过来的人,对新诗的产生缘由,以及新诗在整个中国新文化变革运动中的意义不能说不了解。而在了解的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有道理吗?
反对季羡林先生之说的当然说他没有道理。那么支持他的人呢?我看了看,在他们为季羡林先生辩护的言论中,大体上的说辞主要集中在新诗不如古典诗这一点上。而支撑这一点的呢?又主要在于古典诗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体现,而新诗放弃了与传统的联系。也就是说:很可能季羡林先生之所以说“新诗是一个失败”,其依据是它没有达到古典诗那样的成就。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问题似乎就明了了,在这一点上,季羡林先生并没有说出什么有新意的话,因为从新诗诞生之日起,将之与古典诗比较,并由此得出新诗不好的结论,几乎是所有反对新诗的人的共同说辞。本来,已经诞生九十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生活中诗歌最主要的形式的新诗,应该没有必要去反驳季羡林先生的这一言论。因为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了,不管新诗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它都以事实说明了自己作为文化变革产物的存在。
不过,具体的反对可以不做,对新诗存在合理性的谈论还是应该展开。而我想说的是:一个人到了今天还认为新诗是失败的,那他真正没有搞懂的问题不是别的,主要是他没有看到新诗的产生并非是孤立的事情,它是“势”的产物。即:诗的文体之变,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这一点就如明儒顾炎武所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
其他的我们不说,身处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的顾炎武亦能清楚地辩析出变革在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的轨迹,并指出“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那么到了今天,中国之体已在现代化进程的催生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难道诗歌之变不是正常的吗?所以说,新诗的存在,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存在。它的出现以及发展,任何人都不能将之仅仅看作是一种孤立的诗歌形式的问题,对它认同与反对,实际上表明的亦是如何认识今日中国之形势的问题,不能不依附的亦是越出了一般纯粹的诗歌美学的对现代文化发展的认识。
在这里,我当然不愿意说季羡林先生连这一点都不懂。不过,不懂的确是大有人在。在当今说新诗的坏话的人,很多都是一再表明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热爱的人,是文化上的民粹主义者。可惜的是,这些人却从来只是以简单的情感代替对问题的认识,他们从来没有看到变革对于诗歌的意义。而在这样明了的事实面前,我只能说他们没有意思得很。因为很显然,新诗的存在已不可能“不存在”了,要它变,也不是变回到与古诗一致的形式,而是得等到“不能不降”的时候。
6
中唐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在变革的要求下,出现了对“奇”的热衷。韩愈一脉下来,无论是李贺,还是皇甫氵是 ,都在后来的文学评论中,被评者称为以“奇”为胜的诗人。皇甫氵是 的诗现在是不太看得到了,他的文在追求“奇”的情况下,已到了晦涩得难以句读的地步。而他本人关于求“奇”的解释,则是为了在“奇”中达到“正”,但其实又没有达到。这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言写诗必求意外一样。关于这一点,我有自己的看法,从大的方面来说,我还是喜欢“正”,即中国文化的主脉,以凛然大气、清晰雅正、朴素庄重求得诗之风貌。所以,我不太喜欢李贺的诗。在我的感觉中,凡是剑走偏锋,以精灵古怪求得一已之诗格的,最终所得不过是诗歌的风格化。而这样的获得很难成就一个诗人的伟大。李贺,包括韩愈,就诗而言,并不是最精绝的,亦不能说是中正之主流,就是如此。
7
把日常生活写进诗里,有考证说是始于陶渊明,后来杜甫的一些诗亦对之有所涉及。不过真正将之作为写作的重要问题,并从策略上去谈论的,应该是起于白居易。只要看一看他的《与元九书》关于诗的谈论就很清楚了。因而有论者说,到了中唐,中国诗歌的写作领域有所扩大,与白居易、元稹等人的大力倡导有关系。所以说到写作的日常性,虽然是中国诗歌一开始就有的东西。就是后来,尽管对日常生活的观照,已被看作诗歌写作中正常的存在,但亦不是多数诗人感兴趣的,大量的写作者,仍然是循着中国诗歌一贯的来路,把诗的注意力放在常规题材
——战乱、离别、观景、说事……——的处理上。这一点,有今人没搞明白的,夸张地说对日常性的关注是中国诗歌主要传统,错矣。
8
我并不是那么喜欢白居易的诗,但他的有一种态度我还是很欣赏的,就是他在入仕后以慵懒的心态面对生活。这样的态度使得他在喧嚣的长安不被官场的复杂所影响。之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他生性使然,另一方面还在于他很早就认识到人如果在名利面前放不开,会陷入逐名求利的忙乱之中。
9
有人认为我近两年的诗都是在“说道理”。因此有些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诗似乎不应该以“说道理”构成篇什,而应该“绘相描景”,最终以意象让诗意凸现出来。对这些人的看法,我不以为然。难道诗真的不可以“说道理”吗?中国古代早已有以“说”为主的诗,进入二十世纪,“说”更是诗篇构成的主要方法之一,只要这些人多了解一下诗歌的发展情况,他们应该不会把“说道理”作为一个问题谈出来。艾略特的《空心人》难道不是说吗?卡瓦菲斯关于同性恋的诗不是说出的吗?还有就是米沃什晚年的很多诗篇,其陈述基本上是建立在“说道理”的基础之上的。但不管怎么看,他们都是伟大的诗人留下来的伟大诗篇。我虽然不敢以为自己的诗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写诗多年,对构成诗的方法与途径,自认还是有一些研究,所谓“说道理”,关键的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说什么样的道理,或者说出的是不是有道理。在这一点上,我自认做得还不错,一是我不会无所依凭的“说道理”,二是我说出的并非没有道理。有了这两点,我觉得应该够了。而如果举例说明,像我去年的一些诗作,如《临时的诗歌观》,今年的两首诗《餐桌上的色情考》、《论某某电影剪辑问题》,都是建立在对事实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对现象的描述。写这些诗时,我恰恰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正是对这些诗的阅读促进了我这样写。因为我看到,即使是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其被人多为称道的晚年诗,其实都是在对现象的叙述中完成对生命的认识的,而且他的认识常常带有总结的意味。说实话,写诗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如果不想对什么东西做出总结性的发现,还在那里纠缠细节的营造,其实是很不正常的。但这种不正常现在似乎成为了中国当代诗歌存在的最普遍现象。我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只是有一点我的感觉越来越明显,每当我认为自己的写作有了一点进步,自己感到满意的时候,恰恰是别人认为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像很多人告诉过我,他们喜欢我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而我自己觉得真正写出有意思的作品是2000年以后,因为正在2000年,尤其是2003年以后,我终于可以写一些别人不感兴趣,但我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题材了。我相信这种对个别性的关注,是我建立“自己的”写作的正式开始。如今,这种已经开始的写作让我觉得可以不再计较自己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关系,我甚至希望它能让我最终脱离与中国当代诗歌的表面联系。
10
“玉露清风凋枫林”。这是杜甫《秋兴八首》中的一句。往年读到它,只是觉得写得很美。但一月下旬走了一趟湖南、江西、贵州,时逢大雪,漫山遍野为冰雪覆盖,一片凋零的景象,对杜甫的这句诗有了更深的体会。那段时间,一路走一路脑袋里反复出现这句诗,并思揣杜甫当年一定看到过我今日见到的景象。于是暗叹他描写的精确。
11
我们常常在书中读到这样的记载,某某某曾经著过什么什么书几十卷,但如今已经散佚。或者某某某留存世上的,只有别人著作中引录的几个残句。而这些人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都是名重一时的人物,有些甚至与同时代有著作留存下来,被今人称为伟大人物的某人,生前一起被并列为同样重要。在文化流布不发达的过去,不停的战乱,朝代的更迭,这样的事情发生,想起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是有时候我不禁会想:今天我们认为某某某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某某某是最伟大的诗人,会不会有某位作品散佚了的人,他同样了不起,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呢?譬如谢安,在六朝谢氏家族史上,他的地位比我们今天称颂的谢灵运、谢眺都高,正是他才真正将谢氏家族推上了世族大家最显赫的高位。史书上也多次说他睿智过人,风流绝世。但就是因为他写过的很多东西没有传下来。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的仅仅是他淡定中指挥人数少于敌方十倍的军队打了历史上著名的淝水大战,并给中国文化留下“草森皆兵”、“风声鹤唳”等成语。这样一个人物,我很愿意相信他的出手一定不会平淡,要是他的著述全部留存下来,说不定真的会让文化史改变叙述的。所以,一部历史只能被看作是残缺的。也说明文化的意义也可以被看作是:“保留”。就是说:保留实际上是文化存在的第一要义。没有有效的保留,一部完整的历史叙述就不可能存在。一个人的历史意义也不会显示出来。而这个道理,今天已经是普遍的道理了。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不少人拼命地想挤进历史叙述的篇章中,就在于他们认为那是一种真正的存在。只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保留也是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的,如果一个人保留下的东西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那么保留就是为他立了一块耻辱柱。那是让后世的人有了批判和嘲笑他的原始资料。
12
看到网上又有人谈论中国当代诗歌的南方精神。这个话题似乎有些年头了。不过从发言的人的情况我看到,似乎总是南方出生的诗人更关心地理带来的中国当代诗歌的差异问题。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我没有看到北方诗人谈论中国诗歌的北方精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中国文化的生成、发展,在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现象:由于国家的首都大多数时间是在北方,因此文化的主要影响力,虽然有第一个留下实名的南方诗人屈原,但都是在北方形成的。尽管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的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诗歌南北方都产生了一些。但真正构成了中国诗歌影响力主干的,仍然是来自北方的诗人写下的诗歌。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上不少伟大的诗人都是北方人,就连南朝的那些主要诗人,像谢灵运、谢 ,其家族的文化根脉仍属于北方。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是不是由于中国诗歌的主要影响力都是由北方传播开来的,因此处于南方的诗人不免在心理上感到在现实中存在着文化的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处于南方的诗人一直在心里有一种对文化中心不在自己生活的地域的焦虑。因此这种焦虑使得南方诗人对地域差异的敏感,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化影响力,成为他们要叙述问题的内在驱动力。
当然,也许这样看待问题是简单了。但是,由于尽管现在的南方诗人们以强调的口吻指出中国当代诗歌的南北差异是存在的,但是从他们的谈论中我看到的情况却是:他们所指出的种种不同,除了带有明确的符号化特征外,并没有真正地从文化发展的深层次指出问题产生的关键原因,而更多地只是从地理、气候的差异来谈论问题,譬如一谈到南方诗歌就说它是阴柔的,细腻的,一谈到北方诗歌便说它是粗犷的,刚硬的。但这些真的是中国诗歌南北不同的特征吗?如此简单的划分,在我看来带有机械主义的色彩。而如果我们随便选择一些诗人做案例分析,便会发现真实的情况似乎并不能这样一下子就划分出来。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能把像杜甫、元稹、李商隐、苏东坡这样的诗人用一种风格化的区分法划归到哪一方。还有就是,尽管历史上有影响广泛的江西诗派,但其源头却是像黄庭坚这样的诗人,他们的诗作,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其不少人的作品也并非有时下人们认为的南方特征。而我们也知道,现在的人们说到的诗歌的南方精神,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诗歌为证,反而是在词,或者说元曲上找到的雷同多一些,即人们多是从婉约派的诗作,以及昆曲中看到了可以拿来说的特征。当然,就艺术的精致而言,婉约派的一些词,以及昆曲留下的一些曲目,的确很好,但是它们在内里所贯穿的,如果只是将之以南方精神来评说,是并不够的。
而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内的诗人,尤其是最好的那一部分诗人,他们的创作实际上对这一文化的所有地域都是有所感知的。他们总是能够在非风格化的意义上写出自己选择的题材的最精微感受。因此也就不是在地域的意义上,而是在文化的支配力的意义上达到最有效地呈现作为一种文化的最优秀价值。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南北精神,在这样的诗人身上是贯通了的。至于说到仅仅单纯地求得一种地域文化在自己的作品中成为显明的特征,我觉得这是那些次一等诗人不得已而干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获得对作为文化共同体内的所有部分的有效把握,因而只能做到执其一端,在表象上求得一种符号化的获得。但我认为恰恰在这样的时候,他们让人看到的并非是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东西,而仅仅是得到了对现象的陈述。我相信任何一个有野心的诗人,都不会满足于自己的作品只是获得一种地域性符号化的成立。事实上最有意义的诗歌从来也不会是这样的东西。哪怕在一种对具体的地域的描述中,它也会让人看到其中所贯穿的一种文化的总体性价值。而这一点,是作品价值的必须所在。我们的确很难认定没有体现一种文化共同体总体价值的东西会成为这种文化共同体共同承认的经典。到是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我看到当一种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认识成为一个诗人创作的前提后,会真正产生出对地域局限性的超越而在写作中呈现出具有整体意义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所达到的是对诗学意义上的绝对价值的触及。
在这一点上美国诗人庞德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因为像他的诗歌巨制《诗章》第四首,第四十九首,以及冠名为“中国诗章”篇什,都是对他而言,具有异域色彩的题材触及,但讫今为上,我没有看到人们仅仅谈论这些诗篇是什么地域性的东西,反而有评论家认为在对异域文化的使用中,他为英语诗歌提供了少见的美。还有一个例子是现代诗人冯至,他最有影响力,受到不少评论家推崇的《十四行诗集》,其写作的来源却是德语诗歌的影响。实际上到了当代,文学的影响力最具有趣味的一部分,应该说是与现代文明带来的跨地域交流有关的。正是在不断地被异域文化的新鲜感冲击的情况下,人们在写作的变革中才出现了对新奇的把握。而诗歌创作中一个最有意思的现象亦是在不断与自己熟悉的东西疏离的过程中,那种被称之为“发现”的品质才从作品中渗溢出来,从而成为其生命的支撑力。所以说,哪怕我们需要谈论一种对自身的写作而言具有支配力的前提,也应该以更广阔的眼光看待问题是怎样的。而一味地,只是站在一种简单的认识立场上谈论问题,希冀从某种并不真正具有文化意义的地域差异上求得自身写作的成立,就穿了是一种为自己的写作寻找借口。但是这种借口实在是太小气了。它让人看到的情况是:当一个人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上面后,他所做的事情便成为了不停地把一些自以为能够体现地域特征的词汇以夸张的方法使用。
13
中国古典文学,能够给我们留下警句的诗人并不多,就算陶渊明这样伟大的诗人,留下了很多伟大的诗篇,但并没有留下多少警句,我算过,杜甫是留下警句最多的诗人,像他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等等,如今已是我们民族的箴言了。虽然一个诗人并不是要留下警句才能称为伟大,但如果有警句留世,当然是值得后人夸赞的。因为那些能够被人们到今天还可以使用的警句,说穿了,就是语言的活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