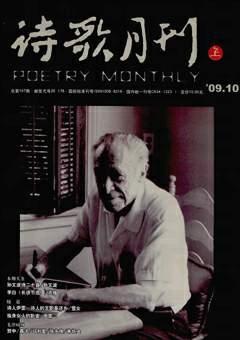查尔斯·布可夫斯基诗选
张文武译
结束
就像玫瑰一样
在应该已经开放
而太阳却好像
开始厌倦等待时
我们从来不去费力开放
自由
28号,他整晚都在
喝酒,他一直在想她:
她走路、谈话和爱的方式
她对他说那些貌似真话的假话的
方式,他知道她每条裙子
和每双鞋子的
颜色——他知道她每只鞋的后跟
和它的弧线
以及它衬托出的腿的轮廓。
当他回家时,她又出去了,
回来后又是一身恶臭,
她是这样
凌晨3点回来
像一头吃屎的猪一样肮脏
而他
拿出屠刀
她尖叫
退到里屋的墙边
仍然有些漂亮
尽管浑身臭气
然后他喝完杯中酒。
那件黄色裙子
他最喜欢的
她再次尖叫。
然后他拿起刀
然后把它从腰带上取下来
然后在她面前把衣服撕碎
然后割掉自己的睾丸。
然后把它们拿在手里
像杏子
一道红光闪过,它们被扔进
马桶
而她继续尖叫
整个屋子红了
上帝啊上帝!
你都做了些什么!
而他坐在那里,拿着三条毛巾
捂住双腿之间
也不管她现在是去
还是留
是穿黄还是戴绿或者
别的什么。
一只手捂着,另一只手
拿起酒瓶,他又倒了
一杯酒
你喝酒吗?
完蛋了,那个破旧的黄色笔记本
又暴露在岸上
我从床上写
就像我
去年那样。
要去看医生,
星期一。
“是的,医生,虚弱的腿,晕眩,
头痛,
背也受伤了。”
“你喝酒吗?”他会问。
“你一直在
锻炼吗?
吃维生素吗?”
我想,我生病只是因为
生活,那些陈腐
而又动荡的
因素。
甚至,看着马儿
在跑道上跑着,
也似乎
毫无意义。
买票进场之后,比赛没结束,
我就早早离场了。
“脱衣服吗?”
汽车旅馆的店员问。
“是的,真是无聊。”
我对他说。
“如果你在那里
觉得无聊,”他对我说,“就应该
回到这里来。”
于是我来了
又来
枕着我的枕头
只是一个老家伙
只是一个老作家
拿着黄色的
笔记本。
有东西
正从地板的另一头
向我
走来。
哦,
这次
只是
我的猫。
城里的深夜
醉倒在某个城市黑暗的街道。
是夜晚。你迷路了,你的家
在哪儿?
你进了一家酒吧去找自己,
点了苏格兰威士忌和水。
该死的酒吧,这么潮湿,你的
袖子被弄湿了
一大片。
这是一家黑店——苏格兰威士忌没味儿。
你点了一瓶啤酒。
穿着裙子的死神夫人
向你走过来。
她坐下来,你替她买了瓶
啤酒。她身上发出沼泽的臭味。她把一条腿
压在你的身上。
酒保咯咯地笑了。
你让他有些担心,他不知道
你是警察、杀手、疯子
还是
白痴。
你要了一瓶伏特加。
你把伏特加倒进啤酒瓶
直到倒满。
凌晨一点。死牛的世界。
你问她,脑袋值多少钱。
你把酒一饮而尽。有股
机器润滑油的味道。
你把死神夫人撇在那儿,
你把那个咯咯发笑的酒保
撇在那儿。
你已经记起你的家
在哪儿了。
你家里的餐具柜上
有整瓶的酒。
你家里满是乱七八糟的
烟头。
“粪堆星球”上的杰作。
爱在那里大笑着
死去。
青鸟
我的心里有一只青鸟
他想飞出来
但我对他非常粗暴
我说,待在那里,我不会
让任何人看到
你
一首就要写完的诗
我看到你在喷泉旁喝酒,双手
微小而苍白。不,你的双手不是微小
是短小,而喷泉是在法国
你在那里给我写了最后一封信
我回了信,然后再也没有听到你的任何消息
你过去常常给我写疯狂的诗
都是关于“天使和上帝”的,全是大写字母。你认识了
一些著名的艺术家,他们大部分
都是你的情人。我回信说,没事,
继续,加入他们的生活吧,我不嫉妒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曾经在
新奥尔良住得很近,一个半街区,但从没见过面,
从没有接触过。你和这些名人走到了一起,
写他们。而当然,你发现
这些名人很在乎他们的
名声——而不是跟自己一起躺在床上的这个
美丽的姑娘。你把那给了他们,并在早上
醒来后,用大写字母写诗,
关于“天使和上帝”的诗。我们知道上帝死了,他们
说的,但是你的话让我不敢确定了。也许
是因为大写字母。你是最漂亮的女诗人
之一,我跟那些出版商和
编辑说:“她,给她出吧,她是疯狂,但是她
很神奇,她的火焰里没有谎言。”我爱你
就如同一个男人爱着他从来没有碰过的女人,
只是给你写写信,有几张你的照片。我本来可以
更爱你,如果我能在一间小屋里,点上一根
香烟,听你在洗手间里小便。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你的信越来越悲伤,
情人们背叛了你。你无力挽回这一切。你说,
你有一张哭泣的长椅,它在一座桥上,
坐落在一条河上的桥。每天晚上,你都坐在这张
哭泣的长椅上,为你的那些情人哭泣,他们
伤害了你之后就忘了你。我回了信,但是再也
没有收到你的信。一位朋友写信告诉我
你自杀的消息,这时你已死去三四个月了。如果我
和你见过面,我可能会很不公正地对待你,或者,
你会那样对我。还是这样最好。
友好
总有人要求我们
理解别人的
观点
不管那观点
多么过时
多么愚蠢或者
让人讨厌
总有人要求别人
去评价
他们那彻头彻尾的错误
他们在友好中
尤其是在
成年之后
浪费掉的
人生
而我们主要和成年人
打交道
他们成年以后
很糟糕
因为他们的
生活
没有焦点,
他们拒绝去
看
不是他们的错?
谁的错?
我的?
有人要我隐藏
我的观点
不让他们知道,
因为他们不想面对
恐惧
成年没有错
但是,那种可耻的
被蓄意
浪费掉的
人生
夹杂在这么多
被蓄意
浪费掉的
人生中
是错误的
就像麻雀
要放生,你就得杀生。
当我们的悲伤跌落在
盛满血的海上,
我在那内部严重断裂的浅滩上走着,浅滩边缘
是正在腐烂的生物,白色的爪子,白色的腹部,
这长长的死亡的一线沙滩,对抗着周围的景色。
亲爱的孩子,我只能像麻雀那样
对待你。在流行年轻的时候,
我老了。在流行笑的时候,我哭了。
在本来无须太多勇气就能爱你的时候,
我却恨你了。
记忆中的微笑
我们养了一些金鱼,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
放鱼缸的桌子旁,是可以看风景的窗户,
厚厚的窗帘垂下来。
我的母亲永远微笑着,她希望我们全都
幸福,她对我说,“开心点儿,亨利!”
她是对的:在能开心的时候保持开心,总是一件
好事。
但是我的父亲继续打她和我,每周都要来那么几次,
只要
怒火在他六英尺二英寸的身体内燃烧,在
他不了解是什么从他的内部袭击他的时候。
我的母亲,可怜的鱼,
她希望能幸福;尽管每周都挨两三次打,
却要我高兴:“亨利,笑一笑!
你为什么从来不笑?”
接着,她就会微笑,让我看清应该怎么笑。那是我见过的
最悲伤的笑。
有一天,金鱼死了,五个都死了。
它们漂在水面上,侧着身子,它们的
眼睛依然睁着。
父亲回来后,把它们扔给了厨房里的
猫。我们就这么看着,而母亲
微笑着。
人群中的孤独
肉裹着骨头
他们把一颗心
放在那里
有时候是一个灵魂,
女人们把花瓶
往墙上摔
男人们烂醉
如泥
没有人发现这个
人
就这么
看着
不断从被窝里
爬进爬出。
肉裹着
骨头,而
肉寻找的
不止是
肉。
根本没有
机会:
我们都陷入了
一种奇特的
命运。
从来没有人发现
这个人。
城市的垃圾堆满了
废品收购站满了
精神病院满了
医院满了
墓地满了
其他地方
都没有满。
悲伤的目的
我甚至听见了群山
它们怎样笑
在它们蓝色的山腰上来来回回
再跌落水中
鱼哭了
水
是它们的眼泪。
我听着那水
在我不停喝酒的夜晚
悲伤变得如此强烈
我在钟表中听见了它
它变成我衣服上的结
它变成地板上的纸
它变成鞋拔子
洗衣票
它变成
香烟的烟雾
顺着长满暗色藤蔓的教堂向上爬……
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爱,不是太糟糕
或者,没什么生活
重要的是
在墙上等待
我生来就是为了这个
我生来就是为了让玫瑰在死者的路上尽快凋落。
刮胡子时刮伤了脸
没有什么是恰到好处的,他说,人们看起来的样子,
音乐响起来的方式,词语被写下来的
方式。
没有什么是恰到好处的,他说,人们教给我们的
一切,我们追逐的爱,我们的
死,我们的生,
它们都不是恰到好处的,
它们几乎无法接近恰当,
我们的生活
一个接一个地,
堆积成历史,
物种的浪费,
碾碎的光和路,
不是恰到好处的,
几乎一点都不合适,
他说。
我不知道吗?我
回应道。
我从镜子前走开,
早晨,下午,
晚上
没什么改变,
都被固定在原地。
有东西闪了一下,有东西破了,
有东西留了下来。
我走下楼梯
又走进去。
忏悔
等待死亡
就像猫
将要跳到
床上
我为我妻子
感到非常难过
她将看到
僵硬
苍白的
尸体
再一次摇晃它,然后
可能
再来一次
“汉克!”
汉克
不回答。
我担心的不是我的死,
而是我的妻子
她将守着
这一堆
废物。
然而
我想
让她知道
和她
躺在一起的
每个夜晚
即便是最无聊的
争吵
也是
美好的
最难说的
话
我曾经最怕
说的话
现在
也能说了:
我爱
你。
毁掉
威廉·萨卢因说,“我毁掉了自己的
生活,因为我跟同一个女人
结了两次婚。”
总有一些事情
会毁了我们的生活,
威廉,
这只取决于
什么或哪一个
先找到
我们。
时机一直都很成熟,
我们随时
都会
被抓住。
生活被毁掉
很正常
无论你
聪明
还是不聪明
都是一样。
只有在
自己的
生活
被毁掉时,
我们
才发现
自杀者,
酒鬼,疯子,
囚犯,吸毒者
等等,等等
只是存在中
常见的一部分
就像
厨房架子上的
剑兰,
彩虹
和
飓风
以及
空虚。
你
你是最好的一个,她说
你又大又白的肚子
和毛茸茸的脚。
你从来不剪指甲
你有一双胖手
爪子长得像只猫
你红得发亮的鼻子
和我所见的
最大的睾丸。
你射起精来
就像鲸从背上的洞里
向外喷水。
畜生畜生畜生,
她亲吻我,
你早餐想吃点儿什么?
因与果
那些最好的总是死于自己的手,
只是为了摆脱,
而那些留下的
不可能完全明白
为什么
每个人
都想
摆脱
他们
地狱是个孤独的地方
他65岁,他的妻子66,
有老年痴呆症。
他的嘴
患了癌症。
做过
手术,放射
治疗
这毁了他的
下颔骨
所以不得不用金属丝
将下巴固定。
每天,他把妻子放进
橡皮尿布
就像
对待一个孩子。
他的身体条件
不允许开车
他不得不乘出租车
去医疗
中心,
说话有困难,
只好
把路线
写下来。
回来后
他给妻子
换尿布
打开电视
晚餐
看晚间新闻
然后进卧室,拿起
枪,对准她的
太阳穴,开枪。
她倒向
左边,他坐在
沙发上
拿起枪
放进嘴里,扣动了
扳机。
枪声没有唤醒
邻居们。
后来
燃烧的盒装电视便餐
唤醒了他们。
有人来了,把门
推开,
看见了。
很快
警察来了
例行公事
发现了
这些东西:
一个已没用的
存折
一本支票簿
余额
1.14美元
自杀,他们
推断。
不到三星期
来了两个
新房客:
名叫
罗斯的
计算机工程师
和他的妻子
学芭蕾的
阿纳塔娜
他们看起来像是
积极进取的
又一对。
垃圾箱
太棒了,我刚写了两首
我不喜欢的诗。
电脑里有一个
垃圾箱。
我刚把这些诗歌
挪走
丢到了
垃圾箱里。
它们永远消失了,没有
纸,没有声音,没有
暴怒,没有胎盘
而后
只剩一张干净的屏幕
等着你。
在编辑拒绝你之前
拒绝自己
总会好一些。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下着雨的夜晚,而收音机里
还播放着难听的音乐。
而现在——
我知道你在
想什么:
也许他应该
把这个
私生子
也移到垃圾箱里。
哈,哈,哈,
哈。
黑暗中的朋友
还记得
我在一个陌生城市的小房间里挨饿
拉下窗帘
听古典音乐
我年轻,我如此年轻,这像体内有一把刀一样
伤害着我
因为我别无选择,只有尽可能久地
躲藏——
不是自怜,而是为我有限的机会而沮丧:
试着与人沟通的机会。
只有那些老作曲家——莫扎特,巴赫,贝多芬,
勃拉姆斯对我说话,
而他们已经死了。
最后,被饥饿吞噬的我
到街上应聘低薪的
单调的
工作
桌子后面的陌生人为我面试
没有眼睛的人,没有面孔的人
他们将拿走我的时间
打乱它
弄脏它。
现在我为编辑和读者以及评论家们
工作
但是依然游荡,喝着
莫扎特,巴赫,勃拉姆斯以及
贝多芬
有些好伙伴
有些人
有时候让我们能继续孤独下去的
只有死者
他们使围住我们的墙
喋喋不休。
爱·名誉·死
它此刻坐在我的窗外
就像一个去往超市的老妇人;
它坐在那里看着我,
它的汗不安地
通过电线、雾、狗叫声冒出来,
直到我突然
把报纸扔向纱窗,
就像拍击一只苍蝇,
而你能听到这平静的城市上空
发出的尖叫,
然后,它离开了。
结束一首诗的方式
跟这相似——
突然变得
安静。
伟大的莽汉
我是一个天生的莽汉
我喜欢躺在床上
穿着汗衫(当然
是污迹斑斑)(还有些香烟
烧出的洞)
光着脚丫
手里拿着啤酒瓶
努力甩掉
一个难熬的夜晚,跟一个
仍在地板上
四处走动的女人说着话
她抱怨这个抱怨
那个
我迸出一个
饱嗝,说,“嘿,你不
喜欢?那就从这里
滚开吧!”
我很爱自己,我
很爱作为莽汉的
自己,而
她们似乎也是如此:
总是离开
但几乎
都会
再次
回来。
鞋子
在你年轻时
一双
独自
待在
橱子中的
女式
高跟鞋
便能燃起你的
骨头;
在你年老时
那只是
一双
没人
穿的
鞋子,
也
一样
很好。
巴黎
决不
即使在更冷静的时刻
我也决不会
梦见自己
戴着
贝蕾帽
骑着自行车穿过那座
城市
而
加缪
总是
令
我
厌烦。
我来了……
凌晨三点,干掉第二瓶酒之后,
醉了。我敲出了十五页
诗歌
在这逐渐退去的黑暗中
一个为年轻姑娘们的肉体而疯狂的
老男人
肝脏没了
肾正在完蛋
胰腺疲倦了
血压升到了最高点
挑战黑暗
击中眼睛
击中脑袋
击中屁股
如舞场的一朵花般,射击
别无选择
心里有一个地方
永远无法填满
一个空间
甚至
在最好的时刻
以及
最好的
年代
我们也将明白
我们将会
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明白
心里有一个地方
永远无法装满
然后
我们将等待
再
等待
在那个空间里
落幕
一个无比漫长的音乐剧之后,
幕落了,有人声称
看了这个音乐剧不止一百次。
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了这个落幕:
鲜花,欢呼,眼泪,雷鸣般的
赞美。
我没看过这个特殊的音乐剧,
但我知道如果我看过,我将
无法忍受它,它将
令我恶心。
请相信我,这个世界和它的
人民以及它那娴熟的表演
很少为我而作,只是对我而作。
还是让他们继续取悦彼此吧,这将
使他们保持在我的门外,
而为此,我自己将报以雷鸣般的
赞美。
月亮、星星以及世界
夜晚散一个长长的步——
这对心灵有益:
向窗户里撇几眼
看着疲惫的主妇们
努力摆脱
她们发酒疯的丈夫。
努力摆脱
她们发酒疯的丈夫。
衰落
早上八点,我在房子旁边赤身裸体,
往身上涂芝麻油,
耶稣啊,
我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吗?
我一度在黑巷中战斗,
只为开怀一笑。
现在我不笑了。
我把油和惊讶泼到自己身上,
你想要多少年?
多少天?
我的血液已被玷污,
一只黑天使坐在我的脑中。
事情总是这样,
源于某物而归于虚无。
我理解城市的陷落,
国家的陷落。
一架小飞机从头上飞过。
我抬头张望,仿佛这种张望
真的有什么意义。
没错,天空开始腐烂:
时日无多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如此。
接近伟大
在人生的某个时期,
我曾遇到过一个男人,他声称
自己曾到圣伊丽莎白街拜访过庞德。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她声称
自己不但拜访过
E.P.(庞德)
还跟他
做过爱——她甚至
跟我说
艾兹拉肯定在那些长诗的
某些章节里
提到过
她。
是的,就是这个男人和
这个女人
女人说
庞德从未
提起过
这个男人的来访
而男人则声称
那位女士
跟大师
没有任何瓜葛
她只不过是在
吹牛
可是,因为我不是
“庞学”专家
我也不知道
该相信谁
不过有一点
我很清楚:
如果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
就有很多
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过来攀亲戚
那么在他死后,哈,
人们还不
炸开了锅。
我估计,庞德
既不认识那位女士
也不认识那位先生
或者,即便他认识
其中的某一位
抑或是
两个都认识
也只能说明
他在一家疯人院里
可耻地浪费了一段时光
写作
通常情况下,
在你
和不可能性之间,
只有它。
没有任何酒,
没有任何女人的爱,
没有任何财富,
能比得过
它。
傍晚与约翰·芬提的短暂谈话
他说,“福克纳在好莱坞工作的时候,
我也在好莱坞工作。
福克纳最糟糕了:天黑的时候,
他因为喝得太多,站都站不起来,
我只好帮他打出租车,
几乎天天如此。
“但是他离开好莱坞后,我留了下来,而既然我
没有喝成那样(或许我应该那样),我应该
有勇气跟他走,离开这
该死的地方。”
我告诉他,“你写得跟福克纳
一样好。”
“你那样认为吗?”他在医院的床上
微笑着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