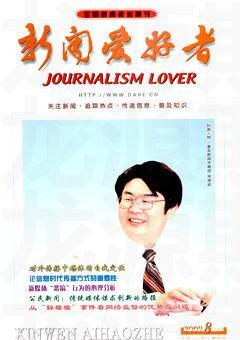手机短信文学后现代特征探析
桓晓虹
摘要:手机短信文学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伴随着手机短信功能的日益加强而诞生的,以手机为媒介的文学新样式,传达出后现代的多重文化特征:异化性、开放性、平民性、游戏性、快餐性、潜意识性,从而使短信文学呈现出复杂多元性。
关键词:短信文学后现代复杂特征
当今时代是个多元化思想并存的时代,有传统文化对人们根深蒂固的影响,也有现代、后现代文化对人们的冲击和警醒,共同构成一个复杂多变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下,短信文学所使用的“话语”“代码”除了传统的文字之外,还依赖音像、数字、字母和其他符号,甚至有些文本大部分借助的是音像动漫、计算机字符等的辅助作用产生多种意义,离开了辅助的内容,便不成为文学了,从而体现出多媒体互融的特点,如彩信文学。而多媒体互融、多元文化的影响等,使短信文学具有了异化性、开放性、平民性、游戏性、快餐性、潜意识性等后现代特征,加速了短信文学作为新时代条件下诞生的新文学样式的不断完善、确立和丰富,对短信文学走向成熟、绽放奇花异葩,成为文学殿堂独具特色的、拥有最平民的作者、占领最普遍的读者群体的一种文学样式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异化性。弗洛姆指出,消费异化普遍存在。“在消费异化的驱使下,人们相信这样的原则:每个欲望都必须立即满足,任何欲望都不得受挫”。在当今物质消费日益扩张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不能沉潜于严谨务实的生活中,而是以追求感性快适,追求无意义化等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短信文学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普通百姓的庸常人生,竭力回避一切崇高、宏大。甚至追求无意义的空洞,在无意义中放逐自我,关怀世俗生活,表现出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强烈的叛逆、解构精神。短信文学的语言、符号等运用,外在形式的非常规化,所体现出来的快餐化、肤浅化、嬉皮士的文学追求,以及幽默好玩的玩笑态度甚至黄色化所表现出的“有意堕落”等,亦体现出对传统文学的异化和颠覆。如一首题为《黑》的诗歌:“黑夜/我穿着黑衣/干着黑色的勾当/却没有留下黑影。”和顾城那首“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相比,从意义而言,根本没有诗味,简直不能称做“诗”。且表现出对顾城已成经典的作品的解构、叛逆和异化。而一篇得票率颇高的《心的房子》:“我的心是一座封闭的房子,房子的里面只有一扇窗子,窗的外面满是秋天的叶子,那扇窗外是我惟一的心事;我的心是一座空洞的房子,房子的墙上写满你的名字,我喜欢看窗外飘零的叶子,也喜欢这样想象你的样子。”每一句都押了韵,似乎很有诗意和散文性,可要找它传达出来的意思,空洞得几乎根本没有意义。表现出对主流文学的严重疏离、叛逆。
开放性。短信文学文本不再是封闭的不可触动的经典范本。而是开放的,读者和作者都可以介入文学创作流程。但短信发送需要有相应的手机号码,它不能像网络文学一样一按键盘就可昭布于世;并且它的交流对象往往是自己熟悉的朋友、同事、同学、亲人。发、收者之间特定的社会关系使短信文本的书写不得不仔细斟酌。这使得短信文学互动却不混乱,开放又有约制,大大增强了短信文学自身的净化功能。
有一位网民对网络文学的开放性作过这样的描写:“买来猫一个,鼠标点四方,打开入窗口,转帖十六方,来的全是客,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走页就翻,有什么周祥不周详。”而短信文学的开放与此截然不同,其开放是秩序的,是有相对范围的。有人情味的甚至充满亲情的,是互动而有节制的。彼此的距离在有节制的开放沟通中不断拉近。
平民性。文化大众化是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展开,也是后现代文化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知名学者程文超指出:“今天的社会……越来越不需要精英。人们制造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也将越来越快地消失。”杰姆逊认为,在后现代社会里,“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限基本消失……商品化的逻辑浸渍到人们的思维中,也弥散到文化的逻辑中”。短信话语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打破了艺术和生活的界限。
短信文学的民间性和平民化的倾向是由手机媒介引起的。手机媒介使平民阶层,主要是社会中占大多数的被统治者赢得了表达自己话语的空间和相应的话语权利。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居民手机短信消费行为的一项调查显示。63.1%的被访者曾经使用手机向他人发送过短信,其中年轻人发送的比例高达89%。从这些数据来看,大众是手机媒介的上帝,没有大众对手机媒介的青睐,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短信文学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优越性。大众所热切关注的、渴求的、讨论争议的等,自然而然成为短信文学所关注和热切表现的。在短信文学中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关于社会百态的小篇章,看到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景象书写。短信文学的大众化是前所未有的。
大众化的作者,大众化的受众。共同构建了一个绝对自由平等的乌托邦王国,其中无拘无束地回荡着民间真正的声响,自由自在地袒露着大众化的审美追求。短信文学借助大众化强有力的翅膀成功飞越贵族文艺、精英文化那高不可攀的宝座,轻轻松松飞进平常百姓家,抚慰着人们的疲惫身心,展示着文学的独特魅力。
游戏性。西方世界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后现代主义高高树起了大众文化的旗帜,热衷于游戏,努力摆脱官方的一切约束和规范,在自由、怪诞、戏谑、轻松中放纵地享受狂欢节文化,在文学创作上。大众文化主张创作的游戏性、反深度模式。后现代主义的声音在当下中国得到回应。比如,“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带着炸弹,去银行看看,警察准备了一副手铐,狱长张罗了一床毛毯。生活的烦恼,向狱长说说,犯罪的细节,向警察谈谈”,该短信将犯罪表述得如此轻松、诗意,一方面纵然是对社会严肃面孔的调侃,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玩笑界限的思考。这种玩笑是无深度的,是对人们游戏精神的充分演绎和积极满足。
席勒说:“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也才完全是人。”我们在各式各样的短信中“快乐着别人的快乐,幸福着自己的幸福”。短信文学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仅仅为了搞笑、娱乐、整蛊而作。如,“横眉冷对考试卷,眼睛直对钢笔尖,英雄不怕打零蛋,挺直胸脯交白卷”,这类话语短信的严肃意义被消解,成为幽默,甚至成为开玩笑性的游戏话语,看不到对生活的严肃,对交流的一本正经,对人生的审慎态度,看到的是玩世不恭,看到的是快乐调侃,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毫无隔阂毫无防备毫无拘谨的自由自在和彼此的娱乐、调节、排解,而这些又是如何地释放了人们与生俱来的游戏冲动,填补着人们伴随着成长内心深处日益增强。现实生活中却被日益“饥渴着”,以至于早已处于虚空状态的游戏需要。
快餐性。如果留心会发现,“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