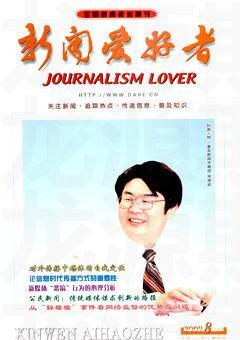《红星》报的非新闻业务
王卫明 陈信凌
《红星》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1935年8月3日因红军即将进入草地而停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这份报纸的非新闻业务是怎样的呢?
一再策划和发起活动
与现在的许多报刊一样,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红星》也曾策划和发起一些活动,例如,捡子弹壳的运动。1934年5月30日第45期第四版刊登王宗槐的《我们检弹壳的成绩》,其中写道:
“《红星》报提出检子弹壳的运动后,得到红色战士很热烈的回答与拥护。关于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第二师曾普遍在党团小组中讨论了,立即发动进行,并决定以每个党团小组为单位去收集,检阅党团员。这一工作的进行,成为经常应有的工作。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同志,更积极去收集,每次战争后检阅一次;就是负伤的同志都能很积极的搜检。最近两月中单青年,共捡到了子弹壳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发,子弹八千三百九十发。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现我们还在继续努力进行着,希望其他各部队的同志,也要注意这件事呵!”
此外,《红星》还一再对读者发起号召。例如,1933年8月13日新第2期第2版刊登了《热烈购买经济建设公债》;1933年8月19日新第3期第2版刊登了《本报号召红军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1933年10月1日新第3期第4版刊登了《两个号召》,这两个号召分别为“红军部队快速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每个红军战士每个月写两封家信”,《红星》还为后者特设专栏登载“红军家信”;1935年1月15日第68期第2版刊登了《本报号召
本月廿一日前每三人扩大一个红军》。
1934年11月7日出版的《红星号外》,实际上也是一次号召——《本报号召
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
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3年11月30日,《红星》曾发起六次号召,这些号召“在红军部队中引起了一些反响,特别是在白区每月扩大一千个红军的号召,得到各部尤其是东方军的响亮回答”。
重视与兄弟媒体的协作
与兄弟媒体进行报道或活动方面的协作,有利于形成舆论合力。对此,《红星》比较重视,甚至曾专门刊文推动相关协作。
1933年12月3日的第18期第四版刊登了《关于红星报的号召——给各红军报纸的编辑者》一文,文章指出:“各红军的报纸,对《红星》的号召是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许多报纸上很少看到对《红星》号召的响应与回答,甚至有些问题《红星》已提出了号召而自己又再来一次。这主要是由于不了解《红星》的号召是代表总政治部的意见,是带有领导性质的。各红军报纸对这些号召的任务,应该是伴着它的周围,把一切报纸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一号召之下,组织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来响应和回答《红星》的号召,亦即是总政治部的号召。”
而在1933年11月26日的第17期第二版,刊登了《本报响应青年实话的号召以战争的胜利来回答群众慰劳我们的热忱》一文。
印务情况
《红星》的刻印方式以铅字印刷开始,以铅字印刷为主,但有不少是手刻蜡纸油印,最后以油印结束:
第一,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第31期(1933年3月3日)至第35期(1933年5月12日)和第68期(1935年1月15日)是手写油印的32开报纸。
1933年8月6日,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新第l期,恢复铅字印刷4开报纸。
第二,未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字样的新第l期(1934年10月20日)至新第26期(1935年8月3日)是手写油印的4开报纸。
据负责刻蜡版的《红星》报工作人员赵发生回忆,“《红星》报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时期和长征途中。前一时期是铅印,纸张是自己造纸厂造的毛边纸……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是油印的……纸张是从根据地带出来的。过草地以后。入了藏民区,担子挑的纸用完了,就买一些印过藏经的纸,用背面印报。”
《红星》的印张也不固定。一般为“本期一张”,但也有“一张半”或“两张”的情形,如1934年9月10日第46期“本期一张半”。1935年1月15日第68期“本期两张”。
1934年6月5日,第46期,一版刊登了《印刷所声明》:“本期报,第二、三版位置装反,油印工友上版时弄错,望读报者同志注意为盼。”落款为“军委印刷所”,表明这时是由军委印刷所负责印刷《红星》报。
发行情况
一度定价大洋三厘。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3年8月6日新第1期。没有标明售价。第3l期(1933年3月3日)至第35期(1933年5月12日)《红星》报,系手抄油印,没有标明售价。
1933年8月13日第2期至1934年9月25日第66期。《红星》报一般都在报头区刊登“定价大洋三厘零售铜元一枚”字样,标明售价,此前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附加副刊,售价也一样不变。
1935年1月15日第68期起(第67期散失,情况不详),《红星》报均系手抄油印,不再标明售价。
1932年3月11日,23日的第11、12期《本报特别启事》:“近来连接各地方来信,购阅本报,要求多多印发,以便广为推销,兹特规定凡地方订阅本报者,每份铜元一枚,作辅助印刷费,由各地方机关直接写信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社订购,预订若干期若干份,均先将订报的钱寄来,写明通讯处,即按期照付,至于红军学校,后方医院兵工厂,拥护红军委员会、各军区所属地方武装等机关部队,仍不收报费,特此启事。”
发行量在中央苏区名列第四。《红星》报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就达17300份。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1月22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曾提到:“仅在江西苏区,《红星》报的发行量就达一万七千三百份。”
而据《中央苏区美术的蓬勃发展》的介绍,“1934年1月26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向‘二苏大作报告,总结了中央苏区群众文化宣传活动的发展情况:已出版发行大小报纸34种,其中《红色中华》已发行4万份,《青年实话》已发行2万8千份,《斗争》已发行2万7千1百份,《红星报》已发行1万7千3百份。”
由此可见,《红星》报的发行量,在中央苏区数十种报刊中名列第四,仅次于《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和《斗争》。
另据1932年12月19日的《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作者为原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介绍,《红星》也发行至湘鄂西苏区。由此可以推测,《红星》报的发行范围不局限于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其发行量超过了17300份。
当然,非常时期(例如,战斗非常激烈时,长途行军途中)的《红星》报。发行量达不到17300份,例如,“长征途中的《红星报》……每期印700至800份”。
发行机构及主要读者。“当时《红星》报的发行是由总政治部发行科负责,它的主要读者是红军指战员及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长征途中的《红星报》……发到连队。”
《红星》报的内容十分符合目标读者定位——红军指战员:“卫生讲话”、“卫生常识”都与红军指战员(特别是行军时)的健康维护有关;“小玩意”、“猜谜”都是娱乐性栏目,但这两个栏目的具体内容都是与军事有关的;“红军歌曲”、“红军诗歌”、“红军歌谣”等栏目的开设,也显示出《红星》的军报特色。
广告只刊登于中缝
《红星》报的广告只刊登于中缝,内容除书报刊出版发行的广告外,还涉及招生广告、遗失启事、寻人启事、领取股票及红利的启事等。
1933年11月12日第15期,第六版和第七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这样的广告:“《中国地理常识》出版印刷了仅三千份。购者从速,定价每本大洋壹角,红色战士减半。发行处——红军总政治部发行科。”
1934年3月25日第34期,第一版和第四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3条广告:一是《我们红色战士所渴望盼步兵战斗条令第二部出版了》;二是《卫生学校函授启事》;三是通知领取红军合作社股票及红利的启事。
1934年1月21日第25期,第二版和第三版之间的中缝刊登了《遗失党证声明作废》和4则《访问启事》。其中3则《访问启事》的内容分别为:
钟涵兴,兴国上社区秀水乡长岭下村人,一九二九年到×红四军,三年未写信回家。
妻曾祥瑞
温春发仔,于都×区黄凹×乡孟口村人,当红军三年没有写信回家。
弟温柔
龙××,公略中鹄区第十一乡兆省村人,一九三零年九月到X红五军,无音信。
兄龙文
从内容上看,上述《访问启事》实际上是寻找红军战士的寻人启事。(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4年度资助项目《江西苏区新闻事业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