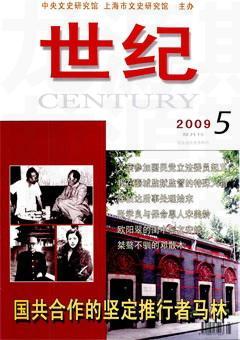桀骜不驯的邓散木
王晓君
邓散木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书法篆刻家。其书法气雄力健,浑厚流丽,富金石韵味;其篆刻沉雄朴茂,清新古拙,老辣奇倔,在印坛独树一帜。但邓散木的一生坎坎坷坷,走得却十分艰难。在上海我曾拜访过邓散木夫人张建权,从而对邓散木有了更多的了解。
拜师学艺
邓散木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邓策为孙中山先生发起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支部闸北区会长。邓散木从小被送入英国人办的华童公学读书,因脾气倔强,不能忍受英籍老师的辱骂和挨打而中途退学。他在《六十自讼》中写道:“教师碧眼胡,贱我如奴星。”从此,邓散木走了一条“埋首故纸堆,无师自钻寻”之路。
邓散木家住上海浙江北路,弄堂口有个成衣摊,摊主名叫韩不同,人矮小瘦弱,貌不可相,然而他能文能武,写得一手何绍基体的好字,还有站桩功的绝门。他便日日向韩不同学书练武,渐渐地他的指、腕、肘、臂都有了力,可以单手握住核桃,用劲将核桃“握”得粉碎,这无疑为他成为书法家打下扎实基础。有一年,韩不同回常熟探亲,染上瘟疫而病故。邓散木痛哭不已,发誓练好字来报答师傅。邓散木在家除临师傅留下来的帖之外,还专心地临摹书房里李肃之为父亲写的四条屏。不到两年时间,他已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邓策感到“孺子可教”,便带了邓散木去见李肃之,李肃之见之击节夸奖并收他为自己的学生,把腕指点。
不久,经李肃之保荐,邓散木进入上海会审公廨(上海临时法院)顶替李肃之的位置,成了上海公廨最年轻的文书,那时他仅18岁。
邓散木一天能写六、七千字,日书信封八百,成了公廨里的快手。工作之余,他还从事书法、篆刻,所获润例便掷于酒家,于是他的落拓不羁的性格和饮酒海量之名声传遍四方。弄堂里的几个好事者便邀他打赌:一天之内如能喝完一坛酒(50斤),就再奉送一坛。血气方刚的邓散木一口答应。到了约定的日子,好事者拿来了好几坛酒。十来个打赌者从早晨喝开了,到了中午,剩下了3人。下午一个醉昏了过去,一个求饶,只有邓散木还在喝。夕阳西下,50斤老酒点滴不存,邓散木神志爽然,并赢了一坛酒。其实他喝酒有个习惯:要么边独酌边读书,要么大发其“疯”,哇啦哇啦大哭一场了事。他在《醉话》中说:“每日能大笑一次,能有益卫生,此理人人知之。独吾谓每日能大哭一次,其益当较笑为尤胜,盖举抑塞磊落之胸襟,无自排泄,并欲笑而不可得者,概以一哭了之,则霎时便块垒顿消矣。”
三次易名
邓散木脾气很怪,怪得似乎有些不通人情。他30岁后改名为“粪翁”,将居所称为“厕简楼”;40岁后改名为“散木”;63岁后改名为“一足”、“夔。”名改得很畸,不易理解,其实,他几次易名都有他的道理。
邓散木的父亲邓策是早期的国民党员,受父亲影响,邓散木对“国父”孙中山极为崇拜,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也参加了国民党。自“四·一二”政变后,邓散木对国民党产生了信任危机,很快脱离了国民党。邓策抵御不了社会腐败的风气,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沉沦了。社会的丑恶,家父的沉沦,使邓散木再也忍受不了了,但又无可奈何,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粪翁”、“海上逐臭之夫”,还专门制了一块铜牌“厕简楼”挂在门前。邓散木在《六十自讼》中说道:“非敢求惊人,聊以托孤愤。”铜牌挂出,惹了不少非议,然而他均嗤之以鼻,不予理睬。说来有趣,抗战前,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托人来找邓散木,要他为其亡母撰写墓志铭,书写墓碑,但必须除去“粪”字,署他名,润例可从优。邓散木听后顿时来气,说:“既然讨厌粪字,又何必找我粪翁。我虽贫穷,但宁可无米下锅,灶清灰冷,也不改‘粪字。”说完便毫不客气地将来人“请”出家门。他的夫人张建权对邓散木改名“粪翁”,且在书写时将“粪”字写成“冀”也更为不解。邓散木解释道:“荀子曰‘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堂上的杂草、污秽还没有弃除掉,哪还有空闲到郊外去观察有没有杂革呢?如今的天下,杂草丛生,污秽遍野,不打扫打扫,怎么得了。至于粪字头加撇,我是永远不会忘记洋人打我的那记巴掌。”
邓散木在三十年代初到抗战胜利之前,先后办了11次个展、合展,名噪江南,时人称他为“江南祭酒”(首席之意),将他和齐白石齐名,为北齐(白石)南邓(散木)。而邓散木深感不安,感到自己对解救民族危亡几乎没有作出什么贡献,挂此桂冠,实在惭愧。抗战胜利后,他见百姓没有得到任何实惠,反又陷内战之中。那些达贵显要却在灯红酒绿之中贪婪地吸吮着民脂民膏,怨在心中,叹自己无能如一节无用的木头,无力挽回狂澜。《庄子·人间世》曰:“匠石之齐,见栎社树,曰:‘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榔则速腐,以为器则毁,以为门户则液樠(满),以为柱则蠹,是不才之木也。”邓散木以散木自名,可见他当时的心情有多么的悲伤。
邓散木第三次易名是在63岁后。60岁时,他脚患溃疡出浓,经医院诊断为“血管堵塞症”,必须截肢。左足被刖后,邓散木靠着拐杖渐渐成步。他没有倒下,凭着毅力依旧拿起笔和刀,写诗、书字、治印。此时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他,不断向党,向社会呼喊,自己是爱党、爱人民、爱生活的。他易名“一足”、“夔”。“夔”乃为雷神,只有一条腿而其声如雷霆,其光如明。他曾诗曰:“腿乎腿乎别矣汝勿忧。汝在我命危,汝去我命留。我命留,犹得为社会主义建设备一筹。”那时的邓散木正是激情有余而报国无门。
婚事畸仪
邓散木与张建权是在南离公学相识、相知、相爱的。当时,邓散木任校长,张建权为“文绣班”教员。他们于1926年4月18日结婚。张建权清楚地记得邓散木草拟的结婚请柬,上面工工整整地写道:
××先生:
我们现在定于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在南离公学举行结婚仪式,所有繁文俗礼一概取消,只备茶点,不设酒宴。
到那时请驾临参观指教,并请不要照那可笑而无谓的俗例送什么贺礼;倘蒙先生发表些意见和指导我们如何向社会的进取途径上前趋,那便是我们比较贺礼要感谢到千百万倍的。
你的朋友邓铁张建权鞠躬
张建权曾对我这样说:“我们这样做,无非想一改旧俗,追求些新思想。不料,散木大大的‘闹了一场,使许多人接受不了,但散木那对不良世俗的憎恶和其叛逆的性格却展露无遗。”
张建权的婚事由她的大姐操持,大姐是个旧观念较深的女子,姐夫又是洋行的副经理,十分讲究面子。婚前,大姐一再提出,即使是文明结婚,不设酒席,但接新娘的这一天,至少要来辆披红挂彩的轿车相接,不然,太寒酸太丢面子,让左邻右舍笑话。张建权将此意转告给邓散木,散木听了后也没吭声。婚前两天,邓散木亲自送来从华安公司支借的200元钱,请大姐费心为张建权买点衣服和首饰,至于彩车之事,他说到时候再说。
娶亲之日,张建权妆成之后等候邓散木来车迎亲。上午8时许,汽车喇叭声声,散木一身中山装,独自一人
进门,小车也未披红挂彩。大姐十分生气,诘责邓散木说:“邓先生,今天是什么日子,车上光秃秃的连个喜字也没有,这不存心让人笑话吗?”邓散木接口便说:“文明结婚不必讲究外表。”大姐听后更生气地说:“树要皮,人要脸,你不要脸,我要。”说着拦在门口,不让邓散木接新娘子。邓散木拉起了嗓子说:“这是我结婚,我高兴怎样办就怎样办!”就这样你一句我一言地吵了起来,越吵越烈,几乎到了动手的地步。张建权见势不妙,便劝大姐说“有车便好!”邓散木趁机拉着张建权的手冲出了大门。
婚礼是在南离公学礼堂举行,礼堂内早已挤满了宾客,热闹非凡。墙壁上挂满了红红绿绿各种“家具”、冥通银行的“钞票”和送死人的“长锭”。那些橱、柜、桌椅、马桶、夜壶等全用马粪纸剪成,糊上彩纸,格外惹人注目。这时,还不断有人送“长锭”进来。一位平时关系还可以的牙科医生拎着几串“长锭”,口中不停地嚷道:“邓先生,很对不起,鄙人来晚了一步;张先生,向你祝贺,特送上一点贺礼,望请笑纳。”邓散木高兴地接过“贺礼”,挂上了墙壁。张家随去的客人面对出奇惊人的布置,个个瞠目结舌,不知所云。
这一安排,张建权事先也不知道,也许是气懵了,她昏昏然手足无措。至于结婚这一天仪式到底如何进行,张建权至今回忆不出。
晚上,客人已散,他们也准备进洞房。这时,邓散木父亲定了一桌酒席,托人送到学校。邓散木喜上眉梢,邀来在校老师,将办公桌合拢,摆成酒席,11人尽情痛饮,一醉方休,不知不觉地喝掉了130斤绍兴酒,邓散木夫妇也在醉醺醺中步入了两旁挂有“长锭”的洞房。
婚后几天,有朋友来小坐,谈及婚礼中的摆设,大有不解之感,道“新房门前缘何挂‘长锭,墙上又何贴‘冥钱?”邓散木笑着回答:“我们结婚,果然不能免俗,以送死人的‘长锭、‘冥钱来装饰洞房,聊示吉祥而已。”
交友白蕉
邓散木与白蕉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都有“怪杰”之称,他们对敌切齿痛恨,对友真挚诚恳,“真”藏于“怪”之中,同仁称其“双璧”瑜亮沪上,白蕉曾戏言道:“白蕉摩挲金石,少好刻画,世多俗手,遂长其傲,谓天下无英雄,王天者当我。”一次,经吕梦蕉介绍,他俩在市楼相识,散木进《三长两短斋印存》十余册相赠,白蕉启视,谛读大骇,遽忘进酒,大呼“铭钟鼎,勒燕然,大书深刻期他年,粪翁不死当此肩,我得知音也。”两人遂订莫逆之交。从此,同桌而饮,同榻而眠,亲似手足。白蕉曰:“粪翁素有怪名,予拙无所见。昔者杯水对饮,粪翁席间
亦语予,往颇闻人言白蕉怪,何独不见子怪。”白蕉曾撰文介绍散木时戏言说:“自见粪翁每篆刻,吾不敢再握刀。”粪翁也极赞白蕉书画:“白蕉绝不轻许人,此公专攻二王,见地甚高。”可谓惺惺惜惺惺。
邓散木与白蕉个性脾气相似,常有孤芳自赏、不合时宜之嫌,但有良知,有爱国之心。1937年,上海金山沦陷后,白蕉悲愤交集,诗以寄志:“今日此天地,何人起霸图。干戈争短隙,零落笔封胡。昔下阳朱泪,空期楚幕鸟。我言初已尽,未肯便为奴!”邓散木则刻印自励:“忍死须臾”,边款为“一二八,是奇痛,是奇耻,两昆仑,今安在?忍死须臾,矢誓东海”之白文。两人同心,为抗战募捐奔波,合办“杯水书画展”于大新公司,将展览所得的“杯水车薪”捐与抗日救亡组织,一时轰动沪上。1943年2月,日伪方面拟定他俩及当时另一位“名家”出席中日文化协会并代表华人发言,邓、白接帖,当场撕毁,拒绝出席。此时,日伪方面已发稿登报,难堪之状不言而喻。他们不愿结交权贵,不屑与附庸风雅之辈为伍。记得有一次上海闻人杜月笙做寿时,托人拿来一张精致的百寿图纸,要求白蕉书写寿文,白蕉掷地一旁,不予理睬。杜月笙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无独有偶,有一富商向邓散木求字,声明润格从丰,只要署名不用“粪”字。散木当即拍桌大骂,此人仍喋喋不休,纠缠不清,邓散木一气之下,将他推出门外。散木说:“美名者滔滔天下皆是,奚取于我?我固贫,守灶冷,易名匪石难转。”一席话掷地有声。
1935年底。白蕉与邓散木同游南京并假环球旅社举办邓散木个展。此时,徐悲鸿与张大干等同游黄山而归,见白蕉报载《愿为粪翁标榜者》一文,徐悲鸿即往旅社聚晤。徐、邓均有相见恨晚之感。三个遂同登酒楼,凭借酒力,痛斥国民政府。四座食客闻言胆战心惊,纷纷逃遁。翌日,徐悲鸿书函予邓散木,上写:“日前饱览大作,深以为幸。弟平日对于寻常报章所标榜者,恒多漠然置之,见白蕉文而往,几乎失之交臂,险哉!顷俟友人寄石,便将赴沪再访尊居,以定一切。”
1942年5月8日,白蕉与金学仪假上海邓脱摩饭店举办婚礼,邓散木应邀出席。席间,邓散木送上一大包贺仪,形似元宝,外面贴有红纸,上面写道:“不要立即拆开。”客散礼毕,白蕉夫妇拆开纸包,解了一层又一层,尽二十多层方“水落石出”,乃其一对精心篆治的石章,一方刻“大吉”,一方刻“花好月圆”。夫妻双双喜出望外,视为珍宝,可惜经过十年动乱,两印散落人间,不知去向。至今,白蕉夫人思来仍惜之惋之。
右派风波
解放后,邓散木参加了“上海文联土改工作团”赴绍兴参加土改,前后四十余天。土改回来,邓散木失业在家,有时不得不靠出售旧书旧报刊度日,政府多次为他介绍工作,均被他拒绝。他说:“国家初创,财力有限,让生活比我还困难的人先就业吧。”他曾写信给章士钊,信中提及“尘羹涂饭吾能惯,未费公家薄俸钱”。邓散木积极为里弄工作,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各种运动中。1954年,他作为新成区的人民代表,列席了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聆听了陈毅、潘汉年的报告。
后应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之邀,邓散木一家北上,以饱满的热情研究起简化汉字的书写方案。他向书法造诣很深的孙逸园先生请教小学书法教材的编写经验。其间,他结识了画家马万里。马万里先生能书能画又能治印,徐悲鸿曾评他说“画格清丽”、“书法似明人”、“治印尤高古绝俗”。不久,马万里赴广西就职,画了一串丰硕的紫葡萄给邓散木,祝他事业有成,弟子满室,学识更富。邓散木受托成立了“北京书法研究社”,举办了“时人书法展”和“明清书法展”。陈毅时为国务院副总理,也参观了“明清书法展”,观后,大加赞扬道:“为国家办了一件好事。”邓散木总以为书刻艺术的春天来到了,正欲大展鸿图时,1957年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在收音机旁,邓散木认真收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峰又反复强调说:“只要建议有可取之处,就会采纳,至于态度如何是不会计较的。”出于对党、对人民政府的坚信不疑,邓散木以《书法篆刻是否孤儿》、《救救书法篆刻艺术》为题,向党作了“书面发言”,且又在交心材料中直言不讳地写到
既称“百花齐放”,无香之花应让它畅放。
既称“百家争鸣”,鸦呜也应让它鸣。
“镇反”、“肃反”中有些是被冤枉了的。
新诗内容枯燥,辞面不美,不讲音韵,不耐
咀嚼,不及旧诗。
……
随着整风鸣放的深入,邓散木对整风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不赞成“随便下结论,随便扣右派帽子”。他严肃负责地向组织表明“我不怕戴右派帽子,骨鲠在喉,不得不吐”。很快“北京书法研究社”成了反党组织,邓散木自然也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解释过,申辩过,可得到的却是“态度恶劣”的指责,只得“低头认罪”,虔诚地“挖根”,痛苦地“检查”。他给好友白蕉写了封长信,详细叙述了自己挨批戴帽之经过,并辛酸地叮嘱白蕉“你独眼看世界,说话更要留点神”。他想用自己以沉痛代价换来的教训告诫好友,不要重蹈覆辙。不料,与邓散木同样耿直率真的白蕉在邓散木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同时,也早早成了右派分子。从此,两头受了重伤的猛“豹”,只好乖乖地守在铁笼之中舔舐满身屈辱的血污。
为毛泽东刻印写字
邓散木自60岁被扣上右派帽子后,备受歧视,又加上截肢、伤腕、切胃、癌变,苦不堪言,但他对生活仍充满着信心,凭着坚强的毅力和清明的神志,孜孜地追求着自己的事业。1963年1月9日,66岁的邓散木正式接到摘去右派帽子的通知,泪湿衣襟。他急切地致信好友冯亦代、白蕉、桑弧、唐云,让他们同享快乐。5月1日,他在北京举办“回到人民中间”后获准的第一次、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的书画篆刻展。此时,他已截去一足,癌细胞也扩散至肝脏,他拄着拐杖前去“巡礼”,见观者甚多并不时予以高度肯定,他快慰地笑了。
8月的一天,章士钊的秘书益知先生来到邓散木家,提及毛泽东主席很喜欢篆刻及书法艺术,章老意请散木先生给毛主席治一印及写几幅字。章士钊与邓散木的友情一直可推算到1934年。那时,章士钊在上海法政学院任院长。一天,邓散木办个展,章士钊坐黄包车经过,见展旗上飘着“粪翁”二字,心中纳闷,便招呼车夫停车,径至展厅,看个究竟。不看则已,一看大吃一惊,水平如此之高,出乎意料,他对邓散木说:“你的字里透着一股奇倔之气。愿交朋友。”过了几天,邓散木收到了由益知先生送来的章士钊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诗曰:“粪翁鼻头著何粪?却惹荀令三年香。偶尔龙蛇一挥洒,高堂素壁生奇光。平生论书先人品,汀洲嘉兴斯道强。畸人畸行作畸字,矢溺有道其废庄。”自此以后,章士钊与邓散木诗书不断,交往不绝,成了忘年之交。邓散木的“畸”名也越来越响亮了。当时邓散木正病入膏肓,见章老所托,便一口答应。他硬撑病躯,寻觅金石,裁纸打格,书就篆、楷、隶、草四体毛主席诗词及刻就“毛泽东”一印,托益知先生带给章士钊。印为明黄色,石制立方体,顶部镂空琢双龙。“毛泽东”白文三个线条横不平,竖不直,似欹斜荒疏,然而读来大有“自然天成”、“返淳归朴”之感。印的一侧刻有“一九六三年八月,敬献毛主席,散木缘时六十六”字样。章老见之赞日:“好个龙纽大印,刀力非凡。”这一被称为“文物极品”的印章现已为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收藏陈列。章老对四体毛主席诗词条屏不甚满意,建议散木书写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邓散木竭尽心智,写成四首五律四条屏。其一为篆书,通篇杂有甲骨、金文和竹简的韵味;其二为隶书,含碑刻之味;其三为行书,快马斫阵,一往无前之气概跃然纸上;其四为楷书,凝练老辣,不乏篆刻的金石气。落款“一九六三年第十四周国庆前夕,俚言四首代颂,敬以各体书尘(呈)毛主席匡谬。”章老见之,十分喜欢,不久便呈给了毛主席。
同年9月初,邓散木“脸大肿”,好友冯亦代前来探访。冯老知散木嗜酒,携来“茅台”一瓶,相向对酌。散木不曾忘记,自己右派帽子在身,又遭截肢之痛,冯老不顾受累之嫌,写信给胡愈之替他请命的情景,感激之情涌上心头。面对摘帽的邓散木,病重如此,冯老潸然泪下,心如刀绞……
1963年10月8日5时,邓散木终于休息了,他对篆刻书法艺术的执著追求,在政治上所遭逢的种种苦难;对未来的神往,连同他的灵魂,都在这时终止了,一代大师轰然倒下了。
今年是邓散木诞辰111周年,也是他夫人张建权作古3周年纪念,我谨系小文,聊申缅怀。
责任编辑张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