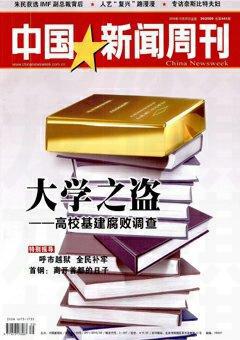白毛女嫁黄世仁的禁忌
长 平
从学术上说,任何禁忌,包括西方人所說的“政治正确”,都是对思想的钳制。人们应该具备是非观念,但是没有什么话题是不可讨论的
白毛女是否应该嫁给黄世仁?这个话题最近成为新闻热点。在年轻人那里,这可能纯粹是一个婚恋八卦,就像翁帆该不该嫁给杨振宁一样。但是在中年人及老年人听来,它首先有一个打破禁忌的感觉。在若干年前,也许有思维特别活跃的人士,在私下里谈论这些话题,但是在课堂及报纸上公开讨论,是难以设想的事情。
中国不仅是一个世俗国家,而且在过往很长时期内宣布“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对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在学术上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在中国人大反封建迷信的年代,它反对有神论的含义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在很多方面,中国社会又具有宗教性质,而且是欧洲宗教改革之前的宗教性质,比如“文革”期间的偶像崇拜,又比如说“神圣”这个词的广泛使用——也许很多人会辩解说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但是众所周知那些被神圣化的东西,其不可侵犯性并不亚于真正的宗教事务。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毛泽东去世了,他享年八十三岁。三年级有一个学生,说了一句“我今年八十三岁”,就遭到一顿暴打。一个正当壮年的男教师,对着这个调皮的小学生拳脚并用,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地乱滚,但是没有任何人同情他,我们都觉得他死有余辜,因为他竟然说自己是毛主席!此前,老师告诉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婴儿大便之后,没有擦屁股的纸,就将已经破损的毛主席画像揉皱了替用,遭人举报,她被抓去枪毙了。我的一个朋友讲过,当时他作为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毛主席逝世的追悼会上,不仅没有和大家一起哭泣,还忍不住笑了,他的妈妈回家后痛哭多日。后来他知道,妈妈哭不仅是害怕别人举报,更是认为她的儿子脑子有毛病,因为毛主席逝世这样的大悲痛,竟然不能让他伤心;不伤心也就罢了,他怎么可以笑呢?
歌舞剧《白毛女》成为舞台明星,然后成为“八个样板戏”之一,变得家喻户晓,正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它和其他“样板戏”一样,是缔造这些世俗神圣性的工具。神圣性这种东西,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工具往往也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当时谁要敢说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后果恐怕仅次于拿毛主席画像给小孩擦屁股。
历史证明,宗教的偶像崇拜未必不可,但世俗的个人崇拜非常危险。同理,宗教的神圣性可以承认,而世俗的神圣化则为虎作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六十年的成败,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这些世俗的禁忌被逐渐打破的过程。尽管执政党主动对个人崇拜进行了否定,但是仍然有很多话题成为政治禁区。
最早的突破是小心翼翼的正面尝试。比如有人说,嫁人要嫁周总理那样的人,因为他长得那么英俊。今天看来这么平常的一句话,当时在报刊上读到,很多人都有一种偷尝禁果的兴奋,因为你居然把普通人的择偶标准和伟人联系在一起。随后,有人开始用疑问的形式,挑战一些神圣主题。我记得从维熙先生有一篇小说,正面描写了犯有叛国罪的人物,我读了之后觉得非常刺激。那个所谓叛国罪,其实是公民没有迁徙自由并且受到迫害之后的潜逃。有人想要投靠帝国主义,这是多么大的罪过啊!乒坛名将何智丽嫁给日本人之后,成为日本选手小山智丽,真的让人难以接受。慢慢地,部分人开始知道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是公民的权利,郎平执教美国队便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
事实上,关于白毛女嫁黄世仁这种话题,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是这种打破禁忌的尝试中最安全的一种方式。今天重新提起,为什么还有偷吃禁果的感觉呢?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有很多禁忌没有打破,还有很多“神圣”的事情,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没有条件的、不容置疑的、只看立场的东西。人们对此怀着宗教徒般的虔诚,如果有人用讨论的口气提到这些事情,立马就会伤害他们的感情,就会被要求闭嘴,甚至呼吁公权力去制止与惩罚。
禁忌是一堵墙,看似阻隔了别人,其实围住了自己。很多人因为禁忌而成为井底之蛙,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举例说,当去年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事件时,有不少中国人打电话给《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说一句“加州要独立”,然后放下电话,猜想美国人如何痛不欲生。事实上,如果加州真的有这个想法,很多美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不会认为这是神圣不可讨论的事情。假如你看到我这个例子,心平气和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那么你是一个讨论者;假如你忍不住非常生气,那么你可能生活在禁忌之中。
从学术上说,任何禁忌,包括西方人所说的“政治正确”,都是对思想的钳制。人们应该具备是非观念,但是没有什么话题是不可讨论的。期待更多的政治禁忌,就像白毛女嫁黄世仁一样,成为生活八卦。★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