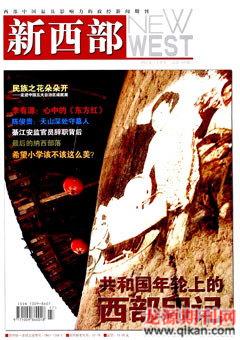一个农民眼中的关中农村60年
陈小玮
陕西合阳农民侯永禄早年读过两年中学,19岁回乡务农。他有一个习惯——写日记,从1940年一直记到2000年,30多个大小不一的本子,累计200多万字。侯永禄的日记记载的虽然只是一个农民家庭生活中的芝麻小事,却涉及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出中国农村60年的巨大变迁。
侯永禄是陕西省合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却写了整整60年的日记。
2006年12月,一本名为《农民日记》的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侯永禄老人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的日记能变成一本书,可他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孙们却觉得这些日记有着特殊的意义。遗憾的是,侯永禄老人已于前一年去世,没能看到儿孙们为他出的书。
侯永禄老人的小儿子侯争胜在西安一家研究院工作,说起父亲的一生和他的日记,侯争胜感慨良多:“一个贫苦农民在艰苦的岁月里,不但没有被生活压垮,还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了自己对国家几十年变化的所思所想。这种坚毅和执着,从一定高度讲,代表了中国农民的崇高境界。”
知识青年回乡务农
“我回到家安心种起了庄稼。”侯永禄在1949年4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
高小毕业的侯永禄,上了一年合阳县办的简易师范学校。后来学校与合阳中学合并,他又在合阳中学断断续续读了一年。淮海战役胜利后,新解放区急需大量干部,侯永禄那一届学生就提前毕业,随军南下参加革命。可侯永禄说服不了他的母亲,只好告别同学,回乡务农。那一年,侯永禄刚满19岁。
“新中国成立了。合阳县的村村乡乡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位于最南端的路井乡格外热闹。除召开大大小小的庆祝会、座谈会,报告会之外,庄稼人用民间‘社火来表达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侯永禄在日记中记下了新中国成立后乡亲们的反应。
这一年,侯永禄家里的地打的粮食虽然不如人家多,却是父亲去世后10年来最多的一年。没有了各种负担,生活便不那么苦了。虽然也给解放军管饭,但管饭后解放军每顿还给1000元(此为第一套人民币的币值,1955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后,1元等于第一套1万元)的伙食费以及四两粮票。起先大家还不信,兑现后大家真的信服了,说解放军不哄人。
1950年冬至1951年春,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无房的农民,分到了房,没地的人,分到了地。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
土改后,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走起路来抬头挺胸,扬眉吐气,高兴起来还会哼上几句眉户戏《梁秋燕》。
有资料显示,土改让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1951年粮食和棉花产量比1950年分别增长8.7%和49%。
1952年春节,侯永禄花了14000元,割了两斤肉待客,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农民收入一增加,粮食够吃且有了剩余。
那时,农民对政府发出的号召都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棉花要增产,侯永禄一家三口一粒粒地选棉种,政府号召防霜,各家就在地头堆好柴草,鸡一叫,枪声一响,城头火光一起,四面八方都是火光,烟罩地面久久不散;政府号召积肥,麦田地头堆的全是肥堆,一家比一家多;政府号召使用新农具,侯永禄从合作社贷款,花了大约三斗麦的价,买了一架五寸步辇,用了两年后入了社。
从互助组到农业社
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政府的号召从来都是一马当先地响应,只有互助组觉得头痛。侯永禄与其他四户组织了一个互助组,但只有两头毛驴和一头乳牛,缺一个能驾辕的牲口。没有牛车,地里的麦子就拉不回来,但组里的人家单家独户又都买不起牲口。侯永禄觉得自己家地最多,就把自家的毛驴卖了。又借了些钱,买了一头牛。但那一年蚜虫成灾,18亩小麦只收了四石,交了公粮后,口粮都成问题。买牛借的债又必须还,他只好卖了堂前地。
如果算经济账,这头牛买得很不划算。时值麦收时节,牛价很高,可互助组里的人家有架子车箱,却没有轮子,靠牛拉麦的想法也没能实现。而且,靠牛碾场又太慢,一天干的活还没有毛驴一晌干的多。最让家人发愁的是,推碾子磨面牛更使唤不上,最后只好又买了一头驴。
1954年,工作组召开互助组组长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建立农业初级社的计划。8月份,侯永禄带头报名入社。他家30亩地,折股21.8股,全社一共1150股,牛评价为200万元,驴65万元。全社一共有75头牲口,总值为10800万元。
成立农业社头一年,土地和劳力按1:1比例进行分配,侯永禄家的土地股分了227元,两个劳力分了234元,与自耕比并不少。入社不吃亏,于是,号召扩社时,没入社的农户就积极响应了。
1956年春节,侯永禄在自家门口贴上了这样一幅对联:“扩了社大闹增产争取早转高级社,百家地连成一片准备就使拖拉机。”横批是“越有雄心”。
1956年4月,8个初级社合并为高级社。高级社的分配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按劳分配,土地不再参与分配,这样一来,像侯永禄这样劳力少的家庭,收入和上年比就明显降低了。、
饲养员不论天晴下雨,每天都有工分,一下子就有钱了,每月收入70元,抵得上两个外出当干部的工资。劳力不少积极参加劳动的社员,收入也不低。侯永禄是社里的会计,工分只能按中等劳力计算,母亲年届花甲,在家做饭带孙子,不参加劳动,妻子菊兰参加劳动,但碰上雨天就挣不着工分。一家六口人,靠两个人的工分养活,难有余钱。
这时,正好队长想把幼畜与大牲口分开饲养,侯永禄家里有地方,就承担起牛犊的饲养工作。这样一年下来,多挣了几百个工分。虽然这一年天旱,小麦亩产只有218斤,棉花亩产52斤,一个劳动日作价只有1.66元,但侯家的现金收入并不比前一年少。
一分到钱,侯永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辆自行车。尽管供销社进了一大批自行车,但不几天就卖完了,供不应求。当时有三种牌子的自行车,有一个顺口溜评价道:“‘永久结实‘飞鸽利,骑上‘白山太生气”。侯永禄不想求人,就买了一辆“白山”。
这辆自行车几乎成了侯永禄的专车,他去县上开会再没走过路。妻子菊兰后来也学会骑车了,但总是没车可骑。
公社化的疑问
1858年是一个跃进年,这年2月,高级社的干部到区上开会,传达省上召开的大跃进誓师大会的精神。主要精神是要突破常规,大干快上!要大修水利,要大办农业,要大炼钢鐵,要把旱地变成水浇地。这次大会一直开到晚上才散。
各大队开始大搞工业集资,收集社员家里的废铜烂铁。侯永禄把家里的一斤半铜麻钱、旧铁辕以及父亲当铁匠时
用的大锤等工具都支援了出去。
8月份,路井乡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包括12个高级社以及两个乡。用侯永禄日记中的话说,“真是‘一大二公的大摊子”。
两个月后,公社宣布:从下月起,社员工分只作为发工资的参考,实际工资按劳力级别发,劳力级别的衡量标准有5项:政治思想,体力强弱,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参照底分。工资分为基础工资和奖励两部分。
11月,全公社宣布吃饭不要钱。“我十分惊奇!难道真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为了定额记工,为了包工,保产,包投资的‘三包,不知道熬了多少透天亮干的工作真的就不需要了吗?吃饭不要钱,食堂也就不要馍票,菜票了吧?财会人员也就轻松多了。”侯永禄在日记中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不过,不记工分的弊端很快显现出来,哪里有活哪里干,队与队之间可以互相支援,不讲报酬。表面看干劲冲天,但劳动效果并不大。几十个人拉一个大胶轮车送肥,有人跑得慢,落在车后头,使不上劲。到食堂吃饭,倒是吃了一碗又一碗,形成“干活磨洋工,吃饭放卫星”的现象。大多数人出勤不出力,甚至出现“病人多、孕妇多、产妇多”的“三多”现象,特别是像出圈、铡草这样的累活,重活没人爱干。
大跃进修的水利工程,能派上用场的不多。老八沟水库的闸门,一次暴雨就被冲垮了,从未蓄过水。意外的好处是,洪水漫过后,改良了土壤,利于耕作;凤凰岭水库上上下下长满了荒草,从没蓄过水;打了很多水窖,也没水,却有晚上或雨天路滑掉进去的危险,后来就被社员悄悄填了。
饥饿的日子
1960年的统购政策,是购买余粮的90%到95%。但这一年大旱120多天,小麦亩产和上年的206斤比,减产70多斤,粮食显得很紧张。
1960年11月21日,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陈书记在公社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传达了上级精神,要自力更生,不向上要,用“核压挖清节”来解决困难……今后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安排后8个月的粮食标准的思路是。三低、二平、三提高,最低15斤,最高18斤。……口粮标准一压再压。七口人一月只有110斤口粮,每人平均不到16斤,每顿饭每人吃不到2两粮。”
从食堂里打回来的饭,不过是稀饭糊糊。每次大女儿西玲吃完饭,总会低声长叹一口气:“唉!”不知是没吃饱,还是喝撑着了,3个大人只是红着眼圈,没人敢问。
怀着身孕的菊兰,只好趁阴雨天没活时提上笼到地里拾豆角,不论绿的,黑的都拾回家,煮给孩子们充饥。后来,菊兰又到处挖野菜,风雨不避,落下了湿疹的病根。她甚至还偷偷跟上一些妇女晚上去掐喂牲口的苜蓿,掐不到苜蓿时,就偷偷到地里掐些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
侯永禄在日记里写着这样一句话“难道真的要往死里饿吗?”
1960年是解放后最困难的一年,这一年的12月又是最困难的一月。队里将晒干的红薯叶分给社员当粮吃。为了充饥,大家把红薯根、红薯蔓都刨来吃。周围村里村外的榆树皮也被人剥光吃了。
最困难的时候,菊兰又生了孩子。侯永禄的岳母提着一笼麸子馍来看女儿。自夏收后,岳母一直在没耕过的麦茬地里拾麦穗,这才救了菊兰娘俩的命。
1961年春节,物价尤其贵,一张红纸2元,一斤萝卜5角,一个蒸馍1元,侯永禄什么也没买,空手回了家。这一年,饥饿的社员们连拜年的兴趣都没有,春节过得冷冷清清。
“1961年,队上开始给社员分自留地。集市贸易开放后,虽然不许黑市买卖粮棉,但管得不是特别严,菊兰就把自己织的布拿到集上卖。菊兰织布手艺好,6丈布卖了84元,这才解决了一家人的吃饭问题。
这一年贯彻《六十条》,路井公社分为3个公社,路井大队也一分为三。收入分配上也有了一些变化。小队三包超产,队里开荒以及自留地产的粮食,小队进行分配,副业收入也归小队分配。为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超产的30%奖励成粮食,其中80%按劳动工分奖给社员,20%按供给分配。
社员捡的麦穗也可自食自用。七,八天的时间,菊兰捡的麦穗磨了三、四十斤面,填补了口粮的不足。
这时,也允许社员下灶了,绝大多数人拍手称快,办了3年的食堂,解散了。尽管政策上是坚持自愿,但干部没有一个人愿意办下去,炊事员也没有一个人想干下去。
1961年,口粮标准依然没有提高,路一大队的粮食亩产是入社来最低的一年小麦亩产只有132斤。前一年亩产200多斤,都出现饿死人的情况,这一年该咋办呀?
放了暑假,孩子们去捡瓜皮,回来后把瓜皮洗干净,用刀切成条晒干,以备冬天食用。自己开伙做饭,就需要燃料,队里分的麦草,棉秆不够用,孩子就去捡煤渣。运气好的时候,一次能捡七,八斤。有一次,5岁的小儿子争胜和妈妈去看外婆,走到村口就不走了。他看见村口倒煤灰的地方,有不少煤渣,就蹲下捡,没地方放,就把煤渣放进衣服兜里。
孩子们捡煤渣的日子持续了10多年。
侯永禄也时常要骑着自行车从澄县煤矿往家带炭。100斤炭只需花五,六毛钱,但耍上坡翻沟,清早出去,赶天黑也回不到家。为了买炭,侯永禄骑车时摔过一跤,缝了43针。
基本核算单位转移到小队后,社员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队长再也不发愁活没人干了,反过来倒是社员怕没活干,挣不到工分。
1962年春节,侯永禄写的对联更像是给自己鼓劲儿:“吃糠咽菜咬紧牙稳渡难关,推碾拉磨挣断绳誓夺丰收。”横批是“苦尽甜来”。这一年,侯家自留地产小麦230斤,红薯1000多斤,加上生产队分的,全家人可以不用挨饿了。
“胡来”的“文革”
1963年,小女儿引玲考上中学没有上,回家劳动了。多了一个劳力,年底决算时分到了80元现金。
为多挣工分,菊兰月子里选棉种,两瓮棉种挣了几百工分,队上挑粪,别人嫌脏不干,侯永禄主动要求干;引玲回家干农活,看拉架子车挣的工分多,就每次都抢着要拉车。
1965年,夏粮丰收,秋粮、棉花也丰收,家里三个劳力,收入多了,分了368.99元的现金。全家一致决定买一台缝纫机。过去手工做衣服,一件布衫就要花两天的时间,菊兰太辛苦了。这一年年底,侯永禄买了一台上海产的飞入牌缝纫机。
就在这个时候,“文革”开始了。
村里一下子大变样,成了红卫兵的世界。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排成队,听红卫兵指挥着跑步。哪个跑得稍慢,就被鞭子抽。这些“四类分子”头上带着高帽子,帽子上写藿名字,名字上被打著红叉,脖子上挂着本来应该挂在牲口脖子上的铃铛。侯永禄记录了当时的心情:“有些心跳,……这不是胡来吗?”
有一次,批判大会组织全体党员去
田间参观范家洼大队的棉花秋田作物长势情况,半路上却碰见一伙打着红旗的青年人,他们抓住郭家坡的一个党员,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乱抓乱打一阵,并给他脸上抹上黑墨。那人被打得鲜血直流,却无人敢上去拦挡。
红卫兵开始破四旧了,年轻人把自己没见过的首饰,摆设、衣服都叫四旧,认为拜年,庆寿、敬神、祭祖统统是四旧,有的地方连房子上的脊兽都当四旧给砸了。春节拜年也不许拿花馍。
侯永禄读中学的大儿子胜天和同学步行去北京,但毛主席接见了八次红卫兵后就不再接见了,胜天终没能实现亲眼看到毛主席的愿望。两年后,他从学校领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算是毕了业。
1972年,社员劳动一天,10分工最高的只值0.41元,低的只有0.25元,全年每人口粮高的是31.3斤,低的是230斤。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改革开放前夕。
“最好还是大包干”
1978年,是一个转折年。
这一年,侯永禄家里出了两个大学生。二儿子从部队考上了张掖师范,三儿子考到了延安大学。小儿子争胜虽然距中专录取线差了半分,但却上了县重点高中合阳中学。
1982年7月,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讨论实行哪一种形式的承包制,经过表决,绝大多数人同意大包干。
队上采用抓阄的办法分了牲口、农具和责任田。侯永禄运气不好,只分到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锨和一个刮板,外加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
侯永禄在日记里写道:“1954年入社时,自家的地是27亩,同时还有一头牛和一头驴,外加饲料种子。但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分田到户后,侯永禄就买了一个架子车车厢。“50多岁的人了。还准备为自己的家大干一场。”侯永禄写道。
1985年春天,侯永禄在自家院子里新盖了10间瓦房,女儿引玲家以998元买回全家第一台黄河牌14寸彩电。侯永禄高兴地写道:“公社吃了大锅饭,多年粮食难过关。各种办法都试遍,最好还是大包干。”
晚上,电视里演《济公》,村上很多人都来侯永禄家里看。房里挤不下,侯永禄干脆把电视机搬到房门口,让大家在院子里看。白天演《西游记》,侯永禄怕光线太强,看不清楚,便在房门前用帐子和凉席搭起了凉棚。远处的人站在太阳底下,热得不行,侯永禄便将凉棚再扩大,席不够用,连新凉席也搭上了。小凳子不够坐,他又拉出长凳子、椅子、门槛、木板,饭桌,连石墩,砖头都用上了。人多时竟有百余人。
种地开始赚钱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农民开始有了种种烦恼。
别人种粮食时,侯永禄的女儿西玲却大胆地种上了甜萝卜。当年收获1万斤,以2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合阳糖厂,收入200元,长这么大,她第一次见这么多的钱。
1990年,西玲家开始种西瓜,几亩西瓜就收入960元,还不耽误种麦,很划算。第二年,村民们跟风大量种植西瓜,可恰逢南方遇洪灾,交通受阻,瓜价一个月内由1角4分降到4分。到8月份,有人开着四轮车收瓜,满满一车才30元,实在卖不掉的瓜,就被埋在了地里。那一年,西玲家的瓜也只收回了成本,没有赚到钱。
种地种伤了。西玲投资4250元开始办面粉厂。加工100斤粮食1元2角,剥皮每百斤2角。但好景不长,别人买了更先进的磨面机,磨的面质量好,加工费还低。尽管西玲也把加工费降了,但来的人还是越来越少,她只好以卖废铁的价格,卖掉了机器。
最让侯永禄难以承受的还是农林特产税的征收。
1999年11月19日,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1999年的农林特产税任务特别高,今天西玲过来说,村上来收苹果税的人蛮不讲理,要把她的缝纫机抬走,幸亏有人帮着拦挡,才又抬了回来。
“为了一个苹果税,弄得人心惶惶。”收苹果税的乡干部要把侯兴才家的电视机抬走,他只好交了250元的税款外加100元的罚款才保住了电视机:侯振山家的四轮车被押到了镇上,侯四易家的粮食被装走了几麻袋,王新吾家槽上的大乳牛被牵走了……
这一年,西玲家的苹果总共卖了4000元,缴了900元的税。收税的人到地里大致看一眼,说缴多少钱就缴多少钱。“减去成本,往地里投入那么多劳力和钱,到最后还是贴钱”。这让终年在土地上劳作的西玲异常沮丧。
2004年年初,陕西省宣布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取消除烟叶外的农林特产税,改征农业税。村里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2005年,依靠棉花收入,村里基本普及了万元户。
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村民“种地开始赚钱,过上了好日子”。
后来国家对种粮进行补贴。第一次直补,每亩补5元,钱不多,但还是让在家务农的西玲激动了一个晚上。她遗憾地说:“如果爸爸还在,日记里又会有‘快乐,‘激动、‘满意的字样吧。”
侯永禄老人是2005年去世的,在此前后,他的儿孙们一直努力着想将他的日记整理出版,特别是他最疼爱的长孙侯亮,为了此事在北京各个出版社来回奔波了几年,直到2006年年底才如愿以偿。
如今,侯永禄老人的儿孙们又在努力将他一生的故事搬上银幕。读导演专业研究生毕业的侯亮写好剧本后,已交给著名導演吴天明拍摄。侯亮说,他想用这部电影向建国60周年献礼。
(本文图片由侯永禄儿子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