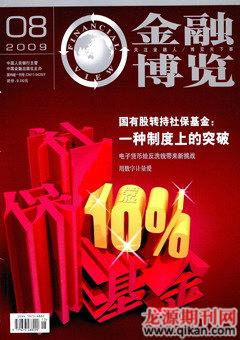明清货币商人及国际金融市场
孔祥毅
明清中国金融革命中的货币商人,不仅仅活跃于国内,也大胆地参与国际市场,与外国商人进行金融业务往来:支持对外商品出口,经营熔炼贸易白银;在国外采购国家铸造制钱的生铜,补充国内货币供应:对外商直接进行贸易融资;与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抗争合作;走出国门开设金融机构,办理国际汇兑与借贷,服务海外华商与侨眷,等等。总的考察,明清货币商人及其金融活动,已经介入国际金融市场,但遗憾的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却因国内外金融环境的改变而在强势发展中迅速衰落。
支持出口商品和输入白银
从明中期到鸦片战争前,中国通过贸易从世界吸收的白银约为51560万两,合19334多吨。1821年至1850年,仅晋商经陆路向俄输出商品,每年就在800万卢布上下,而俄国对华贸易的差额用粗制的白银工艺品来支付,晋商将其熔炼改铸成银元宝,投入国内市场。17-18世纪,中国商人在外贸中吸收了大量西班牙,墨西哥银元,也补充了国内白银货币。日本学者田久川说:“清商多买日本铜及金银,一些商人还成为内务府所辖的贩铜官商。1648~1708年的60年间,日本金外流约240万两,银约37万贯;1662~1708年的46年问,铜外流约11450万斤。”确实如此,从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开始,晋商每年两次用大型帆船从长江口出海,乘季风开往日本长崎,先后七八十年,为国家购进生铜约21000万斤,补充了中国铸造铜制钱的铜源。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认为,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白银数量比从太平洋上运来的美洲白银多3倍到10倍;由英国输入中国的白银约有5110万两?由欧洲其他国家输入的白银约有3853万两;美国在1805~1840年间向中国输送的白银约有6148万两;除了以上国家外,西班牙以菲律宾的马尼拉为中介,用美洲白银交换中国商品,1700~1840年间,从这一渠道输入中国的白银约为9360万两。这些货币关系的展开和白银、铜甚至黄金的净流入,说明了中国商业革命对金融货币极大的吸纳能力,同时也说明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融合所产生的向外扩张的巨大能量。
其实,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简单,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一次给其广州大班的信件中写道,“我们完全没有能力为你们提供下一季度购货所需资金的最小帮助”,不过这种窘迫的局面不久就有了缓解。东印度公司开始默许港脚商和英国散商将印度的原棉和鸦片运到中国销售,再用他们换回的白银来支付英国从中国购入丝,茶的货款。于是在中,英,印之间产生了一个循环贸易;中国向英国出口丝,茶,英国向印度出口棉织品,印度向中国出口原棉和鸦片。但这个循环贸易是单向的,因为中国不需要英国的棉制品,英国也不需要来自印度的鸦片,印度几乎不买中国的茶叶。为了维持这种单向的贸易循环,汇票的使用便成为必需的了,即出现了中国汇往印度:印度汇往英国、英国汇往中国的“循环汇兑”的结算办法。美国以伦敦签发的汇票来结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始于19世纪20年代。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商社,以美国对英国出口棉花而拥有的债权为基础,签发由伦敦兑付的汇票来结清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从这时起,在“中、英、印”三角循环汇兑关系之外,又出现了同样以伦敦汇票为中心的“中,英、美”三角循环汇兑关系。
中国商人在对俄罗斯和外蒙古的商品交易中,还提供贸易融资。如总号设在外蒙古科布多的晋商大盛魁印票庄,像东印度公司一样,利用清政府颁发的“龙票”(一种营业特许证)特权,垄断部分对外贸易,并以他们的借据“印票”为据进行高利融资。在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科亦有中国货币商人的金融机构,如恒隆光、独慎玉,成元汇等。
弗兰克说,“中国人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亚洲在1750年之前很久的世界经济中就已经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欧洲黯然失色。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弗兰克认为,15~18世纪末,是亚洲的时代。尤其是中国与印度,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的中心。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可以肯定地说,明中叶到19世纪中期,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产出的头号大国,国民生产总值居全球之前列,是国际贸易的强国。商品的出超,白银的大量涌入,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金融活动的中心。
与外资金融的斗争和合作
16~19世纪上半期,商业革命引发金融革命,中国由“农业金融”过渡到“商业金融”。而领先一步的欧洲工业革命,使工业国家的金融网络开始伸向中国,不仅外国银元流入中国,而且铜币、纸币和银行也进入了中国国内市场。
外国银元的流入,最初是西班牙元(又称本洋),因其“计枚核值”,流通方便,几乎成为一些地区的标准货币,先闽,广地区,继而向北扩展,道光年间“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供不应求,本洋对纹银升水达10%~15%。1 9世纪50~70年代,墨西哥“鹰洋”取代了“本洋”的地位。后来,美国羡其厚利,仿制了一种贸易银元出口远东,接着是日本银元、西贡银元,香港银元、印度卢比银元,都成为“鹰洋”的劲敌。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后,排挤中国纹银,银元开水,引起大量纹银出口换取银元,并再度流入中国市场。道光皇帝1829年曾下令禁止,但实际上禁而不止,各处仿造蜂起。光绪年间,自铸银元以维护利权的呼声越来越紧,清政府在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允许两广总督张之洞设厂试铸银元,直到1910年(清宣统二年),才出台了统一成色为千分之九百,重量为七钱二分的规定。
大量外国银元流入的同时,还有一些外国铜元也流入中国市场,国人称其为“夷钱”,主要是越南和日本铜钱。日本宽永通宝多从宁波,上海,乍浦等港口贩入,越南光中、景盛,嘉隆、景兴通宝,景兴巨宝,大宝等在缺少制钱的闽、广地区大量流通,广东潮、汕,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尤甚,“掺杂行使,十居六七”。清末,光中、景兴等钱至少流通于闽、广、台、鲁以及北京附近乡村和四川重庆。
外国纸币的流入是在19世纪70年代至清末,其中包括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和外国银行在境外发行的纸币,有的用中国货币单位,有的用外国货币单位。英钞使用地域最广、日钞、俄钞、法钞、德钞次之。
19世纪初,英资保险公司首先进入中国,到1858年,已有5家外资银
行在中国的香港,广州、上海等城市设立分支行13个,清一色的英国资本。当时,上海钱庄使用的庄票,已取得外商的信任与欢迎,特别是经营茶叶的外商,他们认为“钱庄期票与现钱一样,无论在购货或还账上,均可流通无阻”。随着上海设立“租界”,“商贾云集,贸迁有无,咸恃钱业为灌输”,中外金融机构同时发展,尚未发现太多的矛盾。
19世纪60年代,是外国银行来华设行的第二个高潮。首先是法国银行插了进来,英商银行又来了几家,英商汇丰银行干脆将其总行设到了中国的香港,并且发行货币,扩张业务,迅速形成垄断地位。彼时苏伊士运河的开辟、无线电通讯的发展,大大缩短了中西贸易的周转时间,改变了信息和资金转移的方式。
19世纪90年代,德、日、俄、法、美等国银行相继来华,出现了外国银行第三次来华设行高潮,彻底打破了英国的垄断,中国金融基础被西方列强控制。明清以来的中国货币商人的金融机构,业务、利润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侵蚀。一向谨慎的山西票号看到沿海城市分号不能盈利,逐渐收缩回撤,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货币商人的钱庄,遇到强势外资银行。也不得不调整战略,本来它们的资本金都不太多,常常依靠向票号和外商银行融资才能正常开展业务,此时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外商,有的甚至干脆充当外商的买办。此时,票号,钱庄中落,而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自办的几家新式银行立足未稳,仍不可能支撑中国的金融体系,必然演变出半殖民地金融的特征。当时,中国的外贸更多地被控制在驻华外商手中,出口商品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几乎取决于伦敦市场的国际价格,使中国外贸商人变成了猜测银价涨落的投机者。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欧亚贸易的欧洲先锋英国,始终在考虑对亚洲贸易白银出超问题,于是在英国占领孟加拉之后,大肆在当地种植罂粟转销中国,用鸦片贸易逆转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态势,中国开始了白银外流的历史。从此,全球金融格局改变,那些取自美洲的白银经由东亚重又回流到伦敦,进而回流到美国。鸦片贸易引发的白银危机瓦解了中国的货币体系,也改变了国际金融货币的格局,中国丧失金融大国的地位,改写了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重视近代以来中国金融环境的逐步恶化。外商企业与外国银行的进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经营带来一定的示范作用,但是资本的运作,毕竟须臾不会离开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它们操纵股票投机和资本运作,1867年上海金融风潮,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等等,其背后无不受制于外资。例如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其原因不仅有胡雪岩联合国内丝商与美国为首的国际丝商竞价斗争失败,同时还有上海怡和洋行受香港怡和洋行指使,操纵开平煤矿股票,将其从1两白银一股拉到19两白银一股,然后全数抛出,使其跟进者顿时破产,波及钱庄,上海78家钱庄倒闭68家。风暴继而波及汉口、天津、宁波,杭州甚至僻处东南的福州和远在华北的北京。更重要的是政府对外政策的失误,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及战后的不平等条约,战争赔款,被迫举借大笔外债,让外资银行实际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恶劣的金融环境扼杀了明清中国金融革命的成果。
票号在海外的收缩
明清金融革命中的货币商人,资本雄厚者多在海外设立众多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也随着时局的变化跌宕起伏。在此,仅列举合盛元票号以观其一二。
1 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日本侵占我东北营口等地,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业务停顿,濒临倒闭。总号东家郭嵘与大掌柜贺洪,大胆启用了18岁的申树楷为营口分号掌柜。申树楷来到营口后,一边接管业务,一边调查研究,发现合盛元营口票号存款,历来以官款为大宗,放款主要是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家。当时营口人心惶惶。存者纷纷提取,贷者无法收回,人心浮动,再无大宗汇兑业务;各钱庄,票号对随之而来的日商心怀敌意,不愿交往。而日商对中国商民更怀有戒备,票号业务无法开展。申树楷鉴于日俄战争后很多日本人来到东北,看中东北大豆,豆油,豆饼,而中国人很喜欢日本的火柴、海味,杂货,便主动找机会,亲自与日商打交道,找到一个比较可靠的日本人,大胆地突破晋商只用山西人的几百年老规矩,雇用这位日本人为合盛元的“跑街”,向日商招揽生意。这一招不仅基本解决了双方的疑虑,而且也解决了翻译问题,业务局面很快打开。就这样,合盛元营口分号起死回生。
稳住营口以后,申树楷把视线移向东北全境以及鸭绿江彼岸之朝鲜,1898年在朝鲜新义州设立代办所,1900年改为支号,并增设南奎山支号。合盛元票号东家和大掌柜看到申树楷的成功十分欢喜,遂想到英商汇丰银行、日商横滨正金银行等不断进入中国,为什么不把票号设往东洋和南洋?更何况我国在东西洋及南洋群岛从事工商业的华人为数众多,留学欧日的学生也不下万人,海外华商侨民汇兑,悉由外国银行搡办。利源外流,中国商务大受其困。总号便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派申树楷率伙友携巨款乘风破浪赶赴日本神户,几经周折,终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在神户建起了中国在日本的第一家银行“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申树楷然后马不停蹄、穿梭于横滨、东京、大阪等处,筹划设立合盛元的出张所,几经周折,于同年冬季,合盛元票号在东京,大阪、横滨等几处出张所先后开张。合盛元除汇兑中国出使人员经费及官生留学费用等款项外,同时为目商办理商业汇兑。清廷王公大臣亦盛赞合盛元票号“开中国资本家竞争实业之先声,亟应优予提倡”。1907~1909年三年间,合盛元票号东京支店的现金出入额增加了6倍,1808年的存款总额达到4106047日元,超过了汇丰银行长崎支店的存款。
正当合盛元在日本站稳脚跟,蓄势发展,拟将海外银行推及西洋,南洋各埠之时,辛亥革命爆发,军阀混战,票号被掠,损失惨重,政府存款逼提,贷款无人归还,票号根基动摇,各地蜂拥挤兑,在股东无限责任制下,数十家票号无一逃脱破产的厄运,合盛元票号不得不宣告歇业,撤离日本和朝鲜。
服务华商与侨眷的侨批业
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向东南亚的移民,到16世纪时规模逐渐扩大,19世纪后期形成高潮。移居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与原籍侨眷通过汇款和信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此形成了为华商和侨民解送信款的跨国金融业务,称为“侨批业”(其具体名称各地不一,有“信局”,“批信局”,“侨信局”、“汇兑信局”,“华侨民信局”、“批馆”、“侨批馆”、“汇兑庄”、“侨汇庄”,等等)。
侨批业最初于19世纪中后期始于福建、广东和香港地区,后逐渐发展成为专为东南亚华商与侨眷解送信款
的兼有金融与邮政双重功能的民间经济组织。据记载,19世纪80年代,国内已有此类机构21家,其中厦门有8家,汕头12家,新加坡有49家。这些侨批业的投资人,潮州商34家,福建商12家,其他3家。20世纪初日商台湾银行调查课调查,在东南亚的新加坡,槟城、巴达维亚、万隆,日惹,梭罗、三宝垅、井里汶,马尼拉,曼谷,西贡、仰光等地已有侨批局400余家,中国国内厦门有70多家,汕头有80余家,广东等其他地方十多家,例如“郭有品天一汇兑银信局”(简称天总局),由旅居菲律宾华侨郭有品于1888年在其家乡福建龙溪县流传社(今龙海市角美镇流传村)创办,1892年扩大为四个局,总局设在流传社,厦门,安海(晋江)、吕宋(菲律宾)为分局。专为海内外华侨和侨属办理书信投递和钱币汇兑接送等服务,由于其注重信誉、管理严格、赢得了海内外侨民侨眷的信赖,业务日渐拓展,至清末分局达28家: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暹罗(泰国)、安南(越南)、新加坡、缅甸七个国家有21个分局,国内有厦门、安海、香港、漳州、浮宫、泉州、同安等7个分局。鼎盛时期年侨汇额达千万银元。
侨批业的发展源于沿海移民,1840~1910年,经厦门出国的移民为257万,回国移民152万;1871~1910年间汇款约34328万元,平均每年约858万元。它们寄回原籍的汇款以厦门为集散地,再经由厦门转入内地侨乡,构成了厦门及其周围地区商业和金融业的支柱。1914年,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发现侨批业的巨大利源,曾一度自设侨批局,与之竞争,受到其他侨批局的反对和抵制。厦门侨批局的同业组织——厦门市银信业同业公会——也致函厦门市商会,呼吁取消银行附设的侨批局,后经双方协商,达成谅解,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扩展海外金融业务。中国银行与侨批局建立合作关系后,业务有了一定进展,不过,1936年与1932年相比,汇款仅提升了28个百分点,环南中国海的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市场,仍然是侨批局的天下。
侨批业为什么发展迅速,就连专门从事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都无法与之竞争?因为华商与侨民汇款,百元以上者均由各银行用票汇交于收汇入持票来领;而散处乡间的零星小额汇款,不仅地域分散,而且收款人多不识字,不明汇款手续,向由信局用信汇办理,直接派信差连信带款送收款人家中,此项零星信汇占全部汇款的绝大部分,汇费每百元仅1~2元。南洋各地信局约300余家,委托厦门各信局约60余家转交解付,厦门各信局再委托福州、泉州,漳州各县区信局代为转解。南洋信局为收汇机关,厦门信局为媒介转解机关,各地信局为送达机关,此项送款信差有当地乡长和铺保作保,历来信用可靠,绝少舞弊,并能够为收款人代写回信,收款人仅付一二角钱代书费或脚力,为乡人所欢迎,信差收入颇佳,故多自重,地方官亦极力保护,为其地方税收一源。
可见,侨批业的发展,既有组织与经营网络化的制度优势,又有服务乡土性的特点,成为东南沿海金融业的一大特色。
——日升昌留给后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