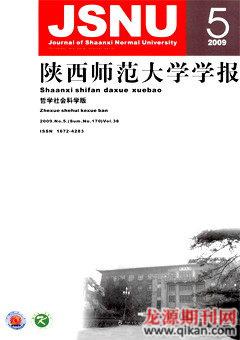论陕西作家的地缘情结与审美方式
赵德利
摘要:黄土情结是陕西乡土地界所独有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它包括了由地理环境而生的地缘、经济、政治和人际乡情等多种文化“原型”。陕西作家的文学创作源于这种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地缘情结,并因此而形成三种主要的审美方式:以善与美的冲突为基质的审美方式,注重展示传统伦理与个性欲望的冲突,表现时代背景下的血亲伦理冲突的悲剧意义;写今贯古的双层意蕴结构审美方式,既通过表层描写反映特定时代的民众生活,又在文本深层意蕴结构中寄寓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史今同构”的双层审美效应;文化批判为主导的审美方式,揭示与批判了民族民间文化传统中有悖人性人伦的丑陋行为与阴暗心理,具有文化的批判性和审美的现代性。
关键词:陕西作家;地缘情结;审美方式
中图分类号:I209.9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5-0069-08
陕西作家具有独特的地缘情结与审美方式。20世纪80-90年代,陕西作家因描绘黄土地上生存的农民的创作实绩而在中国文坛独领风骚。他们的创作风格不同于京津沪等城市作家,也与其他乡土作家有明显区别。研究他们的生活与创作,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义的价值坐标,那就是陕西作家的创作源于地缘情结,得益于民间文化的借鉴、创化和现代审美文化的透视与建构。他们由此而形成的文学审美方式,形式多样范式不同,又同出于地缘情结。地缘情结好似陕西作家的根,积淀深厚,影响深远。因农本而促生的写实文学观,因帝都文化培育的文学使命观,因内陆闭守促生的文化保守观,都在陕西作家的创作中构成独异品格。而地缘情结的“得”与“失”也是陕西文学兴盛和衰落的根由。
一、黄土情结: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
从整体上观照,陕西作家以书写“乡土”文学著称于文坛。陕西作家对土地和农民的关照源于他们的地缘情结——黄土情结。黄土情结是他们创作素材和思想认识的心理源泉,是他们为之欢笑,为之悲泣的黄土地人的命根。他们正是从对黄土情结的内视即生活文化体验中抓住了黄土地的精魂才成为“作家”的。源于黄土,抒写黄土地人,最终又要命归黄土,这是他们的共识。他们认为,黄土地上的历史、文化和农民才是他们写作追寻的根本,才是酿就伟大作品的土壤。陈忠实曾坦言:“我出生于一个世代农耕的农民家庭。进入社会后,我一直在农村工作。这样的生活阅历铸就了我的创作必然归属于农村题材。我自觉至今仍然从属于这个世界。我能把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感受诉诸文字,再回传给这个世界,自以为是十分荣幸的事。”正是基于‘这样的生活认识和审美理想,陕西作家才创作了影响很大的反映黄土地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平凡的世界》、《浮躁》、《白鹿原》、《八里情仇》、《最后一个匈奴》、《热爱命运》、《水葬》、《最后那个父亲》、《狼坝》、《高老庄》、《羊想云彩》等。
情结,照荣格的解释,是指个人无意识中聚结的一簇心理意识丛,或是富于情绪色彩的一连串的观念与思想。情结的产生与形成不仅仅与个体曾经意识但又因遗忘或抑制而潜入无意识中的内容相关,而且还与生理遗传的集体无意识相连。本文所谓“黄土情结”即指世代生存在陕西“黄土地”上的人们,基于相对封闭而又十分优越的地理条件与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心理印象丛。它首先是世代居于黄土地上的人们进行物质劳动并由此形成的精神活动在心里留下的印迹,即心理“原型”。这种原型并非人人可以用意识来拥有和再现,而是具有某种可以开启沟通的先天倾向和潜在可能性,只有沉浸于先天经验的“环境”条件(即后天类似的经验)中,才可能启唤出来。其次是通过祖先的言行继承下来的经验与规范,并同现代人新的生存活动经验沉淀融合成的一连串的思想与观念,即情结。例如,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规范内容与共产主义的斗争经验因相近似而同构,成为陕北人(扩而言之则为陕西人和中国人)的一簇心理意识丛。因此,黄土情结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原始性心理内涵,而是随时代变迁和社会实践而不断继承发展的心理意识丛。它上承远古人类的生存活动的心理印迹,下接传统文化与当代生产斗争的种种经验,是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心理情结。
情结对于个人行为来说,具有极大的制导力。它往往使人根据情结的力量选择行为对象,抑制意识的活动。就像荣格所说:“不是人支配情结,而是情结支配着人。”尽管情结的作用常常有负面效应的一面,但是,它同时又往往就是灵感和动力的源泉,对于个人事业取得成就具有重要推动力。陕西作家生活在经济落后的黄土地上,却又写出了具有博大精深的历史感的佳作,就是明证。
黄土情结是陕西乡土地界所独有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它至少包容了由地理环境而生的地缘、经济、政治和人际乡情等多种文化“原型”。陕西的地理位置居中国中心,亦是黄河流域文化的中心。如果说长江流域文化圈的人们因地势落差大,水量丰富湍急而具有浪漫灵活、善于幻想富于开拓精神的话,那么,黄河流域的民众则因黄河的裹挟流淌的滞缓、凝重,而具有勤劳朴实、偏内向、重实际的特点。而陕西人则又因北依长城与沙漠封固,东有黄河潼关阻隔,南架巴山天堑,西望祁连山脉而独成“王国”。陕西(尤其是关中)有着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肥沃深厚的黄土地表,四季分明的亚热带气候,充沛的雨水,使农业耕作最早在此萌生。粮食的丰足带来了人口的增加,随遇而安的人们便由家族扩展而为亲族,继之为村落、乡镇。黄土地供给了维系血缘而居的人们一切衣食。特定的地缘环境与物产特质,培育养成了陕西人喜食酸辣、爱吼秦腔等乡土文化特点。而这一切,又相异于同属黄河流域文化圈的晋、冀、鲁、豫等省区的人。
黄土地理环境决定了农耕生产方式的必然生成,也同时决定了小农经济及其意识的孪生发展。原始农耕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的,自产、自销、自给自足。农业耕作的生产方式,培育了他们信奉天命与先人经验,讲究看风水地穴的心意信仰;同样,农耕方式也促成了他们企盼风调雨顺过安稳日子的文化心理和勤劳朴实从田里找食的文化性格。土地对人的恩泽,使陕西人自然而然地在心理积淀了依恋故土,不思拓迁,不慕异地的潜隐性思想或观念。知足常乐,小富则安,均产均田,杀富济贫……小农意识就这样随黄土情结而刻印在陕西人心中。直至今日,“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仍然是广大农民衷心向往的幸福生活,而“八百里秦川尘土气扬,三千万人民乱吼秦腔。捞一碗长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则是对仍安然于农耕文化生活方式中的陕西人文心态的形象刻画。陕西作家刘成章的散文《关中味》就以富含情感的笔墨,生动地勾画出陕西的地缘物产的特点,表现了陕西人对油泼辣子面的挚爱与知足心理。“在关中大地上行走,想起这些深储于心头的种种情景(春天盛开的油菜花,秋天收挂起的辣子,覆盖四季田野的小麦——作者加),你不由地想到,这片土地,是油泼过的,是辣子炝过的,是面片铺成的,这片土地就是
一碗油泼辣子彪彪面。”至于贾平凹在《美穴地》中对“风水”信仰文化的描绘,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杨争光在《收获》杂志上连年头条发表的土匪题材小说,都能印证黄土情结及其文化心理对陕西作家创作的直接关联与影响。
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文化,也是黄土情结的一个重要的原型形态。陕西自古帝王都,十三朝帝王曾建都于此。周朝的“成康盛世”,汉朝的“武帝盛世”,唐朝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陕西政治文化的基础。建立在黄土地与农耕方式上的政治文化,自然看重并推行以家族为基础的宗法制,看重土地私有与小农经济,重农轻商,强调效法先君,崇古尚老。这种政治体制因为小农经济易于维持生存的原因,其治国之道自然侧重社会人际秩序,而偏轻物质发展与进步。因此,以伦理调教为中心,以家国同构为治理模式,以天人合一来强化“天道”,便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虽然它后来由陕西推向全国,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只要将社会革新的时限向20世纪划近一点,人们便很容易地看到,在每一次变法革新和反封建立新学的运动中,惟有陕西境内相对安稳,极少有变。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后,相对于各省的社会经济发展,陕西人仍然抱守着小农经济的方式与意识,满怀希望地在黄土地里耕作丰足的生活。让他们以牺牲宁静安适的伦理生活来换取喧闹的现代生活方式,无异于将前一种已经习惯的享乐替换为后一种享乐,这是黄土情结作用下的人们不愿冒险的。
还有“学而优则仕”作为古代社会的一种仕途捷径,至今影响着陕西人的人生抉择。而“父母在,不远游”,更是基于黄土地能颐养天年创生的孝悌观念及其人生信条。这一切都足以说明,黄土地发生的文化原型,首先是陕西人拥有,最终也为陕西人所有。所以,对它感受体验最深切的自然还是陕西人(作家)!高加林在走投无路时扑到黄土地上的情形,同我们所理解的陕西人的黄土情结多么吻合!路遥寄寓人物多少同情?《白鹿原》之所以能显示出博大精深的文化历史感,与陈忠实对黄土地上生成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切感受怎能分开!
乡情文化亦是缘于黄土地及其农耕生产方式所形成的一种惟地缘为亲的心理原则。中国文明社会是在原始氏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西方斩断血缘关系而跨入资本私有制不同,中国私有制社会保持了浓重的家族血缘关系。尤其是陕西的黄土地,因为宜于农业耕作,更促成了以家族为轴心的村落及其小农经济的拓展。人的天性中的血亲之爱及其紧密关联,凝聚了一家一户人和睦生存,这样,就由亲缘而拓为乡缘,“乡”“亲”们便“生于斯,死于斯”,乡邻亲情关系便由此固定化了。在这一派乡情弥漫的土壤上,小农经济得以持久发展,商业竞争机制永难壮大。独重乡情的结果,使人们既勤劳、朴实、内向,又狭隘、自私、保守,生活方式趋于凝固化,从而又形成自我封闭、排他性等心理情结。这种狭隘自私的家族利害观念,后来造成多少乡邻反目,群情排外!杨争光的小说《黑风景》中所揭示的不正是这样一种发自心理排外而实为害己的文化荒诞剧吗?比土匪蛮横无理抢砸西瓜一样更为阴险的,是村人公派鳖娃去土匪巢穴谋杀土匪头子老眼,而后又先土匪一步杀死鳖娃!杨争光通过小说所揭示的正是源于黄土情结而生的保守阴暗心理。
综上所述,陕西作家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山水人情,所凝结的就是这样一种地缘情结。它们既是陕西作家创作的素材来源,又是他们创作的动力与价值坐标。黄土地所赐予他们祖辈和他们自己的那些恩惠与痛苦,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价值观念,促成了他们对人生、对文学的苦苦追恋。这是生活在历史相对浅薄的城市人无法想象与沟通的。当然,陕西作家的思想观念与审美境界也同样受到它的很大影响,他们创作中的缺失与不足亦缘于斯。但是,无论怎样看,这种黄土情结都是最具有文化意味与乡土意味的心理动能,它驱使着作家为找寻在现代失落了的精神家园而不断思索和创作,为守望自己的心灵乐园而苦恋日夜萦绕于内心的故乡情感与思想。由于它继承久远,贯通古今,一旦为作家所体验并清醒意识,就可能成为构造“史今同构”的文学作品的情感与思想基因,成为中国文坛上独领风骚、独具特色的创作群体。而陕西作家的审美方式也因此而生成并独具特点。
二、以善与美冲突为基质的审美方式
居于黄土地以农业为本的陕西人,厚土重迁,中庸和善,悲天悯人,有着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由此而引发的新与旧、保守与革新等社会矛盾,冲击着陕西人积淀深厚的地缘文化观念。面对社会的巨大转型,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传统伦理思想的冲击,大多数农裔城籍的陕西作家真切地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生成以来,家族间和民族内最大的矛盾不是恶与善的冲突,而是个人的自然欲望与社会的伦理秩序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冲突在现代转型社会愈来愈尖锐,愈来愈显示出独特的审美与认识价值。
两千年前孟子曾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里所说的生,可以看作生命体的自然欲望,是生命得以持存发展的基质,它具有美的特质。这里说的义,是属于道德范畴的规范,是社会人伦秩序的合理体现,它具有善的特质。从培养道德人格的角度看,孟子的训导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伦理中心观。但从审美形态的角度分析,善与美的矛盾冲突超越了善与恶悲剧类型,集中反映了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生的悖论现象,涵盖了个体与集体、感性与理性、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关系,构成了审美认知中又一个审美的类型。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古堡》,王蓬的《水葬》,京夫的《八里情仇》,赵熙的《绿血》等小说代表了陕西作家的这种文化透视类型。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冯积岐的《村子》也可归入此类。
综合起来看,这是陕西作家中运用最多的一种审美方式。他们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中以道德评判为底蕴,将人简单地划分为好人和坏人的幼稚做法,而是努力地将新一代农民渴望发展自身的追求,和在追求中突破传统伦理束缚的努力及其悲剧真切地展现出来。虽然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作家大都具有这样的审美认识,他们的作品中也作了类似的解读,但是像陕西作家那样饱经生活苦难的体验,从小就沉浸在独特的地缘文化情结的熏染之中,努力突破传统伦理的束缚,去思考新与旧、保守与革新等社会矛盾的创作情形着实不多。也正因此,以善与美冲突为基质的审美方式的代表作品,才带着黄土地的芬芳,满含着三秦人民的生活苦痛与欢乐,冲击着当代读者的善与美矛盾纠纷的心田,令人们为之感动和回味。
路遥的创作始终与民族命运和现实人生联系在一起。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他所描绘的都是他所钟爱和努力探寻的,即黄土地上的农民怎样走出黄土情结的阴影,在现代文明的引导下建设自己理想家园的迫切历程。崇高的理想和完美的道德情操是他所树立的审美目标,而善与美的冲突则是他
对现实人生矛盾及其悲剧的清醒把握。《人生》中,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纠葛,就典型地表现了高加林的个体人生价值追寻与刘巧珍的传统伦理观念的矛盾冲突。从高加林勇敢地告别家长、恋人而踏入城市,到因社会的复杂冷酷关系被重新抛回黄土地的描写中,不难看出路遥忠实于生活、再现生活的文学观,及其与土地的深刻联系。他就是要把自己的理想人格建立在黄土地上,在人生理想追寻的过程中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平凡的世界》扉页上作家的献辞“——仅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正是作家心扉的展示。在路遥看来,黄土地就是生养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归宿。而母亲无论何时总会以自己的慈爱的胸怀收留自己的儿女的,因此,高加林在现实中走投无路时扑进黄土地的呼喊:“我的亲人哪……”正是路遥黄土情结的真切流露。至于《平凡的世界》中对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纠葛,田润叶与李向前的家庭矛盾,孙少平与田小霞的纯真爱情,以及对田福军、孙玉厚等干部、农民的描写,都突破了简单的善恶价值判断的陈旧模式,而追寻着善与美冲突的审美类型。不过后者比前者结构庞大,生活面宽广,作家对人生理想和完美道德的追寻更坚定也更清醒了。它表明了路遥在对自身黄土情结的透视中建构现代审美人格的努力。
京夫的长篇小说《八里情仇》通过美丽善良的荷花与林生、王兴启和左青农三个男人之间的爱恨离合的矛盾纠葛,展现了中国特定历史年代中人性的压抑、扭曲和绽放的美态。荷花与林生的真挚爱情在遭遇了高度火伤残疾的王兴启丈夫名分时,善真的情爱被巨大的社会伦理所阻遏和压抑。虽然王兴启率真地“归还”荷花于林生屋檐下成夫妻之爱,并最终生下儿子金牛,但名分的遮蔽反而促使林生与金牛父子成仇——儿子视母淫乱,视父偷奸。血亲伦理冲突终于酿成善与美的悲剧:金牛卧轨自尽,荷花“两夫”皆失。作家以民间传奇之笔所结构的情仇故事,撼人心魄,令人对善与美的冲突所产生的美感咀嚼不尽,久久回味。
从总体上来看,以善与美冲突为基质的审美方式,仍是一种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家们秉持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贫苦乡亲的悲悯情怀,对当时社会正在发生着的凡常事件进行“如实”的反映。这些事件虽然是细小的生活内容,却高度概括了影响社会发展变化的“巨大”矛盾,从中可以窥见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种种羁绊。除了善恶争斗,这类作品更注重展示传统伦理与个性欲望的冲突,表现时代背景下的血亲伦理冲突的悲剧意义。所以,它具有较为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色彩,反映了陕西作家关注现实,反思人生得失,创建现代文明与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如果说《平凡的世界》、《八里情仇》和《浮躁》是以全景式视角描绘黄土地上农民对理想的追寻和对完美道德的礼赞的话,那么,赵熙的长篇小说《绿血》则是对黄土地上血亲伦理悲剧的建构。老革命郝永虽然斗杀过地主恶霸杜石,但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情势下,女儿兰草儿、绿草儿双双背叛他的调教而“私奔”,令他尝到了血亲伦理间冲突的悲苦滋味。作家敏锐地捕捉到在革命老区的陕北黄土地上,恪守传统伦理文化的老一辈人与追寻自我生命价值的新一代人的矛盾冲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家把路遥和贾平凹曾经透视过的生活,在更高的冲突层面即最易激起人们情感两重体验的亲情关系上揭示出来,不能不说是对善与美冲突的文化透视型文学的一大发展。
三、写今贯古的双层意蕴结构审美方式
黄土情结是一种历史文化与生活经验的心理积淀,它既可以在作家描绘的表象层生活中探寻到,亦能够透过承载了历史文化表征的传统式家族生活里发掘出来。所谓写今贯古的双层意蕴结构审美方式,是指那种通过表层现实生活的审美描写,既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民众生活相,又在文本深层意蕴结构中寄寓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使作品具有“史今同构”的双层效应的审美建构方式。可以说,这是一种最可能全面反映黄土地人原生态生活世相与地缘文化心理的审美方式。它有别于表象层面反映论式的写实手法,是一种发展的和深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由于这种文化透视方式对生活原型与心理情结、表层描述与深层寓意的“对应,关系要求很高,故此,能够掌握和达到上佳境界的作品很少。陈忠实的《白鹿原》可以视为此类型的代表作。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叶广芩的《采桑子》、贾平凹的《高老庄》、蒋金彦的《最后那个父亲》、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等可归入此类。
陈忠实是一位具有较强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作家。在“帝王之乡”多年的基层生活经验,尤其是走上文坛后强烈的生命体验,使他写作的《白鹿原》与路遥直接抒写农村的“时代风采”的方式多有不同。陈忠实有意将他的文化视窗定格在保留有家族宗祠的清末民国年代,通过生殖崇拜的文化心史叙述主线,作者在表层结构中勾连起了国民党、共产党和“民族主义”三个派系的矛盾纠葛,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处在民族历史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地方势力的斗争情态。为了全面深刻地透视民族文化的心理秘史,他大量描绘了民族特有的乡里社会民俗(家族、亲族、村落)、人生四大礼俗(诞生、成年、婚礼和丧礼)、心意信仰民俗(祈水、阴阳风水、灵魂转世)和经济物质民俗(饮食、居住、耕作)等事象。这些民俗事象是与民族文化同步发生的,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题材的熔炼与择取,使作品的双层意蕴建构有了准确的“对应”关系保证。
透过白嘉轩修身、齐家的过程,陈忠实为读者刻画了一位在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族长形象。他严于律己,孝敬母亲,善待妻子,严于教子,是儒家仁人君子的典范。他对黑娃、田小娥、白孝文“乱淫”的惩罚,体现了传统的名节观;而他与鹿子霖的明争暗斗,则暗示出小农意识中自私、阴毒的心理。所以说,《白鹿原》不仅建构了传统文化的“家国同构”、伦理治家的模态,而且深刻地揭示出血亲伦理悲剧的审美意义。尤其是作家在小说中大量描绘到的那些具有极强的心意信仰的事象,因为曾在远古社会特定环境中“发生过”,并沉积到民众集体的心理,所以,当它被作家依情境形象地描绘出来时,就启唤了读者的文化情结与心理原型,仿佛感受到了一种远自史前又近似现在持续发生着的事件,领悟了极为丰富的缘于生存又高于生存活动的文化内涵,从而达到“史今同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与审美愉悦。
陕西民众长期生活在帝王之都,对于江山社稷他们有着超越外省民众的责任意识和虔敬之心。正是在重农轻商、崇古尚老的帝都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在重视革命理想、勤俭持家的延安精神的感召下,陕西人长期以来看重社会人伦秩序,偏轻社会发展与物质享受。在他们的心理中,簇生着泛神性崇拜的精神,对生长于其中的村庄、田野、山林、水域、荒漠有着亲和与敬畏之感。虽然他们也向往工业文明,渴望有现代化的生活消费,但工业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周而复始的生活结构,喧闹的城市人群和有违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方式,让他们心理难以接受。
这种对农耕传统和“人文生态”执著认同的精神,使陕西作家在面对社会的变革和人生的苦难,而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中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审美的信仰精神,一种浓郁的诗性和神性。作家赵熙的感受颇具代表性和说服力:“远离大城市和人世喧嚣的山地生活,使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人类同大自然这种依存共谐、生死相息的联系……这大自然的山河原本是富于生命的。人同天地的合一和灵魂的融化构成了一种新的意境和体验……那种‘回归自然、‘返朴归真哲学意蕴更赋予作品深层的意义。”
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及其系列小说,虽然写的是“文化大革命”时人民公社发生的事件,但由于作家把文化透视的视角选定在“李氏”生产队,赋予生产队长李金斗具有同白嘉轩一样的“族长”权力,因此,他的小说同样具备了写今贯古的双层意蕴结构的建构价值。小说通过李金斗的干女儿彩芳从女儿到大儿媳,再从守寡后的干女儿续嫁为二儿媳的描写,相当真切地勾勒出贫困落后地区愚昧的社会众生相,透视出千年古俗中童养媳的文化历史内涵。正因为彩芳同榆桂的爱情使李金斗丢人丢“财”,而且与宗族的利益、传统的伦理秩序相对抗、相冲突,所以,彩芳遭唾骂遭毒打被扼杀的命运就毫不足怪了。“桑树坪系列”虽然不同于家族宗祠的题材,但朱晓平的创作实际上开辟了写今贯古的又一条佳径,比之《白鹿原》,《桑树坪纪事》虽篇幅短小不够博大,但它更贴近现实生活,更易于为大众所解读,这是应该引起陕西作家注意和借鉴的。
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是继《白鹿原》之后又一部风格独异、家国与古今同构的优秀作品。作家独异的家族血统与丰富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和文化素养,使她的小说在冷峻写实之中凝构了写今贯古的双层意蕴结构。从表象层面来看,《采桑子》是写满族贵胄爱新觉罗——金氏家族近百年的生活历史。这个一夫三妻妾、七子七女的大家族,犹如20世纪之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化,丰杂而坎坷:长女痴迷票戏而致生命如戏变化无常,长子反叛皇庭投身军统而义无反顾,二子、三子、七子青年时争风吃醋,祸起小女子黄四咪,中年后却在“文化大革命”中人生错乱、亲情倒逆,致使皇亲国戚亦失淫欲之迷。大家族每个成员由富贵到贫穷,由娇性到自持自重或贪婪妄性的人生历程,一如文化古国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艰难蜕变过程,充满象征意味。它使文本结构的深层充溢着文化反思的深刻主题:晚清王朝的衰败,国民政府的软弱,共和国的内耗与复兴,同爱新觉罗——金氏家族的荣耀与衰微,金家子女的争斗与人生选择及其迷乱,同构相生,家寓国体。小说的笔墨所指既达皇庭贵族王公大臣、车辇宫室,又抵民间百姓油盐酱醋、忠臣猛将贤臣孝子,以及贼人、知青、老板、书画家、文化贩子等,善恶淫欲尽揽文中。一部《采桑子》不啻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图画和民间野史,让读者从中感受良多,合卷沉思,感叹不已。小说表现出作家对清(王朝)衰汉(民族)化的民间文化解读的独特视角与人生感悟。比之《白鹿原》,它既有题材上的独特性,又有历史与现代的有益连接。
写今贯古的双层意蕴结构审美方式可以看作是以善与美冲突为基质的审美方式的发展和深化。在这种现代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作家们注重借鉴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叙述技巧和结构方法,在对家族历史及其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构筑以探寻民族文化心灵秘史的同时,注重了对感觉、欲望、魂灵、情感等非理性心理的把握与描写,有的还创造出令人难忘的颇富文化寓言意味的象征意象(如“白鹿”)。它使小说文本不仅反映了生活史实,而且增添了“诗”的灵韵和“思”的深度。这些艺术方法的创用,使文本具有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丰富了作品的历史感与文化感,使读者在家族生活礼俗的复建中,第一次逼近了民族文化心理的内质,探视到民族文化心理的隐秘情结,从而在深刻反思民族民间文化的同时,开始了建构民族文化的新历程。
四、文化批判为主导的审美方式
文学创作一直面临着这样一种价值选择:文学究竟应该将人生描述为一种欢悦的存在,还是把它视作一种对悲剧存在的深刻思考的文化样式?不同的审美认知自然会有不同的审美方式。20世纪中国文学自鲁迅起,持续着一条清醒自觉的知识启蒙、文化批判的创作道路。他们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所思考的生命的痛苦、孤独、有限以及“异化”不同,更多地表现在对传统文化束缚人性人欲、令人麻木变态的批判上。陕西作家中虽然没有以文化批判为主导的创作群体,但是基于黄土情结的体察与文化透视所创作的一些作品,如杨争光的《黑风景》、《赌徒》、《棺材铺》、《老旦是一棵树》等中篇小说,贾平凹的《美穴地》、《五魁》和《废都》以及《病相报告》、《高兴》,还有黄建国的《蔫头耷脑的太阳》等短篇小说(集),依然反映着陕西作家的批判锋芒。
杨争光是陕西成名作家中年龄相对较轻、学历较高、文化批判意识较强的一个。他曾坦言:“我以为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家,中国的城市是都市村庄。中国农民最原始、最顽固的品性和方式渗透在我们各个方面……他们遇到一些事情,他们按他们的方式做了。我就这样写。”这是杨争光为自己的创作,即文化批判做的明确的注解。从《黑风景》杀了土匪头子却反被同村人暗害的鳖娃的遭际中,人们不难看出作家对比土匪更狭隘、更自私的农民的“匪”性的批判。黄土情结中小农意识要求均产均权平等的心理,使遇到危及自身利益时的农民更显得堕落和可怕。正是这种心理情结,使人恋土恋家,不思迁异,不图进取,固守着自己的文化信条。八墩赌财,骆驼赌命(命搭甘草),甘草则心甘情愿地将命维系在八墩身上赌下去。从《赌徒》的象征性描绘中,人们不难体悟到人生不可扼抑的循环怪圈和中国人衰堕的文化秉性。
严格地说,杨争光不能算作现实主义创作类型。他那冷峻的似客观而实则抽象式象征的叙述,使他明显地有别于陕西作家群体的风格。为卖棺材而杀人,这并非生活的常理,而是一种小农意识下的行业心理。就像卖西瓜的渴盼天旱一样,他哪管地里将会颗粒无收!因此,在杨明远身上,作家透析了一种民族文化心理,一种狭隘的黄土情结的原型。尽管杨争光对胡、李两家整个斗杀过程的编造不太“真实”。(《棺材铺》)文化批判和抽象式叙述使杨争光小说具备了“现代”审美意味。作家要表现的是不易为人明察却又时刻影响民众的民族劣根,即民族文化传统中有悖人性人伦的丑陋与阴暗心理。这种心理多已沉淀为一种情结或原型,它对人的促导隐秘而间接,非艺术透视难以认辨。
陕西是一个内陆闭锁的省份,长期生养于黄河流域的人们勤劳朴实、惟地缘为亲。文化的亲和性即黄土情结的长期滋养,使他们相较于其他省份更多出一份文化的保守性。虽然人人都期盼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却认同现实,观念滞后,放弃启蒙。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陕西文坛以文化批判为主导的作家较少,引起全国瞩目的作品也不多。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具有
独立文化自省意识的作家,却能获得超常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创作出独具个性风格的优秀作品。
黄建国的创作情形与杨争光十分相似。他不仅年龄与杨争光相仿,学历相同,而且来自同一个关中县,审美价值取向也很近似。其短篇小说集《蔫头耷脑的太阳》中的大部分篇什,都是择取农民现实生活的琐事,从中透视农民的自私、保守、龌龊,显示出他对他所熟悉的中国农民文化心理的痛惜与批判。《岔口》表象层面是写来发和康麦为拾到拾圆人民币而喜气、猜忌、诅咒的行为,而在深层思想层面实则揭示了中国人思想信仰的岔口,从众迷信、猜忌多疑、图谋不易之财却又不想承担的国民劣根性。
黄建国的短篇小说虽未能产生类同杨争光一样的影响,但只要读一下《蔫头耷脑的太阳》(小说集)就会发现,这位一直在高校教书的农裔城籍作家,正因其对农民生活文化的真切感受,才以痛惜的笔调写出了他对猥琐龌龊的乡民的悲悯之情。《蔫头耷脑的太阳》(单篇)是写兄弟、父子之间隔膜、冷漠的生活关系。作者抓住三成乘车回乡看望老人之事,牵引出大成与二成两家的隔阂。只因三成乘坐的局长的小汽车停在了二成家门口,大成和大成妻便愤愤然上门争吵。对父亲的关照不再遮掩,而“脸面”此时成为争抢的惟一焦点。作家于精巧的构思中利刃剖析了最念亲情的中国人亲情反目、心理成仇的生存窘况。造成亲子间的冷漠的原因,虽有个性追求的原因,但经济贫穷、见利忘义实为根本之源。黄建国强皱眉头俯视人间的一幕,表现出他对乡民父老生存窘况的同情,对亲情渐失的哀痛与批判。
杨争光、黄建国等陕西作家对民族阴暗心理的剖示和批判与鲁迅直面人生拯疗国民劣根病有所不同。鲁迅的文化批判是为了唤醒民众救国救亡,小说中暗含着激愤与焦虑,充溢着热切的呼唤。而陕西作家的文化批判缺少些许启蒙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黄土情结的潜在影响,使他们在审视黄土地人的精神病体的时候,多了一份无奈的家乡文化情感;知识分子的孤高桀骜,又使他们决绝地与民众的丑俗陋习隔绝开来。他们的审美批判中带有戏耍般的嘲讽,态度冷漠而真诚,“病态”描写入木三分。同余华、苏童等人的“先锋式”审美方式相比,他们还缺少对生命的“沉沦”与“堕落”的无情批判。即使如此,文化批判为主导的审美方式也因此具有审美的现代性,而与其他陕西作家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陕西著名作家中,贾平凹是又一个切近“现代”的作家。纵观他的创作,他在走着一条深化的现实主义批判的路子。他创作的《太白山记》、《美穴地》、《五魁》、《病相报告》、《怀念狼》、《高兴》等小说,文化批判与文化象征意味相当浓郁。《美穴地》中五魁和柳子言具有相近的文化人格。五魁从土匪手中救回了视为女神的心爱的女人,却不能给予她以人伦之爱。传统教化中的仁人君子心理使他成为比土匪更“残忍”的人。女人虽然逃脱了土匪的性摧残,却落入了非人性的“禁欲”之中。作家对五魁文化心理的“残疾”的透视可谓出人意料,入木三分。与五魁类近,柳子言这个风水先生更是儒雅君子。面对甘愿献身的如花似玉的四姨太,他竟人欲尽失,不能自控。只有到了四姨太被毁容,“女神”变成“女巫”,成为自己老婆时,他才“再不是往日无能的男人”。柳子言的身心变化,对应了传统伦理“淫”的训诫,表现出“卑”的情结。传统文化情境中的人竟是这般自卑与萎靡,从中不难看出作家对传统伦理的批判,对审美人格的认识与建构。
《病相报告》并不能算作优秀之作。尽管作家有意地在叙述人称与视角和语言风格上做了明显的调整,但古老的故事框架所追叙的人物情节,并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与感受。倒是作品整体上呈现的文化批判精神和人性意识使小说具备了一定的“现代性”,多了一份文化批判与反思的力度。这一点对于陕西作家整体来说,具有认识上的启迪意义。长篇小说《高兴》可以看作是《病相报告》批判意识的延续与发展,作品通过进城拾破烂的农民刘高兴的生活经历,展示了现代城市社会最底层“贱民”的生活情态、命运交错与心灵变迁,表达了作家对“贱民”群体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关注与悲悯,给予了人文主义者的关怀和批判。高兴是一个社会转型中的乡里能人,他在西安拾破烂的社会经历,显映着乡里能人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中的艰难蜕变,从中映照出了转型社会的时代风尚、地域风情、城乡教育失衡,民众的生存状态,以及农民置身城市时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置换临界等诸多问题。贾平凹在《高兴》中所表现出的写作转型和批判锋芒值得关注。
陕西作家的审美方式或可细划出更多类型,以上三种审美方式,主要为论证黄土情结对创作的影响所分,难以囊括陕西作家的创作风貌。这三种类型各有特点,各显优长,各具价值。第一类作品贴近现实,抒写改革,刻画了新型农民的形象,多为传统式现实主义手法。它标明了陕西作家参与现实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第二类作品较第一类更多一些文化透视与文化保守的特色,因刻意描绘族长、臣民的形象,剖析其文化心理,因此也多了隐喻意味,是一种发展的深化的现实主义。第三类作品因为具有现代审美精神,在对土匪、刁民和底层民众的勾勒中糅进了神秘象征的意味,使作品的意蕴变得复杂和丰厚,很难用划一的现实主义来概括。
如果从三种类型代表作家的地域构成来看,还可看出地缘情结影响创作的佐证。生活在陕北的路遥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多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熏陶,因此,他的作品才将人生理想与完善道德的追寻并揉一处,才把人生苦难的承受与悲悯情怀的抒发相同构,表现出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鲜明特征。陈忠实生活在皇天乐土的古长安城郊,传统文化的熏染无论如何相对他人都强盛一些,他对传统人格的激赏多于批判也就可以理解了。正因此,白嘉轩才被塑造为仁人君子,在他身上寄托着作家探寻重建民族文化的理想。贾平凹虽然早已离开陕南,但商州的山水神韵早已渗入骨髓,因此,其作品中显现着传统文化的神韵和神秘文化的色彩也就不足为怪了。
[参考文献]
[1]陈忠实,《四妹子》后记[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2]霍尔,等,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孟子:告子上[M]∥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4]赵熙,秋夜的眼[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
[5]杨争光,老旦是一棵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张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