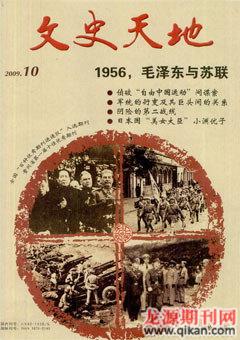阮籍的佯狂之旅
慧 泉
中国的后三国时代,是魏国向晋王朝过渡的历史上有名的乱世时期。此时,虽然魏国的帝王是曹操的孙子曹芳,但已是朝不保夕!就在上一年(公元249年),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司马懿父子发动“典午之变”,把曹芳的亲表叔、执政大将军曹爽等党羽一并斩草除根。仅此一项,前后共诛杀了三千多人!从此开始,司马懿就基本上控制了魏国的政局,但司马氏父子并未善罢干休,又在后几年内连续痛下杀手。帝王中,有魏楚王曹彪遭殃、魏少帝曹芳被废、曹髦为帝后也被诛杀;大臣中,太尉王凌被夷灭九族,李丰、夏侯玄等八族被诛,文钦、诸葛诞等起兵反抗也被武力镇压。至公元260年,一代枭雄曹操打下的基业和势力已彻底干净,曹魏时代结束。
在司马氏集团一步步篡权的过程中,其对反对派和不合作者的镇压是极其严厉与残酷的,可谓杀人如麻。于是,一些本来踌躇满志的士人,便兴起了回避残酷政治的退隐之风。他们所采取的形式,基本上就是饮酒清谈、弹琴啸歌,纵论当下最流行的“玄学”思想。所谓玄学,即是以《周易》《老子》和《庄子》为依托,融合儒道而出的新的思想学说。从而就有了史称“竹林之游”,产生了津津乐道于当时,名扬千载于后世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表面上给世人的印象是狂放不羁,但他们的骨子里面是想求得解脱,寻找人生的出路。司马懿父子以武力篡夺魏国政权的行为,他们是非常反感的,但又不敢公开反对。那么,下一步该何处何从呢?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为自己的灵魂找个归宿呢?对于这个人生的精神境界问题,有的人想到了用孔子的人世同老子的出世相结合;有的人则认为这样还不能彻底的解脱,不足以舒展地安放自己的灵魂,他们选择了走庄子“逍遥游世”的自由浪漫之旅。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阮籍,就是走的后一条道路……
幼丧父沉默寡言掩奇志
阮籍出生于公元210年(建安15年)。他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从此就与母亲相依为命了。丧父的人生悲剧,给阮籍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影响到他小时候起就有孤傲怪癖、寡言少语的性格。除了吃饭,阮籍经常十天半月地关在房间里,主要是看书,要不就是沉思默想,很少跟别人说话。阮籍从小聪慧异质,八岁就能写文章。除了习文,他还兼习武技。可见少年的阮籍似有平治天下的雄心壮志。有一次阮籍登上广武城,俯视楚汉争雄的古战场时,一股自诩的豪情涌上心头,他不禁感慨地说道:“当时没有英雄,使这几个小子得已成名!”
看来,他连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项羽、刘邦都不放在眼里,这时他才刚满15岁。阮籍的远大志向得到了他的族兄、时任清河太守阮武的赏识,逢人便讲道:“阮籍小弟的才华比起我,可高得多了!”
约在阮籍17岁时,他叔叔阮熙到东郡公干,顺便带上这位自命不凡的侄子,想让他见见世面。谁知道,当兖州(属山东省)刺史王昶特地重礼款待这叔侄俩时,坐在旁边的阮籍却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王昶在他们走后感叹道:“孺子阮籍真是深不可测啊!”
这不外说明两点:要么是阮籍确有宏深的气度;要么就是他的性情给人感觉到孤傲和寡合。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卒,遗诏由8岁的太子曹芳即帝位,命曹爽、司马懿等辅政。从此到公元249年的这10年里,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由暂时的合作开始走向到分裂,政治局势也由相对稳定走向动荡不安。与此相关,阮籍的政治态度或生活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剧烈而痛苦的转化过程。
公元242年(正始三年),阮籍33岁。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阮籍“才俊志高”,于是询问部属王默,得到了确认。蒋济便想征召阮籍做自己的属官。阮籍听到此消息,即分析了当时的局势:现今局势被曹爽这个蠢才弄得已很不乐观,而司马氏父子又精于谋略,他们之间暗中较劲已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在这局势诡谲多变之时,哪是我出仕的时候?我还是先等等看吧!于是,阮籍写好一封婉拒信,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蒋济当年在荆州会战中勇胜关羽而取其首级,威震华夏,岂能受此侮辱?便对王默破口大骂,使王默非常的害怕,只好写信劝说阮籍。害怕蒋济将军“虎威”的乡亲们,也都前来劝说阮籍,请他不要连累了大家。阮籍只好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
过后不久,曹爽又召阮籍出任参军,被他以病为由,婉言谢绝。
阮籍先后两次婉拒出仕,前是拒太尉蒋济,后而拒辅政大将军曹爽。同样是婉拒,而心态迥然不同。前者,他对自己的理想尚抱有希望,对政治是观望心态;而后者,阮籍对政治理想前景已经破灭了,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则采取了退隐之态。
在“竹林七贤”里面,阮籍有几招硬功夫是响当当的。一是他的长啸声(吹口哨)可以传到几百米之外。长啸是中国古代隐士传统,它一则可以锻炼身体;二则是在懒得跟人讲话时,便以吹口哨回避,是一种自娱自傲的修身方法。此在稍后的陶渊明,也是以“登东皋而长啸”来抒发他的隐逸志向的。还有唐人王维,也写有“弹琴复长啸”的清逸诗句。第二是他善于搞出叫“青白眼”的行为艺术。据说他见到不喜欢的俗客,心里不快,但又不便于明讲,就会将自己的眼珠子翻到里面,留下白眼对着人家,搞得别人很难堪,只好灰溜溜地离去。如果遇到他所喜欢的人,则会以正眼(青眼)瞧着人家,表示满意和尊重。第三是阮籍酒量惊人的大,在“七贤”中只有号称酒鬼的刘伶可堪比。据说有一首古琴名曲《酒狂》,就是以他俩为原形而创作的。所不同的是,刘伶醉酒后的表演已近乎疯子,让人不堪人眼,因为他醉酒后,便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的坐在家中高声唱曲。当别人看到感觉极不雅观,走进屋里指责他时,他则大声反驳道:“我以天地为屋,草房当衣。我在里面自由自在,干卿何事?你们管得如此之宽,跑到我裤子里来干什么?”
借酒卖傻苟全性命于人世
说到阮籍的醉酒,鲁迅先生给了如此的评语:“他的饮酒不独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
故有的历史学者给阮籍戴了一顶帽子,叫“佯狂”。但在司马氏势力的屠刀下,要想摆脱政治是很难的。一些有识之士要么被迫“应征出仕”而苟且偷生,要么拒绝合作而被找个理由遭杀害。由于政治上的强大压力,“竹林七贤”的一些成员并没有如愿走向山林去做超世的隐士,而是先后出去做了官。阮籍就是被迫地走上了一条“朝隐”式的生活道路:他虽然身任官职,却事不关己;他开口就讲《庄子》,借清谈以表现自己远离政治;他几乎每日醉酒,来掩盖自己对现实的失望和内心世界的苦闷,表现出一个十足的“酒狂”。但这是装出来的,只是装得特有真实感。
阮籍的邻居家开了个小酒馆,卖酒的是位少妇,长得十分美丽且有三分风情。阮籍自从到那儿喝了一次酒后,便隔三岔五地去
那儿喝酒,而且是每去必醉,醉到不省人事了就顺势倒在那美妇的身边呼呼大睡。结果有一天,被这美妇之夫瞧见了,一时妒火中烧!后来这血性村夫手提杀猪刀,经过几次跟踪观察,看到阮籍没有做啥出格的事儿,只是醉如死猪!“唉,这事我得谅解他,人喝高了嘛!再说了,于今生意不好做,这种从未赊欠的老顾客也难找,只要娘子是好好的,也还行!”
后来,阮籍听说步兵校尉一职空缺,阮籍知道:此乃一闲职,它并不真正掌握兵权,不会给司马昭造成压力,找借口向司马昭索求此职并借此脱身。阮籍向司马昭讲道:“美酒是鄙人的大好,听闻步兵营人善酿酒,又有许多藏酒,鄙人自荐任步兵校尉,恳请大将军成人之美!”
司马昭笑着允诺了。阮籍如愿到任步兵校尉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约好友“酒神”刘伶前来一同品尝美酒。那刘伶喝得东倒西歪后仍不肯罢休,临走时又顺带捎上了几坛酒,甚至于上车后对马夫吩咐道:“你找个人扛着铁锹跟在后面,若见我醉死就地掩埋得了!”
司马昭听说阮籍有一小女尚未婚配,就想与他结成亲家,好把他绑进自己的势力圈子。于是,司马昭便派了心腹钟会前去说亲。此番心思,阮籍心知肚明。当钟会到来时,阮籍就已酩酊大醉,满口醉言,问东说西。钟会只好临时住下,第二天又到阮籍住所,进门就一眼看见阮籍手执酒壶,与他说话,简直就是答非所问。这有酒天天醉,凭心而论,阮籍装得也忒过了头,他前后共醉了六十天啊!阴险狡诈的钟会,却屡次向他谈论时事政治,总想从他口中套出个话头来,再找个茬好好地修理他。但酒醉心明的阮籍玩得也好高明,以钟会的智勇双全,却无可奈何,只好回去向司马昭复命完事。
这位放浪形骸的大名士,在别人看来是颇浪漫的,但阮籍所把握的尺度,仅仅是不被杀头而已,真是令人辛酸。阮籍的心思,是以他的诗作来告白于人们的:
但恐须臾间,魂飞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逍遥游世任性而为不拘礼
阮籍虽然任职于步兵校尉,但还常去司马昭的将军府,以维持同大将军若即若离的关系。将军府的大宴他是必定参加的,并且能表现得相当不拘礼节。有时,他两腿外伸八字型而坐,并旁若无人地吹起自己拿手的口哨;有时,他则自个儿提罐豪饮,醉态十足,并且口若悬河地大讲特讲逍遥无为、成仙得道的玄言妙语,也不顾旁人是否厌烦他。此后,阮籍在步兵校尉的位置上一直逍遥了七八年之久。
有一天,阮籍听说城中有个出生寒微、但才貌双全的少女,未等出嫁就染病而亡。阮籍这次动了真情,认为这是老天不公,天妒红颜,虽然素不相识,竟不顾他人劝阻,独自一路找到这少女家里去吊丧。阮籍哭得是泪如雨下,直到将一腔悲伤之情完完全全地发泄了出来,才幽幽地摸回家里。阮籍的嫂子有次要回娘家,阮籍全然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风俗限制,赶去和她话别。有人就嘲笑阮籍不知礼节,阮籍则回答道:“礼岂是为我辈设的!”
过后不久,阮籍上司马昭的大将军府来,碰巧有位官员向司马昭报告说有人杀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当众便说道:“这杀父亲还说得过去,要是杀了母亲就忒过分了!”
一向拘谨的阮籍怎么口出如此狂言?实乃大逆不道!霎时间,文武群臣脸色大变,议论纷纷。司马昭见状也厉声斥责道:“我司马父子一直以孝治天下。杀父者罪不可赦,阮中郎你这样说是何居心啊?”
看到司马昭动怒,阮籍从容地回答:“不然!我听说,禽兽只认得它的母亲,不认得它的父亲。人杀了父亲如同禽兽,而杀了母亲,就连禽兽都不如了!”
阮籍的回答让司马昭竟一时语塞起来,其他的部属则是面面相觑,心悦诚服。这阮籍实际上是在讥讽司马氏一伙呀!古代礼制是把父亲与国君等同看待的,而司马氏将曹操的孙子辈们杀的杀,废的废,这与禽兽有何区别?又有何资格侈谈孝治天下?不过是欺名盗世罢了!
穷途之哭无药可解心伤悲
阮籍这时的“朝隐”,无论是佯狂放诞,还是饮酒啸歌,都无法消除他内心的痛苦。他时常独自驾着小马车直出城门,到了郊外后,让那马儿随意前行,也不管前面是大路还是小路,有路还是无路。待那小马车走到没有路的地方自动停下来了,他也不下车,而是嚎啕大哭,哭完了就拿袖子揩干眼泪,然后驾车回到家里。这穷途之哭,就足以说明现实社会的黑暗恐怖,给他带来多么深的忧愤和苦闷!
此时的司马昭一伙已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他们借维护圣贤礼制的名义,行罗织罪名灭杀异己之实,将圣贤礼制变成争权夺利的工具。而阮籍的痛苦,也在于他的内心世界的矛盾。一方面,由于阮籍亲眼目睹了司马氏集团与曹魏势力残酷政争的过程,看到了大批的名士身首异处,这都引起了他心灵上的强烈震撼,使他经常处在畏惧不安的境地,陷入生命无常的恐惧之中;另一方面,因为现实的扭曲,使阮籍原来所崇尚的传统道德、价值理想都变得毫无意义,变得格外丑陋。那么,如何寻找新的出路、解脱他内心存在的苦痛呢?
阮籍在道家的寓言中找到了神仙世界,并想把自己寄托在这个美好的彼岸世界里,实现对人生、命运的超越。然而,阮籍实际上是个从儒家文化里脱胎而来的玄学思想家。理性使他时常朦胧地感觉到神仙世界遥不可及,而且可能并不真的存在。于是,阮籍的内心世界又陷入到矛盾之中。当阮籍把他的身心融入到青山绿水间时,他又感受到了一种出于自然的适意与快乐。于是,他登山临水,乐而忘归,把痛苦放在自然的溶液中反复搓洗,让心灵沉入安宁的睡梦之中。可是,这些局部的暂时的医治手段,均不能彻底解决阮籍的心病。因为,只要是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继续蔓延,阮籍心灵的痛苦与矛盾就无法解决。不幸的阮籍,没有做出感人的永别,只能孤悬在天地间,痛苦不安地呻吟着。而他不朽的诗篇,也让我们理解了他的那份情怀:
夜中不能眠,起坐弹鸣琴。
孤鸿号野外,翔鸟鸣北林。
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
但事实上,阮籍的“纵酒保身”策略并不是永久有效的。司马昭府中的那些道貌岸然之徒,总在寻找机会要将他置于死地。一天,阮籍家人破门急报:“老爷!你母亲大人已昏厥过去,不省人事了!我来时就双手冰凉,气如游丝,此刻恐怕……,夫人请你赶紧回去!”
阮籍此刻满脸醉意,正与客人下围棋在兴头上。惊闻母病,如五雷轰顶,心都凉了大半截,他本能地欲推开棋盘起身。忽地转念一想,我如此这般,岂不与常人无异?先前多年的佯狂枉自白费不说,那些好事之徒定将找出我的岔子置我于死地。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呀!而这时,下棋的客人也很感突然,立即起身向阮籍歉声告辞。只见阮籍的脸肉抽搐了一下,随即高声说到:“岂有此理!这盘棋已近尾声,下完它再走不迟。”
客人无奈,只好又坐下来陪他把棋下完。等客人走了后,阮籍才显现真性。他跌跌撞撞地走进内室,拿起酒坛就朝口里直灌,
身子则不由自主地瘫倒于地上!这时的他,不禁悲从中来,仰头哀号不止。已是纵酒过度,致使极端虚弱的阮籍,竟然吐出了几大口鲜血。
在母丧期间,阮籍依然如常地去司马昭的大将军府邸赴宴狂饮,而且谈笑自若,没有一点悲哀的表情。司马昭身边的属臣何曾早已愤恨不平了,当着司马昭的面就斥责阮籍道:“你母亲老大人病逝,按礼制规矩你应该在家里白衣素食,守孝寄哀。可你却若无其事,依然纵酒高歌,完完全全是个违背礼制、伤风败俗之人。如任你这样闹下去,必将毁我盛世之气象!”
何曾又转向司马昭奏道:“我主公正以孝治天下,得到全国上下的拥护和响应。为何容忍阮籍这种无礼无德之徒,在服孝期间公然喝酒吃肉于公宴大堂之上?现在已闹得满城风雨了。这事儿要是不严厉惩处,此伤风违礼之邪气,势必很快蔓延到我华夏四方。”
何曾的狠话,恰似一纸分量特重的公诉书,只待司马昭的判决了!司马昭的心,在反复地掂量:这阮疯子也算是我家的僚属,他平时出言行事也很谨慎,未有不利于我,但也没有特别靠拢我。要是此时将他收拾了,定会使天下士人都寒心而饮恨于我。怨恨我连一个从不说是非的疯子都容不下,天下岂有可容之士?想到这些,老辣的司马昭向何曾开口了:“阮籍近来饮酒过多,加上他老母亲离世的打击,他病得已是很不轻了。你就不能替我想想,为我容忍他吗?况且有病而饮酒吃肉,原本也是符合丧礼的!”
司马昭一言九鼎,僚属之中谁敢再进言?只是钟会、何曾之辈先前已串通好,满以为这次阮籍必死无疑。岂料司马昭却一反常态,慈心大发,算是便宜了阮疯子!
表演失败违心醉写《劝进表》
过了些日子,阮籍听人们讲有个叫孙登的高人,独自隐居在北山上的一个山洞里。此人学富五车,通古博今,具有仙风道骨般的风采。阮籍便十分好奇地前去探访虚实。在深山老林里找了两天后,终于见到了孙登。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孙登高人始终一言不发,好似阮籍根本就没有来过!
阮籍只得向他聊起上古之事来,什么黄帝、神农氏的玄寂之道,什么夏商周三代帝王的盛德之美等等。孙登听后,只是抬起头看着阮籍但不说话。阮籍无奈,想了想,接着又向孙登讲起当下流行的如何成仙得道、凝神导气的方法。可孙登依然如故地望着阮籍,连眼珠都没有转动一下!阮籍已然黔驴技穷,不禁仰天长啸一声,转头下山离去。当阮籍下到半山腰,蓦然听得远处传来清澈嘹亮的口哨声,如同神鸟鸾凤的啼鸣一般回荡在山谷。阮籍的心情顿时舒畅了起来。他十分明白,这是一个真正的隐者给予他的回报……
在回来的路上,阮籍一直若有所思。当晚,他早早便吩咐关上了自己步兵校尉府的大门,也不喝酒,伏案沉思默想了一会儿,提笔疾书,写成流传到今的《大人先生传》。这是一篇发挥庄子自由、逍遥思想的名文。阮籍把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寄托在“大人先生”的身上。通过“大人先生”同士君子、隐者和采薪者三人之间的对话,充分表现了他的“齐万物”、“泯生死”的精神境界,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块独立于人世的栖息之地。
在《大人先生传》里,阮籍以“大人先生”的口吻,对世俗间的所谓“君子”,给予了犀利的嘲讽和抨击:“过去,李牧立大功而身遭残死,伯宗忠贞直谏而后代断绝,这都是为了求名取利而却丧亡了身躯,图谋爵禄而却家族灭亡啊!况且,你没有看过那些躲藏在裤子里的虱子吗?它们钻入到裤子的深缝里,躲藏在破旧的棉絮中,还自以为是住在吉祥美好的地方了。它们行走不敢离开裤缝,举动不敢爬出裤裆,却自认为这样是合乎了礼法。但是,当那野火滚滚而来,像烧毁城郊一样将裤子烧焦。躲避在裤裆里的成群虱子想跑也跑不掉了!你讲的这些君子处在人间尘世,同那些虱子藏身裤缝又有什么区别呢?”
公元263年,阮籍已年盖五十有四。而就这年的十月份,他遇到了平生以来最为棘手的一个政治性问题。正是这件政治大事,宣判了阮籍的死期。早从公元256年起,魏国的傀儡王室就无奈地数次动议要给司马昭升爵为晋公、进位相国,赐九锡。此举乃天子之礼,相当于是拱手让帝位了!而相当有谋的司马昭还是感觉于时机的不成熟。没有允诺。这一次,司马昭让人暗示给“魏帝”曹奂:那事儿该办了!曹奂的“帝位”是司马昭给抬上去的,立马就乖乖照办。但是为了做得冠冕堂皇,还要走一走程序:由魏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昭跟着谦让一番,接着由公卿大臣奏文“劝进”。这样一来,司马昭就是上合天意,下顺人心,恭敬不如从命了。
问题出来了:十月上旬魏皇下诏,司马昭致书谦让,接着要有某大臣向魏皇奏《劝进表》。但是,这份欲使魏国“安乐死”的《劝进表》,竟然有人要阮籍来执笔!若以身份而论,是轮不到步兵校尉阮籍来写《劝进表》的。但“异常”的朝廷却没有按常理出牌,偏偏要阮籍获此项“殊荣”!这无异于是逼着要阮籍表态当汉奸呀。而要是阮籍推辞呢?这可是“禅代”政治的关键时刻,司马昭得知后能饶过他吗?阮籍痛恨司马昭的阴险残暴,更加痛恨曹魏后人的窝囊。以朝廷公文的严厉口气,加上几次催逼,天真而无奈的阮籍,只好又借用醉酒的老办法来相应对付。
几天后,朝廷派出的官员来取奏文,此刻阮籍正扒在办公桌上睡觉,当然是个红脸关公,满屋子的酒气了!公差急了,七手八脚地强把阮籍弄醒,焦急地发问:“阮大人!写的东西呢?快给我等去交差!要是今天交不了差,我等小命难保啊!”
阮籍一听,酒醒了大半!虽然面部表情还装得在半醉半醒之间,手脚动作搞得颤颤巍巍,但他无比痛苦的心,却像明镜似的:向魏皇奏《劝进表》,逼我公开表态拥护司马昭,赞同他的篡权行为,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原来就是那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这用心高明而狠毒啊!我要是不写呢,以他们的凶残,我与家人性命不保不说,这几个公差也得受牵连。唉,唉!我的玄言清谈,纵酒佯狂等等,对这个极度残暴的时代而言,最终还是不堪一击呀!
好个阮籍!不愧是魏晋名士、文坛高人。只见他蘸墨挥毫,将那《劝进表》的内容信手写就在了办公桌上,而且是一挥而就!那公差见状,赶紧拿笔认真照样誊正,结果一个字都无须改换。
阮籍写下《劝进表》的当晚,在所遭受的愧疚与悔恨的重压下,自然而然地一病不起了!其后的短暂时日,羞愧、失望、悔悟、哀怨、愤懑,这俱全的五味浸泡着他的全身,搅拌着渗入到他那衰弱的心房。阮籍没有能熬过这年寒冷的冬天,他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作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的离去不是从容的,更不是壮烈的。他离开的瞬间,只有爱妻和儿女们的悲哭声,另有几声昏鸦的哀鸣,算是告慰这抑郁而终的灵魂。而作为一个被严酷政治扭曲的傲世者,阮籍死得确实又很艰难,一种时代悲剧的气氛显得格外的浓烈。不言而喻,那是对当时虚伪“名教”政治的绝妙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