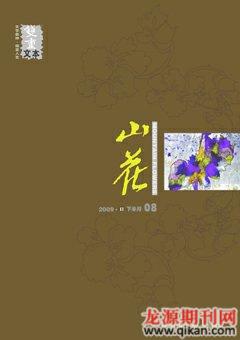“婆媳冲突”叙事模式的变迁与女性解放的再思考
“婆媳冲突”是中国家庭伦理关系的特殊现象,也是古往今来文学家深度阐释的文学母题。从《孔雀东南飞》、《钗头凤》、《窦娥冤》,直至现代的《原野》、《寒夜》、《金锁记》、《孟祥英翻身》,以及新时期的《星河》、《玫瑰门》、《女娲》等,婆媳冲突的叙事模式逐渐出现突破甚至逆转,呈现出现实生活与女性心理的复杂多元,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在简单肯定的同时,更要对不同时代、不同性别作家的观察视角、叙述模式及评判态度作深度辨析。
一、伦理道德批判与女性生存经验的距离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陷入内忧外患夹击之境,以思想启蒙救治国民是接受了西方文明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的选择。破除妇女“附属品”的地位,“使她们做人,做她们自己的主人”,正是个性主义、“人”的解放和自由平等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婆媳冲突涵盖了两代妇女以及母与子、夫与妻的三重复杂关系,理所当然被现代作家再度演绎。
五四时期,男性作家由于身体、心理和情感体验与女性根本隔膜,观察到的始终是社会问题,其作品也只能是女性生活想象性的“仿制品”,是承担男性启蒙思想和拯救意识的形式载体。叶圣陶《一生》、曹石清《兰顺之死》、杨振声《贞女》、鲁迅《祝福》等,都涉及了婆婆(封建恶势力的代表)欺压媳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典型”)的叙事模式,带有强烈道德批判和社会批判倾向,却未曾注意到作为父权文化代言人的“婆婆”也是父权文化的牺牲品。相比而言,在启蒙话语中成长的现代第一批女作家,由于切身体验和“类”的认同感,对婆媳冲突母题的阐释并不止于控诉封建婚姻制度,她们对冲突类型的分析以及女性权利的表述更为贴切。冰心《最后的安息》将婆婆虐待童养媳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教育权被剥夺);陈衡哲《巫峡里的一个女子》逃脱了家庭的束缚,却在父权社会里碰得头破血流(经济权被剥夺);石评梅《董二嫂》为处境恶劣的小媳妇大声疾呼:“什么时候才认识了女人是人呢?”(生存权被剥夺)越过社会现象透视文化心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女性以生育的方式获取了男权文化赐予的权威,再将自身遭受的痛苦报复在下一代非血亲的女性身上,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下,女性解放的艰难程度、时间跨度是这批女性作家无法把握的,迷茫困顿在所难免。
对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多次戏剧改编,透射出20年代文坛对女性解放问题的热情关注。1921年北平女高师学生合编《孔雀东南飞》,1927年杨荫深编《磐石和蒲草》,1929年熊佛西作《兰芝与仲卿》。在大家普遍注意媳妇的苦痛时,袁昌英三幕剧《孔雀东南飞》另辟蹊径对焦母进行深层心理分析,凸现出“婆婆”、“姥姥”所受的煎熬,“苦就苦在我们这颗心没有地方安放”。青年丧夫的寡母在恪守礼教传统的同时,也怀有对幸福家庭的向往和女性情爱的渴念,但“她忠诚热爱和感激的唯一男性就是她的儿子”,情欲爱恨的对象嫁接到儿子身上,自然对媳妇的“霸占”满怀敌意。剧末寡母的疯狂号泣一改以往作品的冷酷疏远,拉近了对婆婆的理解与同情。罗洪1935年的短篇《念佛》、《迟暮》,同样表现出对婆婆这类女性性格心理研究的兴趣。尽管有些“另类”,但女性作家本于生命体验反观女性群体生存困境的叙事尝试,已经与男性创作的功利性泛指和深度模式拉开了距离,也从另一角度呈现出女性心理解放的坎坷波折。
二、评判态度的矛盾犹疑与女性人格心理的反思
“早期男性思想家们一致借用女权主义为利器,反对封建主义;却未等女权主义与女人见面,便将它窒息在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大潮中。”在阶级解放、民族解放成为时代主题之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作者性别,深刻影响作家的叙事模式和评判立场,成为解读婆媳冲突叙事“不可忽视的语境”。
以曹禺《原野》和巴金《寒夜》为例。剧本《原野》的婆媳冲突颇为极端:诅咒、暴力、仇杀、死亡、疯狂……焦母自私残忍阴毒,无论在社会层面或伦理层面都是一个“恶魔”。但对媳妇花金子,曹禺的态度出现了矛盾:在大力张扬她“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原始生命力、深为其神秘妩媚所吸引的同时,又因男性中心意识作祟,对她不合“贤妻良母”规范而深感不安,不断借焦母或叙述者之口谴责其“妖冶”、“魅惑”、“风流”、“强悍”。花金子背负着“不道德”的恶名,必将无法逃脱男权樊篱。很明显,焦母和花金子的极端性格并非生活真实,而是形成戏剧冲突的体式需要,更明显烙有“作家一己和男性群体的想象痕迹”。巴金小说《寒夜》里,汪文宣至死不明白“为什么女人不能原谅女人呢?”他无法体会女性世界的复杂微妙。巴金的阐释是,老派的汪母希望保持“权威和舒适”,鄙视新派媳妇不是明媒正娶、不恭顺,还有经济受挫感,“但媳妇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人”,冲突于是愈演愈烈。应该说,巴金的叙事有所突破:媳妇基于现代教育和经济独立与婆婆分庭抗礼,客观反映了女性自主意识、平等意识的增长。但面对曾树生,巴金的文化立场同样出现了某种混乱,试图在传统儒家文化和现代激进精神之间寻求某种调和,导致他与曹禺陷入了同样的困顿:一方面肯定“现代”女性对自由快乐的追求和对传统的反叛,一方面仍从道德上谴责她“自私”、“逃避”和“虚空”,并设置了她最终被弃的下场。在曹禺和巴金的叙述中,基于男性中心立场的性别优势和道德“俯视”显而易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疏离主流话语的萧红和张爱玲,借由婆媳之间的外在冲突深切体认女人的痛苦和不幸,以此反思女性性格痼疾和心理缺失。萧红将婆媳冲突“冷静”地阐释为女性群体内部的排斥与抗争,《呼兰河传》里“压服”小团圆媳妇致死的,正是以婆婆为首的一群女人。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外在规范已经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随时用它自觉处罚同性“犯规者”。张爱玲《金锁记》则揭示了与男性道德“吃人”相对应的女性性格“杀人”。自闭压抑的曹七巧时刻寻找着心理突破口,无法遏制的破坏性冲动对自己是自虐,“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对他人则是近乎施虐的报复与攻击。她“劈杀”儿(女)、媳的过程,正是由自虐转向施虐的心理变态过程,也是她从弱者的痛苦中获得扭曲的心理“满足”过程。张爱玲对女性人格弱点的“揭密”与“批判”,旨在催生中国现代女性的自省意识。未来文明的大时代里,带有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等“神性”因素的女人,才是“永生的”(《谈女人》)。
三、婆媳强弱对比的逆转与善恶对峙的瓦解
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要求下,解放区作家多以妇女问题表现革命胜利、翻身解放、社会变迁的重大主题。赵树理对婆媳冲突的文学处理,以政治上的先进或落后对应生活上、道德上的先进或落后,叙事模式的转变折射出更多的时代信息和女性解放道路的曲折回环。《孟祥英翻身》、《传家宝》、《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一系列小说,以婆媳关系前后的变化,印证农村家庭关系的调整,印证妇女解放的法律规约。婆婆不仅是道德“恶”的化身,还是政治反动分子、阶级斗争的对象;媳妇则是积极上进的“党的好女儿”,在工作组或党代表的拯救下走出家庭投身革命和生产。如果说五四时代婆媳冲突的叙事文本只“破”未“立”,赵树理模式则指出了解决冲突的“有效”方法——以专政的方式“打倒”婆婆,帮助媳妇“站起来”。且不说作者对女性的有意贬斥和丑化(婆婆们的绰号叫“常有理”、“小腿疼”),单从化解冲突的外部力量来看,“正义”人物正是更高形式的男性权威(“党代表”);而将家庭内部矛盾扩大为阶级敌我矛盾,以专政方式加以解决的结果是:“恶婆婆”迫于政治压力的瞬间转变其实口服心不服,“解放了”的好媳妇则必须承担家庭和事业的双重重压,以“雄性化”换取抽象的“平等”。这其实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另一种异化,与精神、人格层面的妇女解放存在相当的距离。赵树理由于时代和性别的局限,对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和人性内涵的婆媳冲突作了单一化、政治化的解读,“缺乏一种如20世纪20年代乡土作家对父系文化的批判意识”。然而,“男作家的叙述权威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和意识形态现象”,总体而言,当时女作家的叙事大都性别意识弱化,未能对婆媳冲突作出新阐释。
新时期女性话语再度崛起,面对婆媳冲突母题,当代女作家在意义和表征方面多有继承和超越,一方面与历史对话,发掘被掩埋的女性独特经验,颠覆超稳定的男性中心意识;一方面反观自身,反省作为文化创造参与者的女性自身(婆媳双方)的缺陷,探寻人性之全。无论是历史对话还是自我独白,均体现了当代女作家对文学现代性与女性解放的全新理解和不懈追求。
上海作家王小鹰特别关注封建意识的残留问题,小说《星河》、《春无踪迹》、《你为谁辩护》均有婆媳冲突的文学表述。媳妇无法实现工作理想,还受婆婆导演的“借夫受种”闹剧侮辱,试图离婚更遭谩骂殴打。作家指出,在制度给予女性一定的权利和地位之后,婆婆仍无法融入社会更无力与男权正面为敌,只能将同性作为攻击目标,以转嫁无法定位的心理危机。新一代女性必须清除灵魂中的男权意识,张扬女性自觉,才能成为生活的强者。可惜,作品最后安排女主人公在现实的威压下作了自我安慰式的退让。王小鹰的妥协,暗示了当代女性既本能地抗拒男权意识,又在潜意识中受其牵引的折中倾向。“后新时期”的女性文本颠覆破坏的姿态更为决绝。铁凝《玫瑰门》以类似张爱玲的叙事策略,从异化扭曲的女性身上反观男权文化的罪恶。正是男权文化对婆婆司绮纹的拒绝,使她从清纯的进步学生演变为复仇女神,“为了争得一份光明一份自身的解放,她甚至诅咒一切都应该毁灭”。在此,铁凝的审“丑”比张爱玲走得更远。媳妇竹西听随欲望召唤,完全蔑视婆婆并实施报复,她的残忍导致了丈夫和婆婆的死亡,象征着女性与男权文化的彻底决裂。整体来看,“玫瑰门”暗示了一个“报复—反报复—自我报复—共同报复”的怪圈,正是女性之间的这种猜忌、窥视、践踏,造成了女性生存语境的恶化。这正是铁凝的创作本意:将简陋的道德判断延期,转而揭示背负文化传统负累,又受原欲驱使的人类“另一半”的生命本相。徐坤《女娲》同样消解了婆媳善恶对峙的界线,婆婆疯狂报复媳妇以弥补自己的不公正待遇,“弱女子”媳妇与公公乱伦生下傻儿子,傻子长大强奸母亲;媳妇借政治运动斗婆婆,婆婆教孙子仇视父母——报复和反报复不断升级,在不动声色中将女娲造人的母性神话全盘否定;而疲软、弱智的男性形象,也将父权神话彻底摧毁。反神话的女性寓言式文本,完成了从控诉男权社会到解构女性自我的蝶变;只是,反叛和解构之后,女性话语和女性解放该何去何从呢?社会现实和作家文本都没有给出正面回应。
文学作品中“婆媳冲突”叙事模式的嬗变,演绎出被男权文化遮蔽、放逐的女人们曾经鲜活的生命历程。诚如葛兰西所说,文化上的非暴力革命比政治上的暴力革命更为重要,女性解放不应只是一种社会革命或社会运动,它必须也必然伴之以一场深刻而持久的“文化革命”。而包括女性写作在内的文化自救(而非被“拯救”),应该成为女性解放和文化生态平衡的可行策略之一。
参考文献:
[1]罗家伦.妇女解放[J].新潮,第2卷第1期.
[2][美]伊莱恩·肖瓦尔特. 我们自己的批评[A].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李小江.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A].邱仁宗等主编. 中国妇女与女性思想[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6]巴金.谈《寒夜》[A].巴金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7]葛兰西语.转引自[美] 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大学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
刘冬梅(1976—),女,湖南常德人,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艺思潮与文论。
——细读《孔雀东南飞》